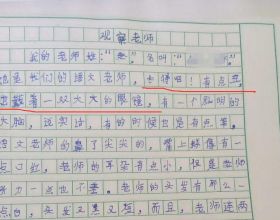文/華靈
1974年,甲寅虎,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聽說那天霞光萬道,一個新生命降臨在豫宛盆地,體重三斤六兩【如今是一百八十斤】剛生下來不會哭,接生婆用銀針在指尖扎一下,終於哭了,聲音細微,但還是改變了這個院落。還嘬不動奶,靠父親吮開後方得享用。作為大家庭的長孫,他受到了特別的優待,母親坐月子吃滿了一百個柴雞蛋。河對岸是著名的光武中學,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當年練兵起義的地方,如今還留存著一棵千年漢槐為證。當時是文革後期,大集體,中華大地上色調單一。
他記事的時候是1981年,聯產承包責任到戶三年後,是年小麥喜獲大豐收,北方農村從此告別了“三紅轉”(早上紅薯玉米糝,中午紅薯面面條,晚上紅薯茶)也告別了黑窩頭(一種用紅薯面蒸的饅頭,黑乎乎的,粘嘴膩牙不好吃)和花捲(紅薯面小麥面分層卷的饅頭,有的還滲上玉米糝),如今倒想回味兒吃吃看,但哪裡有賣?
1986,丙寅虎,小學剛畢業,就鬼使神差般與文學有了初次撞懷,寫下平生第一首詩,就是那首在我心內著名,口中常道的打油詩:“日落西山紅,月出白露生;寂靜夜朦朧,雄雞歌黎明。”在此期間國家百業興舉,農村萬元戶,城市個體戶名噪一時,色調也有單一轉為黑白。
1998年,戊寅虎,二流大學畢業的我,在市糧食局下屬的一家期貨公司上了一年班,月薪四百。此時祖國的發展已進入快車道,各種股票,期貨期權如雨後春筍;各類公司,資產重組如火如荼。我們既經歷了亞運會的輝煌,蘇東劇變的錯愕,銀河號的恥辱,也經歷了1997亞洲金融風暴的猛烈衝擊。在朱總理“下崗分流”的拳拳號召下,我順利下崗,拋棄那華而不實的虛假專業【公共關係專業】,在身為赤腳醫生父親“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勸慰感召下,唱著劉歡的《從頭再來》重新邁入本地一所國醫院校,研習岐黃之術。三年後順利畢業,並考取鄉村醫生資格證,算是子承父業,兩代人雙雙踐行著偉大領袖“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深刻理念。此時的祖國已變得五顏六色,銳不可當!
2010年,庚寅虎,我又繫上紅腰帶,穿上紅褲衩。“而立”遠去,“不惑”遙望。期間我的祖國既經歷了跨入世貿的紅利,奧運會的輝煌,也經歷了令人痛心的駐南大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和汶川大地震。母親也於2006年不幸辭世。面對歲月的饋贈和猙獰,我和我的祖國砥礪前行。經過不懈努力,我順利獲得了國家醫師資格證書。“雷曼時刻”之後,祖國經濟雄踞世界第二,重回塔頂指日可待,顏色也日趨斑斕五彩。
如今壬寅虎年又至。在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文化戰兩強相爭的複雜世界地緣格局中,在新冠疫情肆虐蔓延又隱染不斷的灰暗日子裡,我們的心會多一點理性,多一點思考,少一些任性,少一些驕傲。這些年雖說並非碌碌,但也確無建樹,時不時在網上衝浪,曬曬自己的小資情調和小感慨,為即將到來的天命之年增磚添彩。而祖國,始終是籠罩在我頭頂靉靆雲層中的第一亮色。
回首往事,不僅有飛龍在天的夢想,也曾有膽小如兔的逃避;不僅有猛虎下山的豪邁,也曾有沉睡如豕的消極;不僅有老驥伏櫪的堅持,也曾有抱頭鼠竄的狼狽;不僅有牽牛牧羊的閒適,也曾有雞飛狗跳的日子;不僅有猴年馬月的疑問,也曾有畫蛇添足的多餘……如今漸入天命,才知有些事可為,有些事不可為——心有猛虎,細嗅薔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