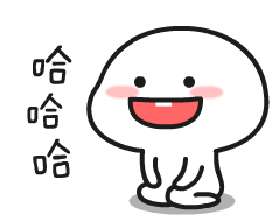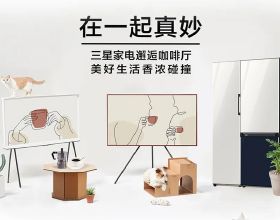勞拉申
在“佛國聖境”山西,一場絲路藝術展,正在冬季的山西博物院拉開帷幕。190餘件東地中海、兩河流域、波斯、阿富汗與印巴地區的珍寶,從日本山梨縣的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來到山西。
被譽為“當代玄奘”的平山鬱夫,一生行走絲路70餘次,保育大量阿富汗、印巴地區犍陀羅佛像,來到堪稱“中國佛教文化博物館”的山西,將佛教的前世今生娓娓道來。平山鬱夫拓展了玄奘的佛經之路,他深入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旅程與東漢的甘英、元朝的拉班·掃馬更吻合。
策展人設計的路線是絲路的逆行,從地中海到中國,由西向東。或許是想將最珍貴文物放在最前面,以吸引觀眾進場,但有種從西方人視角看東方的感覺,彷彿馬可·波羅前往中國的旅行。
文物珍貴好看,特別是黎凡特地區、兩河流域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但對普通觀眾而言,若沒一定史學功底,理解起來是困難的,有人甚至直呼“看不懂”。策展人雖將珍稀文物置於前端以吸引目光,但若沒能對觀眾進行及時的“藝術教育”,恐難達到理想效果。如能更精細化一些,在門口擺放歷史科普小冊子供觀眾提前預熱,或對場地進行更多3D效果和多媒體展示,比只將文物置入櫥窗更能增加觀眾的身臨其境感。
展覽彌補了中國觀眾長期存在的認知偏差,中國人自幼聽聞希臘神話故事,習慣性地將黃金比例、完美線條視為歐洲美學,但絲路文物上的希臘式審美提醒了觀者,“希臘式審美”只是現當代地緣政治產物,從不專屬於西方。當今世界,西方是“勝利者”的代名詞,連同文明一併捲走,巧妙地偷換著文明的歸屬。

犍陀羅浮雕《通往淨土的旅程》,兩位伊朗人坐在馬車上,最右手持花環的是希臘酒神狄奧尼索斯
展覽無疑帶給觀者當今世界稀有的體驗,文物大多來自如今最混亂黑暗的國度:2003年爆發戰爭的伊拉克、2011年爆發內戰的敘利亞、2021年被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邊境衝突懸而未決的巴基斯坦、被西方視為“邪惡軸心”的伊朗。在殘酷戰亂與流血中,無數珍寶被夷平,卻被日本保護下來。日本人對絲路無疑愛得深沉,迄今為止關於絲路最經典的紀錄片,還是日本NHK1980年製作的《絲綢之路》。平山鬱夫認為,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流,日本應對中國文化的恩惠予以回報。
戰火讓世人忘記了敘利亞的文明價值,這場展覽帶給人們重新認識敘利亞的機會,巴爾米拉、阿勒頗曾是古代絲綢之路最西端,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2015年,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洗劫了敘利亞巴爾米拉古城,巴爾夏明神廟和貝爾神廟均被炸燬。敘利亞國寶級考古學家、巴爾米拉文物局局長、82歲的哈立德·阿薩德,為了保護故土文明,不惜與殘忍的恐怖組織對峙,被斬首示眾,成為巴爾米拉古蹟的殉難者。哈立德·阿薩德永遠不會知道,他畢生保護的巴爾米拉文物,今天仍被一位日本學者虔誠地保護著,並被遙遠的中國觀眾致敬著。
當我在山西博物院,看到眼前幾尊公元2-3世紀敘利亞巴爾米拉的雕像時,我為其精美深邃的面孔傾倒,也為那飽含千年憂傷的眼神折服。這是一位希臘哲學家的頭顱,頭髮捲曲、面孔俊美,眼神充滿深深的哀傷與悲憫,彷彿早在1800多年前,就一眼望到今日的人間悲苦,望眼欲穿。
這個戰火紛飛的中東阿拉伯國家,它遙遠的歷史絕非伊斯蘭,而是壯美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早在公元200-300年的巴爾米拉,就留存了許多死者雕像,散落於古蹟,有眼神悲傷空洞的老者,有滿頭長髮而苦難吶喊的女性,表情皆是殉難者神態,傾訴著千年來這片土地的悲情。在巴爾米拉殉難的哈立德·阿薩德,是否也將化為一尊死者雕像,永遠地留存在這片廢墟之上?
他們是死者,可透過玻璃凝視這些千年前的神態時,我看到他們從未死去。每尊雕塑依然活著,保留著永恆的靈魂。精美的小石雕,講述著巴比倫神話中冥王奈爾伽爾的故事,廢墟始終與死亡相連,卻又從未死去。如果天堂中的哈立德·阿薩德得知他的畢生所愛,此刻正在中國被同樣愛著這些文物的人們觀賞,能否得到一絲心靈慰藉?平山鬱夫去世於2009年,若他得知巴爾米拉古城被炸燬、他的同行學者殉難,又會是怎樣的悲痛?此刻,東西方兩位考古學家,是否穿越時空,在天堂彼此致敬?
展覽為轉變觀者的世界觀提供了難得的視窗。這些展品源自阿勒頗、巴士拉、摩蘇爾、巴格達、喀布林、白沙瓦等地,而每當《新聞聯播》快結束時,這些地名就不斷在世界新聞板塊中提到,人們對電視裡這些遠在天邊的地名,麻木、漠不關心,除了戰爭、混亂、窮困,它們似乎一無所有,被拋棄,錘死,乞丐般苟延殘喘。但掃去當今世界局勢的荒誕不堪與現代性的不置可否,這些地名曾是人類文明史最耀眼的珠寶。最燦爛的文明總是與最殘破的現代一體兩面,善惡同體,正是波斯拜火教的“二元觀”,善與惡不斷交鋒,世界從一開始就是二元並存。
帕蒂亞帝國時期的香器敘述著波斯拜火教的歷史。文物展示著古波斯精美的生活方式:金屬器皿、琉璃酒杯、帝國王冠、金銀銅幣、奢華珠寶,即使是“來通”這樣的注酒器也是獨具匠心的牛獸造型,安靜的博物館內彷彿一派歌舞昇平。可惜的是,展覽沒有與山西博物院館藏很好的結合,山西博物院館藏的夏朝文物、波斯薩珊王朝酒器、刻有波斯圖案的虞弘墓等,均可與展覽中同時期文物對應,方能匯通增補。
在《旅行的藝術》中,阿蘭·德波頓寫到,“在壯闊中了悟自身的侷限十分有效,它幫助我們接受那無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惱的事情,並接受我們終將化為塵土的事實。”平山鬱夫的絲路行程累計80萬公里,中亞旅途荒無人煙,人跡罕至。平山鬱夫對荒蕪的著迷與他的出生相關。他成長於廢墟,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見證了萬物毀滅,還因核輻射感染白血病。他在被毀滅的絲路上行走,從佛教中獲得慰藉,最終治癒病魔。
平山鬱夫系統性的犍陀羅佛像收藏,是展覽的高潮,也是最為中國觀眾稱絕的部分。佛教是山西重要的文化積澱,犍陀羅佛像的展出直抵觀眾心聲。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佔領阿富汗,恐怖主義甚器塵上的阿富汗被譽為“帝國墳場”,但公元前6世紀這裡曾是一片佛國淨土,名為犍陀羅。
犍陀羅藝術兼具印度婆羅門教、波斯與希臘藝術風格,佛陀與希臘神明常常出現在同一雕塑主題中,我不禁思索,希臘藝術對於犍陀羅,究竟是影響還是模仿。犍陀羅古蹟巴米揚大佛位於阿富汗,2001年已被塔利班炸燬。然而凝望眼前的雕塑,只有佛法的不執分別、無弗遠近、無有高下、圓融自在。
可貴的是,策展人將山西雲岡石窟佛像與犍陀羅造像進行了對比,並以圖片形式展示佛陀身姿在犍陀羅時期與中國北魏時期的共通之處,直觀地展現犍陀羅藝術對中國佛教造像的影響,事實上中國佛教很可能不是直接從印度傳來,而來自犍陀羅。然而,犍陀羅對大部分中國觀眾仍是陌生的,若能在講解牆上將犍陀羅與中國佛教的關係更多闡釋,觀眾將對其有更強的體悟感,否則只是走馬觀花,缺少聯結。
展覽提及的朝代、地名多采用西方普遍的稱呼,增加了中國觀眾的認知難度,因為絲綢之路地名的說法東西各不同,如“帕提亞帝國”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帝國”,“犍陀羅”“貴霜”即中國史書中的“大月氏”,策展人若能將這些概念多一些補充說明,可以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文物。
從展廳出來,我在紀念品店看到根據展覽文物造型創作的文創產品,十分新穎。但產品未成體系,特別是精美的犍陀羅藝術,絕對是文創的豐富靈感源泉,值得好好開發。另外,平山鬱夫的絲路收藏、犍陀羅藝術在日本和國內都有不少出版物,完全可以在文創商店銷售,不僅幫助觀眾瞭解文物,也能實現出版業與策展業的聯動。
展覽不僅需要珍貴的文物,也需要更精細化的視覺設計、產業聯動,方能與當代人的審美需求與文化消費結合。平山鬱夫的絲路收藏展已在中國許多城市巡迴展出,日本人對絲路藝術的求知精神,值得國內藝術界借鑑,正如平山鬱夫曾說:“在不懈的追求中,每個人都可以獲得自我救贖,都可能讓上天改變計劃。”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