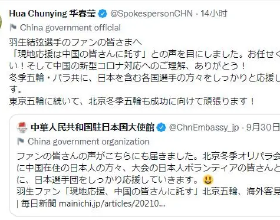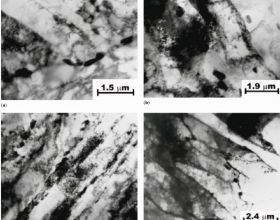在唐代,紋身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表現,在詩歌的時代,當然要透著濃郁的詩歌味道。
那時人們特別崇拜大詩人,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粉絲,他們竟把詩人的作品或者意境紋到身上,雖然有附庸風雅之嫌,但是顯示了他們對詩人的喜愛和崇拜。
最為典型的是荊州葛清,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凡刻三十餘首,體無完膚”。並且詩間配畫、畫中藏詩,如“不是此花偏愛菊”句旁則刺一人持杯臨菊叢;而“黃夾纈林寒有葉”則配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當時就有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白居易知道能有這樣瘋狂的粉絲,應該是很高興了。
瘋狂喜愛當時詩人的還有蜀小將韋少卿。這個韋少卿沒有多少文化,但是他偏偏喜歡文學家張說的詩,就在“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系索,有人止於側牽之”。韋少卿的紋身竟然體現了張說“晚境寒鴉集”詩歌的意境,堪稱一奇。
還有一些小混混,有時也會作詩慨嘆人生,還給紋到了身上:會昌年間(841-860),少年紋身之風更盛,“賊趙武建,扎一百六十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幾句打油詩,將其亡命天涯、得過且過的心境表現出來。
還有“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處,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他寫的詩表達了自己家道敗落、身處困境無人搭理的悲苦,以及無聊與對社會現實的憤恨,詩歌的朝代就是不一般呀!
唐代紋身還有一個功能,竟是為了能保護自己,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趙高在背上紋了毗沙門天王就是四大金剛之一後,官吏因敬畏天王而不敢杖打趙高。人家刺個四大金剛就連官府都無從下手,紋身反而成了他的保護傘,豈不怪哉!
更有甚者紋身洩私憤:“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
還有更高階的,一位叫崔承寵的少時“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紋身也沒耽誤他做官,還幹到了黔南觀察使。平時他用衣服遮掩這些紋身,往往到了酒足飯飽之時,他就會用此捉弄那些戲子優伶。他捋起手臂,大叫蛇咬你,以此取樂。這些段子都被唐代的段成式記載到了《酉陽雜俎》裡。對此,《清異錄》說:“自唐末,無賴男子以扎刺相高”。
大唐的紋身玩到此時,可謂是爐火純青的地步。如果僅僅是美化人體,調節生活也就罷了。可是物極必反,紋身也走了下坡路。
唐代後期的惡少年、乞丐、地痞、惡霸、流氓等好逸惡勞之徒氾濫成災,他們憑藉強力,以紋身作為團伙標記,幹出了許多欺行霸市、橫行鄉里、為非作歹、魚肉百姓的種種惡行。
一旦紋身危害了社會,政府就不會袖手旁觀了,大和九年(835)楊虞卿擔任京兆尹時,就是首都長安的市長,這個市長可肩負著保一方平安的責任,首先打擊了一個紋身惡少:“市裡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無論藏到天涯海角,也不會放過,楊虞卿堅決捕來杖殺之,並判曰:“鏨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罪。”
雖然打擊了一個紋身惡少,但是大多數沒有受到影響,他們繼續為非作歹。
到了武宗會昌年間,有一個住在大寧坊的張幹,雙臂上刺了兩句話,左胳膊上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的是“死不畏閻羅王”,很是囂張,公然挑戰官府。
張乾和這些惡棍一起,經常在大街上打架鬥毆,強行搶劫路人,他們還會把一群蛇放進酒店的大廳中,訛詐店主的錢財,一旦犯了事他們就躲到禁軍的兵營中去,這使得幾任京兆尹都對他們無可奈何。給京城的治安帶了極大地隱患,百姓苦不堪言。
《舊唐書.薛元賞傳》記載了:善於碰硬的薛元賞上任長安京兆尹後,迅速掀起了掃黒除霸風暴。
上任的第三天,薛元賞就開展了一次集中打擊行動,按照事先摸好的底子,密捕了30多個首惡,審訊完畢,命令身強力壯的衙役痛打首惡,公堂之上血肉橫飛,慘叫連連,不一會,30名首惡分子全部活活打死。隨後薛元賞又命將這些無惡不作的痞霸分子陳屍街頭,以儆同類。
當然“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的張幹也在此列,此等手段令脅從分子膽戰心驚,再也不敢招搖過市,欺男霸女了,至於其他跟風紋身的人,也都被責令灸去。
此後一段時間,文身在長安城絕跡,長安城的惡棍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