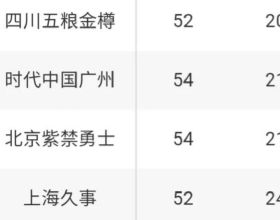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農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狀況相對要好一些。由於在通貨膨脹的形勢下農民一般要比依賴薪水的勞動者好過些,這種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假定看起來似乎是合乎常理的。
實際上,戰爭也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稅捐。作為一系列複雜因素的結果——包括減產、不利的價格關係以及不斷增長的租稅——戰爭後期鄉村的生活條件嚴重惡化。
1、前三年戰爭初期的農村生活
在戰爭的第一年,大自然惠顧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農民:1938年和1939年的糧食產量比戰前時期的平均水平高出8%。然而,從1940年到1943年,糧食產量均低於戰前平均水平。最嚴重的是國民黨統治區主要的糧食作物——稻穀在整個1940一1945年中均明顯地低於戰前標準。
然而,在戰爭的前兩年,實際上所有的農民——尤其是農村人口中的貧困部分——獲得了相對的充裕。大豐收抵消了農產品價格下降的影響。悄悄的比較溫和的通貨膨脹趨勢所導致的資金充裕,緩和了農村地區傳統性的現金短缺,因而有益於那些債務人,包括借貸者和購買土地者。稅收的負擔也大為減輕,因為稅收機關一般都不能以增加稅率來彌補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失。
然而,從1940年始,趨勢改變了,農村貧富之間的傳統差距擴大了,大地主階級更趨富裕,而同時其他的大部分農戶(包括小地主)感到日益增長的經濟貧困。看起來矛盾的是,農村民眾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卻是農產品價格急劇上漲的結果。如在重慶,米價在1940年5月至12月間就上漲了50%。
那一年的稻穀歉收——比上一年減產19%——是價格上漲的原因之一。也許,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正在公開市場上大批購進稻米以供應它的正在膨脹的軍隊,以及1940年6月宜昌城的淪陷,它是產稻省湖南和湖北通往四川的轉運點。
這些事件造成了人們的恐懼,害怕稻穀供應量的減少不只是一個暫時現象,大批的囤積和投機由此而產生。個體消費者購存大量的稻米以防備短缺和更高的價格,而同時,地主和商人積貯稻穀不投入市場以期待日益上漲的價格。由短缺刺激起來的進一步的短缺就這樣傷害了民眾計程車氣,並開始使政府難以獲取必需品。
恐慌在蔓延,爆發了一些搶米風潮。對於這些,蔣介石在1940年11月宣稱:
“我們一定要懲罰這些自私的有錢人……不論他們怎樣分散囤積物資,也不論他們多麼狡猾地藏匿這些物資,我都會把他們的底細弄清楚……如果他們不拿出存糧……就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
為了實踐這一諾言,成都市市長因囤積而被捕,並於12月被槍決。
2、後五年農民苦難的緣由——苛捐雜稅
在政府的苛捐雜稅中,田賦的重要性僅次於徵兵。自1928年以來,田賦及有關的附加稅一直由省和地方政府徵管。但是,在1941年7月,中央政府把田賦國有化,並開始以實物徵收——即徵收糧食及其他的農產品——而不是徵收現金。這是一個重大的財政改革,它對農民甚至政府本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只要有可能,政府就以稻米徵稅,因為士兵和政府僱員們希望供應稻米,儲存和運輸這樣單一種類的糧食也比較簡便。然而,只是在6個省份(雲南、廣西、廣東、湖南、江西和浙江),稻米才是唯一的抵稅糧食。在不產稻地區,必須以其他的糧食替代(如1.4市斗的麥子可抵交1元稅)。
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農民就承受著明確規定的田賦以外的一大批稅捐和勞役服務。戰爭時期,這些稅捐種類和負擔驚人地增長。這些稅有的是由中央政府徵收,如鹽稅,到1944年已成為重慶歲入現金的最為重要的單項來源。不過,其他更大量的稅都由各個地方政府所制定。
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田賦的統一徵收,中央政府佔用了省級政府的財政基礎。作為補償,中央政府在1941年付給省縣政府相當於原來田賦收入1/2的津貼,次年,中央政府不給直接津貼,而改從各種稅中把一定比例的收入劃歸地方政府——如15%的田賦、30%的營業稅以及25%的遺產稅。
然而,這些津貼和部分劃撥完全不足以滿足地方政府的開支,因此,他們就必須搜尋其他替代的歲入來源。例如,縣政府現在便把屠宰稅(這是一種附加到豬肉、牛肉、羊肉價格上的稅捐)當作新的重點收入來源。在戰前的1936年,這種稅不超過縣政府歲入的4%,從1942年始,它成為省政府經費的一個主要來源。此外,地方政府還實行各種各樣的攤派。
攤派,是混亂的特殊形式的稅捐,它有時按年度徵收,有時按月徵收,有的僅徵過一次或不定期徵收,它被用來應付一種特別需要或填補一個突然虧空。嚴格說來,大多數攤派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數的攤派也都是得到了更高一級當局的默許而徵收的。在國統區的任何一地都有這種攤派。在四川,1942年的合法攤派只有保甲捐和教育稅。·然而,在那一年對18個縣的調查中發現有240種不同的攤派。一個縣僅列了11種攤派,另一個縣則有67種之多。攤派的種類令人吃驚。例如,有“捐獻新兵草鞋”稅、“軍屬慰問”稅、“防空幹部訓練”稅、“衛戍部隊油料"稅等。
此外,還有為救國債券、電線杆、修路、教員米糧津貼、學校裝置、保長會議食物及油料、保長行政補貼,軍屬喪葬費用所徵的稅捐。在這些稅捐中有一些數額相當大,有的比較小。
約有1/4的稅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略少於1/4的稅捐由地方士紳和宗教組織設立,一半以上則由鄉村和保甲頭目創立。然而,在所有這些稅捐之中,那些為軍隊籌措資金和供應品的徵收是最重的負擔。正如貴州省主席、知名的國民黨領導幹部吳鼎昌所抱怨,高階當局常常命令縣政府為軍隊和其他防衛需要提供經費,而不考慮這些錢如何去獲得。
還有,駐軍常常需要豬、雞、木柴、飼料、工具、建築物資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解決辦法是下達新的攤派。
攤派的一種特殊形式是軍糧,在那些稅糧供應不足的地區或因運輸問題妨礙了向部隊提供米糧的地區,軍隊的高階指揮官可能向地方政府要求需要的稻米。於是地方當局向本地區居民下達定額、監督糧食的徵收,並徵發勞力把它運輸到指定的徵集中心。根據1946年的一份材料,通常是由商人承擔軍糧的30%,農民承擔70%。像徵購制度一樣,為軍糧所付出的報酬是永遠不變的,其價格遠遠低於市價。而且,由於錢要經過許多官員的手,他們常常刮下一部分,這樣通常只有很少的報酬到達農民和商人個人手中。
根據粗略統計,1940一1944年徵收軍糧的全部數量似乎約等於同時期田賦徵糧的10%。但是,軍糧負擔的輕重在不同地區是不平衡的。有些省份,如湖北、河南、陝西、四川,那裡駐有大批部隊,它們付出了過度的稅捐。例如四川就提供了所有軍糧的1/4至1/2。在第五戰區和第六戰區部隊集結的湖北,1942年的軍糧竟達田賦糧和徵購糧總和的77%。
像陝西這樣的西北省份的負擔無疑也是很大的,因為胡宗南將軍所謂的精銳部隊僅僅在1941年這一年獲得過充足的糧食供應。在所有的其他年份,部隊必須“就地取材”。”
3、後五年農民苦難的緣由——艱難的勞役
正如農民為支援戰爭提供了不相稱的經費和糧食一樣,他們還提供了最大的人力,去當兵及做苦力。政府徵發勞役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並不是件新鮮事,但是戰爭的需求使它成為巨大的負擔。男人、女人和孩子們被徵發去建築要塞、戰壕、道路和機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在滇緬路的修築中,就徵用了16萬勞工。
50萬人被徵募去修築9個飛機場以供美國B-29轟炸機及配屬的驅逐機使用;另有50萬人挑泥擔土為湘贛鐵路鋪築路基。數以百萬計的人被強徵來從徵集中心向各分配站運送稅糧和軍糧,有時用船隻、大車、手推車,但有時,如在湖北,足有一半的大車不能使用,所以必須以人肩挑扛。
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報告說,在安徽每當收穫之後,人們排著長長的隊像無間斷的蟻流那樣,向省府的倉庫運送糧食。
儘管每項工程的待遇之艱苦各不相同,但是這些徵役的勞動條件都是同樣粗陋。勞工們只得到很少的或完全得不到報酬;準備發給他們的工錢常常被各級官僚機構的掌權者所“榨”去;茅舍和衛生條件是原始的。
在四川的機場工程中,勞工們載著石筐要走很長的路程,有的一天最多也只能走完一半行程,成千上萬的人死去、逃跑或嚴重受傷。在滇緬路的修築中據報告有7000人死亡。一個曾任徵募勞工監督的人報告說,勞工們來自60至100裡以外的地區,每次服役10到15天,吃著粗糙的食物,居住在簡陋的茅屋中。但是,據他回憶,勞工們不在乎。實際上,真實情形恰恰相反。原糧食部長徐堪承認,就糧食運輸而言,“每一個人都不願從事這一工作”。
1943年12月,重慶頒佈了一項義務勞動法,要求年齡在18至50歲之間的男人每年必須做10天的有償勞動。同年,湖北省政府起草了一些條例,規定應該支付勞工工錢或一定數量的糧、油、鹽,而且這些勞動應被限制在農閒季節。像那一時期國民政府的大多數法律一樣,這些規定與其說是對現時實踐的法規,莫如說主要是陳述未來的目標。
4、農民承受的負擔
對於戰爭時期農民賦稅負擔的增長是沒有嚴重爭議的。就增加賦稅負擔本身來說,國民政府並未錯,這是戰爭,公民的負擔變得繁重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有爭議的是這種賦稅負擔的增長是否對農民的生計和政治觀點產生了嚴重的有害的影響。
做一個大致的估計,戰爭後期的攤派負擔約等於同期綜合田賦的兩倍。但是比起田賦來,這些混雜捐稅的徵收更加多變,更使人難以承擔。
例如,1942年對四川攤派的調查結果表明,在調查的18個縣中只有1個縣的人民能夠平安承受攤派負擔;另4個縣的人民須經過一些努力後才能承擔;而13個縣——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絕大多數人感到攤派負擔是極為沉重的。
這樣的考察顯然是走馬觀花的,然而它可能是人們對攤派強徵的一系列反應的比較準確的反映。
調查還發現攤派負擔偏壓在小地主、自耕農甚至佃戶這些農村社會的貧苦階層身上,大部分富裕村民和與政治及秘密社會有關係的大地主,能夠說服保甲長以及其他的攤派徵收者寬容他們或強迫他們的佃戶付稅。
大地主和鄉紳集團的富裕成員實際上一直拒絕與政府稅吏合作。定額80%以上的攤派系由保甲長們負責,他們的腐敗是臭名昭著的。他們常常同時徵收好幾種稅,這樣農民們就無法知道他們正在交納的是什麼稅或每一種稅各有多少。更有甚者,他們很少開收據。這樣對他們壓榨的限制辦法便很少而且無效。
其結果是,攤派的實際負擔大大增加。四川的一份調查推測,保甲長們把他們徵收的攤派金的l/3塞進了腰包。1947年的一份官方出版物也指出,投機常常使農民的實際攤派負擔加倍。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政府加於中小土地所有者身上的合法和非法稅捐的全部負擔是多少呢?
這是他們承受徵稅者不斷需求的主要壓力。根據1945年初的《大公報》所載,小農們的付出量五倍於政府下達的賦稅,因為大地主將其大部分賦稅負擔轉移到他們身上。這個數字是與當時的若干估計相符合的,即許多農民的賦稅負擔是他們收穫物的30%、50%,甚至更多些。如果把它總的理解為是指政治上沒有勢力的貧苦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地主階級,這個數字看起來是可信的。
也許,對於賦稅負擔的最令人信服的非定量評價是一位著名觀察家在1945年所說的“許多人已經感到他們不能忍受”。
或許,正如同年5月國民黨官方所承認的:“戰爭中,農民以提供財力和人力的方式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的生活是最困難的。"
5、農民生計艱難下的政治選擇
到戰爭後期,特別進入1943年以後,稅制的敗壞、貪汙、減產和通貨膨脹在鄉村都已非常明顯,一小部分農戶,主要是大地主更加富裕——中央政府在1945年認識到了這一事實。由於改善部隊生活狀況遇有財政壓力,政府便發起了一個專門的“捐糧運動”,其目標主要是大地主與富農。
調查指出,1937一1941年間,地主對土地佔有量在四川省從69%增長到70%,在西康從67%增長到72%。
同年對於雲南昆明附近的一項類似的研究顯示,戰爭期間61%的農民家庭生活水準下跌,只有24%的人(主要是大地主)改善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大體上不變的佔15%(主要是中等地主)。同一時期,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也注意到貴州的同樣趨勢。他寫道,只有“極少數人“過著比過去更高消費水準的生活,而同時廣大民眾的消費已降到不能再降的界點。
1942一1943年河南的饑荒明顯地暴露出政府的苛捐雜稅對於農民的生活能產生何等關鍵的影響。
乾旱、霜害、冰雹和蝗禍使1942年的春夏收成減到正常年景的25%。結果,人們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將肯定要面臨著糧食短缺。使這種匱乏演變為嚴酷可怕的有數百萬人餓死的饑荒的正是政府無情的徵稅和軍糧徵收。
近百萬軍隊駐紮在這個省,他們都得吃飯,而那裡的運輸器械已經被戰爭所破壞,因此士兵們的食物必須由地方提供。是讓軍隊捱餓還是讓農民捱餓,這對於當局來說可能是一個困難的選擇。但是在戰時軍隊獲有優先權。無論有什麼樣的正當理由,結果是可怕的。
農民們交出了最後的麥子以納稅,數百萬人背井離鄉去山西和其他鄰近的省份逃難。農民們不顧一切尋求食物,僅僅是為了得到一斗左右的糧食就會賣掉曾視如寶貝的土地。據報告還有許多人賣兒賣女。政府終於意識到了這一危機,宣佈減兔1/4的田賦。
但是,根據所有的報告,地方官員和軍隊對糧食的要求仍未放鬆。許多人靠吃樹葉、樹皮、花生殼甚至據說還有靠吃人肉度日的。餓死者中有相當大比例的人死於1943年春,這時新的麥子已經長出了顆粒。絕望的農民磨碎這些未成熟的麥子,吃這種漿糊,以至於許多人腫死了。白修德估計,1943年3月,由於這場曾被人稱為“人為饑荒"的災難,約有500萬人“死去或瀕於死亡”。
河南的悲劇是一個極為悲慘的例子,由此可見政府的苛捐雜稅是如何加劇了農民的貧乏。其他地方也都存在著許多同樣的情況,它至少能夠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從1942年起整個國統區的農民的劇烈反抗和起義日益增長。
如1942年初在甘肅6萬人席捲了這個省的20個縣。他們的口號是:“甘肅人治理甘肅!反對徵兵和糧稅!殺盡南蠻子!”
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造反者擊敗了所有派來對付他們的地方軍隊。最後,在1943年的6、7月,經過40天的戰鬥,胡宗南將軍的精銳部隊鎮壓了這一暴動,據報告殺了14000餘人,俘虜了18000人。
1944年在湖北北部,數百人打著反對政府的糧稅和勞役的旗號,在三個鄉內殺死官吏,燒燬了所有政府管理機構。雖然在6月份被驅散,但一個月後,人們更兇猛地再次起事。更為嚴重的是同年在湖北南部的萬餘人的造反。
據報告,實際上國統區所有的省份都有類似的起義——許多就發生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省,遙遠的福建省也有起義。人們悲慘生活的根源通常是徵兵、稅收和強制勞役。因此,起義的攻擊目標自然是政府部門和官員。河南省的饑荒也產生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結果。在1944年,當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一號攻勢下退卻時,河南的農民起而攻擊那些給他們帶來許多痛苦的部隊。他們揮舞著農具、槍和大刀,解除了大約5萬人的部隊的武裝,殺了一些人,有時甚至活埋了一些人。
土匪——中國農村反叛者的傳統的庇護所,用一位在甘肅的美國傳教士的話來說,現在也經歷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高漲”。武裝者、原先的農民、逃避徵兵者和軍隊開小差的,經常是以200一4000人為一夥,劫掠鄉村,威脅老百姓,使公路往來成為冒風險的事,有時並使之中斷。甚至護送的軍隊也常常遇到他們的攻擊。
造反者和土匪大概只佔全部農村人口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農民繼續耕種著他們的土地,服從政府當局,然而,對政府的怨憤正明顯地迴響在全國的鄉村。
國家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在1943年承認,土地稅制中的腐敗正導致農民去造反。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則抱怨人民不理解政府對人力和財力的需要。他說,由於“官民之間的隔閡,以及勒索和騷擾沒有得到充分的查處”,“壞人”利用了人們的不滿製造麻煩。
一位在福建的美國官員約翰·C.卡爾德威爾(JohnC.Caldwell) , 在1944年初報告說“人民的感情和情緒接近沸點”, 他警告說,“人民正不安地騷動”。
美國在中國的一位外交人員在1943年中得出類似的看法,他比較直率地指出,在農村地區的普通民眾中“(國民黨的)威信和影響力也許已經降到了他們的最低點”。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