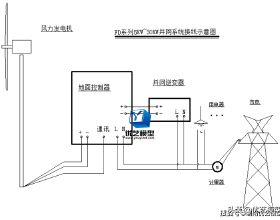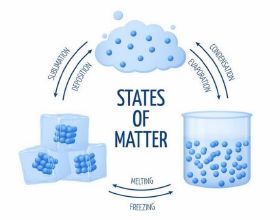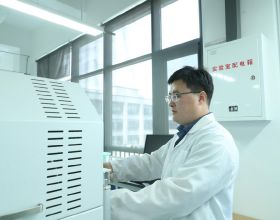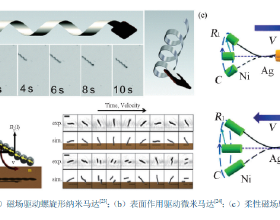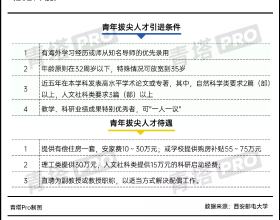無論生活多難,請不要去向往死亡,無論感覺放棄的過程多麼舒適。
終止生命並不會重啟人生,轉回頭看看眾生,哪怕愚蠢而快樂的活著也好。
①
那場事故發生在5年前。
一輛秋遊的大巴翻車,35人罹難,只有一個倖存者,是高筱瑞。
高筱瑞三處骨折,一處比較嚴重的做了手術,另兩處固定了一下。在醫院裡住了一個多月就出院了,回家後,發現不太對勁兒。
以前看門的劉叔看到她的車就放行,這會兒不放行,在崗亭裡眯著眼抽菸看報紙,她爸摁了一聲喇叭,劉叔才慢慢把煙摁滅,走出來伸著脖子朝窗戶裡看,陰陽怪氣地問了一句:“是小高呀,可以出院啦?”
高筱瑞說:“嗯!”
劉叔帶著沒好氣:“我在跟你爸說話。”
奇怪,她爸以前好歹是個領導,什麼時候輪到他喊小高了。
車子緩緩停在樹蔭下。打麻將的,打紙牌的,下棋的,遛狗的,帶娃的,全部停了下來。大家盯死她的車子,看她用什麼樣的姿勢走出來。高筱瑞還拄著根柺杖,走不快。走走停停中,自然碰到誰都得打招呼。可碰到的都是殭屍臉,對方並沒有和她說話的意思。她就這樣經過了最熟悉的一群人,卻又只有她自己。
爸媽住四樓。在她費好大勁兒拐上去的過程中,想明白了一點:
這次秋遊,是她父母單位組織的,每個家庭一個名額,不想去的可以讓給直系親屬。她父母都不大喜歡東跑西顛,正好高筱瑞休假,她就去了。不料一下子死了這麼多人。哪有一個家屬院,一夜間送走三十多人的?
同一個單位,好多內部聯姻,她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都是間接受害者,比如自己家人沒事但兒媳婦的哥是老科長的兒子,走了;半大小夥子的家人沒事,但自己的姑姑走了,如此等等。
高筱瑞在住院期間,最大的感慨是劫後餘生,收到的最多的訊息是“必有後福”。然而回到父母家來,卻看到每個人眼裡熊熊燃燒的,仇恨。
②
高筱瑞對車禍的印象不是很深,只記得自己坐在靠後靠窗的位置,前面是劉伯伯夫妻,劉伯母的名額是他們兒子讓出來的,一路上他們都在講解兒子的孝順,嗓門中氣十足,響如洪鐘。後面坐的是一對小情侶。高筱瑞讀大學起離家,現在工作3年,算起來已經7年不在家裡住,這對小情侶她一時間還沒認出來,聽他倆膩歪才想起是退休了的副局長的孫子和女友。跟高筱瑞坐一起的是同樣落單的徐姨,她有點暈車,要坐裡面,還要開窗戶吹風。她跟高筱瑞說,別看副局長退休多年,還是挺有能耐的,把他孫子的女朋友從一個不著調的單位調過來了,目前是“借調”,過兩年正式手續一辦不就行了麼。還說他給女孩買了一輛飛度,搞笑得很,剛開始女孩要紅的,結果提車那天就跟人撞,老局長迷信,說紅色是出血的顏色,得換色,於是就換了臺黃的。“上班就一步遠,還要什麼車呀。”徐姨說。
好像就是說到這兒,突然一聲巨響,高筱瑞完全失控,她被重重摔到車頂上又摔倒在過道,最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從窗戶裡飛出去的。接著車子跌下山崖,包裹著一路哭喊尖叫。
她回憶不起來疼痛,只記得自己趴在草地上奄奄一息,秋草、泥土和她鼻孔的血流混合,有種銅腥味。她當時的念頭是可能要死了。在那一瞬間她的想法竟然是死就死吧。她並不厭世,很奇怪當時會這樣釋然。略清醒的時候已經有人在施救,她隱約看到消防人員在抬屍體,親眼看到殘肢之後,她真的暈死過去。
③
到家後,高筱瑞問她媽:“這段時間你們回來拿衣服什麼的……他們都這樣嗎?”
“我見著人都躲著走,”她媽說著,轉臉朝她爸抱不滿:“你說咱又不欠他們什麼,怎麼一個個的都這樣。”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她媽這才小心翼翼地問她,為啥就她坐的這個窗戶是開著的,別人的窗戶開不了嗎?高筱瑞想了想,自己真的是隨便坐的,並不知道這個窗戶能開。空調車,確實只有這一處能開,而正巧,徐姨說她暈車要開窗戶。可是徐姨並沒有被甩出來,她也不知道為什麼。難道這也要她去推演一番力學嗎?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高筱瑞也意識到,自己活著成了一種罪過。憑什麼別人都死了就她一個人活著?哪怕一對一半,她也不會如此顯眼。或者只有一個人死了,那麼這個人就成了眾人同情的物件。可是偏偏她活下來了,這個人無論是誰,都會成為靶心。
她爸說,小區原本在全國範圍內籍籍無名,一瞬間成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小區裡每一個人都有離喪之痛,再不沾邊的人也都可以掛得著送禮的邊兒。喪事只好集體操辦,那一天,哭聲如滾雷,大地無聲,草木失色。高筱瑞的父母本來去參加追悼會來著,結果人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他們如坐針氈,還要幫她擋記者,沒等結束就走了。
“每個人的禮都送到位了。”她媽說。
“可是誰願意要你這個禮。”她爸說。
然後兩個人就吵了起來,我們有錯嗎,我們沒有錯。那我們吵什麼呢,我們也不知道。
④
高母不願出門買菜。高父也不願意。兩個人在家唉聲嘆氣。本來女兒死裡逃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卻沒有人高興得起來。高母說:“跟人打招呼吧,怕人家覺得我洋洋得意,不打招呼吧,怕人家覺得我們有罪我們躲著他們。”
這回輪到高父說:“我們有什麼錯。”
然後又是一頓吵。
高筱瑞覺得這日子沒法過了,幸虧她在省會已經按揭一套房子,雖然小了點,也夠三人住了。
“要不然就都搬到我家去住吧。”
父母又吵了一會兒。一人覺得是逃避,另一人覺得逃避就逃避。等另一人想通了,前面一人又覺得是逃避。來來回回,沒完沒了。最後高筱瑞拍板:“就去我那裡住,逃避就逃避,誰還能追殺你們嗎?!”
高母說也是,在這家屬院兒裡住著,如鋒芒在背,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根本沒辦法活著。她是個麻將簍子,以前天天打麻將,現在沒一個牌友喊她,似乎誰喊她誰就是叛徒。這還有什麼意思。
一家人把事情說定,便搬到了高筱瑞家。高筱瑞買的小房子只有50多平方,一室一廳。她爸睡客廳,她跟她媽睡臥室。她媽是個閒不住的人,很快跟鄰居搞熟了,又參與在新的牌桌中。
那一年中老年人朋友圈正興起,人人都愛發些養生諫言或者謠言,諸如西瓜也能傳染艾滋病之類。有天高筱瑞忽然發現她媽發了一條朋友圈,是炫耀打麻將聽啥摸啥,把把胡。
高筱瑞下班回來就說:“你咋發朋友圈了?”
“我憑啥不能發,氣死他們。”
“你還是收斂點吧。”
她媽說:“你劉伯走得算慘吧,胳膊腿兒都乧不攏,他兒子現在不是生龍活虎得很!天天在朋友圈發,炫他的小孩!”
高父想說她幾句,被高筱瑞用眼神制止了。她媽何嘗不是有怨氣,就由著她去吧。再說二老跟了她,將是永遠跟著她,她回頭要結婚生子,還有父母帶,挺好。
⑤
這4年多時間裡高筱瑞談了個男朋友,也到年齡了,差不多便結婚了。
婚後父母跟著搬到她的新家,認真做起了保姆。高筱瑞的老公收入高,與之對應的是特別忙。要說對她不好吧,也談不上,畢竟要忙著掙錢,顧不了那麼多小情小愛。要說對她好吧,也想不起來哪兒好。反正就是過日子,她更多時間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婚後一年備孕,再一年,生了個兒子。
生孩子後高筱瑞並不開心。這股不開心不知道是打哪兒來的,有時候看著孩子睡在旁邊,她覺得很夢幻。這個小不點是自己肚子裡出來的?和自己有血緣關係?她從此就是一個母親?
漲奶,身材走樣,妊娠紋,工作不順,心力不足……她的不高興表現在臉上。
她媽問:“怎麼啦?生個孩子而已,又沒叫你天天搬磚扛瓦,你還有啥不知足的?”
或者:“又不叫你洗又不叫你涮,你咋天天板著個臉?你姥姥生我的時候是在田埂裡生的,生完拿衣服一包繼續幹活。”
再或者:“吃什麼喝什麼都端到你床跟前,你這月子坐得,比哪代人都享福,我的個天老爺耶,現在科技真是發達,洗碗有洗碗機,掃地有掃地機,做飯能定時,暖氣開得比夏天還暖和,這人要是有錢呀,就有了一切。”
若是閨蜜這樣說,還能頂兩句。自己的親媽,頂不了嘴。何況這年代培養不出嘴巴比上代人更刁鑽的女人。高筱瑞有氣發洩不出去,更是窩火。
公婆、朋友、同事,來了都圍著孩子轉:“好可愛呀好漂亮呀。”
誇嬰兒可愛的,大約都是從來沒有抱著嬰兒徹夜不眠過。
⑥
高筱瑞知道自己有點產後抑鬱。她不敢說。因為她沒有理由抑鬱。人人都知道上上個年代的女人可以生七八個孩子,田裡的活一樣不落。她還看見影片裡有的外國人在去醫院的路上就在車裡把孩子生了,生完嘎嘎樂:“a beautiful boy!”
一個夜裡,孩子剛睡著,老公回來,非把孩子抱起來拍合影發朋友圈,配一句話:“跟我像不像?!”
然後他就去回覆後面的一堆馬屁,而高筱瑞哄孩子又哄了一個小時,孩子吃奶吃得她乳頭銳疼。
等她終於可以躺下時,丈夫已經在打鼾。她想睡著,但是她必須等著,等孩子再一次哭醒。
在等待的過程中,很突然地,她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她說她想出去走走。
走到橋上時,她翻了過去。
江水呼喊著:跳下來吧,跳下來就解脫了。
江風微腥,把她衣衫吹得凌亂。只一瞬,她感到莫大的自由。她鬆開了手。在下墜的過程中,她脫離了沉重的肉身。
江水“叭”一聲砸開巨大的水花,很快復歸洶湧。
⑦
高筱瑞死了。父母哭到站不起來。老家的一個鄰居打電話來:“怎麼回事呢,這孩子真是一點不體諒大人,也不為孩子想想,那場車禍就她一個人活下來了,她是代表多少人活下來了啊,她怎麼能這樣呢。”
高父高母終於可以回老家了,雖然這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可所有人終於和他們形成同盟,甚至慷慨地奉獻著更盛大的同情。他們接二連三地登門拜訪,和高父高母一起流淚,他們哭得和當年一樣暗無天日,他們痛斥高筱瑞不懂事……他們好像完全忘記了彼時自己是如何判若兩人。他們在各自的臥室裡也會悄悄感嘆閻王不留倖存者,但是他們出門決不表現出來,他們像被鬼統一了行徑,他們惋惜這個姑娘和這個家庭,他們恨不得主動為二老養老,他們又一次扒開自己的創口真心誠意地慟一慟。
其實高筱瑞在下墜的時候已經記住了他們全體——沒有一個人希望她活得好,在那場車禍發生後,每個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她活得漂亮。她曾經也想興致盎然地活,是自己不爭氣,最後將每個人不曾言說的願望化成了行動。在噩夢中,大巴車承載著生機駛向春天,可突然暗夜來臨,每個人都輕輕推了一把,令她連微小的坎也渡不過去。這看似毫無關聯的兩件事,卻註定讓她生命的每一天都揹著鍋。
她終於被生活滅了口,及時制止了那些親屬絕對無意識的罪惡。
高母老得只剩筋了。她無精打采地坐在門口曬太陽的時候,看到老副局長的另一個孫子開一輛明黃色的車過去。她想起他死去的那個孫子跟高筱瑞差不多大,想起他們本來提的是一臺紅車後來換成了這臺黃車,想起家屬院已經有多年的八卦沒有和女兒說。她靜靜地坐著,60歲的人像90歲一樣遲鈍,她的眼珠從左到右只能挪動一小點便退回來,眼裡蒙了一層白霾。陽光斜刺在高了一大截的小楊樹上,她就與世無爭地坐在那影子裡,小徑人聲鼎沸、喜怒哀樂,都徹底與她無關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