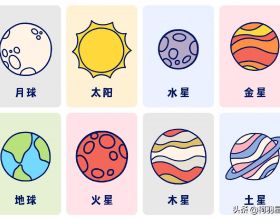真相無人在乎,正義總是缺席。
有人說本片是愛沙尼亞版《白鹿原》,也有人說本片是愛沙尼亞版《鄉村愛情》。前者史詩感十足,後者多了對生活的調侃。一個曾經正直,忠誠於信仰的人,在貧瘠的土地上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真相與正義的不再重要,荒涼的土地上寫盡了主人公一生的躊躇與落寞,拼到終老,不過如此。
有的人天生就是講故事的高手。常人看來平平無奇的耕種收穫,日常糾紛,在他們的鏡頭下就變得深邃凝練,大氣厚重。沒有大場面,沒有戰爭戲,演員都聚焦在農場和小鎮酒館,卻透著一股史詩般的蒼涼。愛沙尼亞導演塔內爾·託奧姆就是這樣一個人。
作為他的第二部作品,《真相與正義》絲毫沒有新手導演的生澀。編劇兼導演於一身,讓他能更好掌握作品的方方面面,充分體現劇本中的細節與韻味。
年輕的富農安德烈與妻子來到貧瘠的鄉下購置土地,開始生活。溼冷荒蕪,重新打造,添置農具,聘用農工。陷入泥濘的耕牛,整日疲憊的身體,永遠皺巴巴的衣服,盡顯愛沙尼亞天地不仁的原生態氣質。
社會學上講,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
僅僅靠安德烈與妻子的相互扶持,他們貧瘠的農莊自然不會有起色。所以他們努力融入當地,適應當地,與可接觸的一切人保持良好關係。
除了鄰居佩爾魯。
佩爾魯粗俗野蠻,狡詐成性,為人刻薄,機關算盡。與讀過書,信奉上帝,凡事謙讓有禮的安德烈形成鮮明對比。
從後來的故事發展中,我們看到了佩爾魯想盡辦法噁心鄰居,坑害鄰居,永遠都認為自己對的混張性格。
這一刻,我彷彿看到了鹿子霖,彷彿看到了謝廣坤。
私拆兩家分界牆,說好的合作只顧自己利益,擅自堵住河道把安德烈田產淹沒,設計打死安德里的忠犬。這個動輒打罵老婆,酗酒成性,十里八村出名的惡人,成為了安德里一家的噩夢。
本片發生的時間還不涉及資本與工業革命,所以男耕女織的鄉土社會就顯得閉塞而原始。靠天吃飯,辛勤勞作,保證收成;夫妻恩愛,養育男孩,繼承家業;與人為善,擴大經營,小富即安。這就是主人公安德烈這輩子最渴望的三樁頭等大事。
但老天爺總不會如人所願,尤其是善良的人。
所以安德烈遇到了謝廣坤一樣的好鄰居,天天禍害他的耕地;美麗善良的妻子連續生下幾個女兒,撒手人寰;女兒豆蔻年華,竟然愛上冤家對頭的兒子,宛若《鄉村愛情》裡王小蒙和謝永強一樣。
孽緣,就是孽緣。佟湘玉的話說,我就不應該來到這片土地。。。。。。
導演用油畫般的鏡頭語言講述著屬於本土的故事。
除了安德烈與佩爾魯這對死對頭之外,用一條繩子追到愛情的長工,小鎮法庭上的爭辯、酒館裡的拌嘴,第二任妻子與前任妻子的協定等等,都細膩表達著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人和事。
生存下去,繁衍後代,擁有工作,養活家人,這裡的人就像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在相對落後的環境中秉承了一代代人的生活慣性,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
讀過書明事理的安德烈,從不願意爭執到開始爭執,從消極對抗到主動出擊,他所堅持的真相與正義似乎對農莊之外的人沒有任何觸動。荒蠻的大環境下自己的生存才是唯一,真相與正義不過是大家眼裡的好戲。
影片從原始的生存境況,上升至真相與正義的堅持。又從安德烈背棄信仰,成為自己最討厭的那個人開始,再次迴歸到生產境況。物質到現實,現實到物質,兩者的轉化,不由得讓觀眾心生感慨。
形而上的真相與正義在時間面前變得不那麼重要,而最平常最俗的生存與鬥爭才是牽絆人一輩子的事。貌似並不大的鄰里糾紛,卻能折騰主人公一生,甚至改變他的初衷和堅持。
幾十年之後,安德烈不再較真了。他放棄了真相與正義。迴歸到一個俗不可耐,又無比現實的人。其實今天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明知道這事不對,那事不公,可有幾個人會較真呢?書本上教育我們要堅持真理,秉持道德,遵守法制,與人為善。可當真理受到挑釁,道德遭遇危機,法制被人踐踏,善良不再重要時,社會的進步難道真的只能體現在科技發展與物質豐饒這兩個方面麼?
佩爾魯的無情冷酷,奸詐陰險,只換來眾人的敬而遠之,背後嘲笑。安德烈的堅持道德,忠誠信仰,卻屢屢遭受重創,除了酒館中靠調侃討回嘴上的便宜,他那份難過只有自己明白。
這世上真沒有感同身受。
影片中安德烈這樣試圖與對方論理,但最後被現實逼瘋的例子今天仍舊比比皆是。武漢老太太天天噁心居民,逼得對方自殺,她無非搬家,能把她怎樣?大街上被扶老者冤枉扶助之人,好心人含恨而死,老者無非一句“我沒想到”就此結束。
類似的事不是一件兩件,而是層出不窮。
社會大眾的道德譴責在流氓面前統統無效,惡人仗著自己年齡、身份、地位等特情況往往有恃無恐。更何況惡人總是很有心機,能夠讓事件走向在法律監管範圍之外徘徊。就算當事人訴諸法律也往往束手無策。加之事件外的我們都是看客,既無權利去管,又不能把自己的時間精力成本放在對某件事上面深究。最終作惡之人往往能夠逃脫一切制裁,受害者只能認倒黴。
《真相與正義》片尾,安德烈放棄了道德與信仰,開始以猙獰的面目對待女兒和眾人,社會用無窮的雙手把他摧殘夠嗆,進而讓他成為他曾經最最討厭的那個人。
《鄉村愛情》裡,王老七可以用鐵鍬教育謝廣坤。《白鹿原》裡,老天爺收了陰險的鹿子霖。而本片中,安德烈最多隻對付死對頭的狗,而他自己以及所有愛沙尼亞人,都被老天爺教育了。
天地不仁,真相與正義說重要也重要,說不重要屁都不是。現實中心中毫無道德約束,法制也奈何不了的惡人往往是真正的贏家。好人只能寄希望於“蒼天有眼”這樣虛妄的字眼安撫不甘的自己。
久而久之,這種真相無人在乎,正義永遠缺席的不堪,都是以犧牲社會正確導向為代價,加速了人心的異化,道德的淪亡。所以什麼老賴啊,流氓啊,為虎作倀的混蛋屢禁不止,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愛沙尼亞不會記住安德烈有多憋屈,我們卻從安德烈身上看到了太多長久以來社會的通病,與他共同見證了人類進步過程中的永遠無法剔除的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