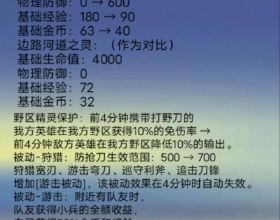28歲那年,Jody Smith突然意識到,自己總有一天會死去。
死亡,每個人類都會經歷的事情,從那一刻起成為Jody的心頭病。
可能是因為父親和兄弟在他年輕時去世一事的影響,也可能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壓力與感觸,在本來就已經患病的情況下,“怕死”進一步演變成了心理上的問題。
對“死亡”這件事,他變得異常恐懼。
恐懼並不是毫無前兆,26歲時,他已經被診斷出癲癇症。
每天大概有3次,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他會經歷短暫而強烈的情緒感受,感覺好像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
有時候,症狀會比想象中嚴重得多。
最嚴重的一次,他在一次家庭聚會上走到外面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然後昏了過去。二十分鐘後他醒過來,發現自己像喝醉了一樣,在鄰居的院子裡跌跌撞撞。
症狀引發了恐慌,喚醒了腦中的恐懼感。
從最初發現異常再到確診,經過兩年的嘗試,各種藥物都沒能治癒他的病症。
恐懼也是這時出現的: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懼吞噬了他的思緒,他開始焦慮不安,精神受到嚴重的折磨。
為什麼會這麼害怕死亡?我們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正在被用槍指著腦袋,或者正身處橫屍遍野的殘酷戰場,下一秒身體可能就會被炸到四分五裂...
生物面對致命威脅和即將到來的死亡時,都會產生巨大的恐懼感,這是一種本能上的反應。
Jody的害怕就是這種害怕。不同於我們平時口頭上說的“我怕死”、“我怕從高處摔下去”,Jody的恐懼感就像是已經被槍指住了腦袋,或是已經站在高樓的邊緣搖搖欲墜,下一秒就要直面死亡。
不受控制的恐懼一直瀰漫在腦海。這種確切的、具有實感的死亡恐懼,已經嚴重影響到正常生活。
為了擺脫這種恐懼,他決定接受手術。
經過一系列前期準備之後,Jody的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醫生切除了他大腦右顳葉的前半部分、右杏仁核和右海馬體,然後將他的頭部重新縫合在一起。
手術後三天,他就已經可以出院。
雖然手術造成了諸如注意力缺失、記憶缺陷等問題,但兩個周後,他持久不斷的恐懼就消失了,他終於不再為自己終將死去一事而煩惱。
他的生活恢復到了比較正常的程度,然而,直到手術後一年多,他才意識到自己對恐懼的反應到達了另一個極端。
那天他在街上散步時,遭遇了五位暴徒的圍堵,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將要被搶劫,但卻沒有表現出任何害怕的跡象。
或者說,他的大腦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知道該如何表現出“恐懼”。
回憶起這件事時,他自己都覺得很不可思議:當時他甚至沒有避開正在接近的暴徒,而是漫不經心地徑直走出他們的包圍,場面一度有些滑稽。
搶劫者可能也沒見過這種場面,當場就愣住了,Jody說可能是自己對恐懼感的缺乏打擊到了幾位暴徒。
之後他還遇到過很多類似的場景:在被蜘蛛咬傷後,他沒有本能地把它甩開,腦子好像還在慢慢思考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
他嘗試去之前害怕的場景中測試自己內心“勇敢”的極限,嘗試找回那種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雙腿發軟的感覺。
但即使是走到懸崖邊上,自己也只會感覺到緊張,完全沒有任何的害怕。
他這樣描述自己如今的“恐懼感”:原本的那種恐懼,已經變成了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做個類比的話,大腦就像關閉了某個APP推送的手機。
你能正常接收到別的APP的訊息,卻永遠收不到關閉的那款APP的推送。你想嘗試再一次開啟推送,卻發現已經找不到如何設定了。
Jody也跟自己的醫生談過這種奇妙的感覺,但對醫生來說這似乎很正常:右杏仁核的切除確實可能會導致病人不再感到恐懼。
當然,受到影響的只是生物面對死亡、致命危險時的那種害怕。
社會關係、人生思索方面的恐懼則不會受到影響。比如“害怕和某人見面”、“害怕事情做不好”、“害怕遭遇失敗”...這種恐懼感依然存在。
失去恐懼感是否會導致人更容易陷入危險的境地?相關研究指出,雖然對可怕的刺激做出反應一直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生存能力,但對當今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並不是最重要的。
原始人類依賴於對錶明危險的感官刺激做出適當的反應,而對當今社會的成年人來說,身邊大多數威脅都是可以習得的。
當大腦能夠明確指出哪些事情會造成生命危險時,本能的恐懼反應似乎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在Jody身上,這一說法得到了驗證:
他對死亡的焦慮消失了,但他仍然能夠察覺到危險,能有意識地解釋感官資訊,分析情況並弄清楚如何避免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不僅如此,他還說手術後自己變得更加外向、健談,他對輕微的不衛生的東西的厭惡程度也已經減少。
除了一些小的記憶力和注意力問題,他的生活要比之前好太多。
如他所說,
“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更喜歡將思想和心理問題類比為為胃痛,而不是性格缺陷。”
“恐懼的原理比我想象的更為死板,它更像是胃痛或是頭痛,而不是難以捕捉的想法或情緒。”
重塑對恐懼的理解之後,Jody再次掌控了自己的人生。
“消除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對恐懼”,而對Jody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恐懼需要去面對、去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