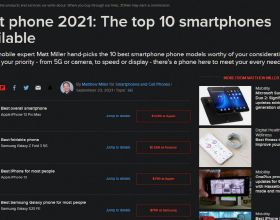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在過去這些年裡成為一個廣受爭論的議題。學術研究者和作家們已經制作了書籍、課程、影片和論文,他們藉此探討這場預期中的革命可能帶來的未來。儘管他們中有些人尋求一種平衡,但也出現了一些過於樂觀的預測,把未來描繪得就像天堂。還有一些預言者警告稱,赫胥黎式的反烏托邦會讓被奴役的人民自願向人工智慧演算法交出他們的自由、政治權利和社會力量,以獲取普遍的基本薪酬。他們預見了一個“後勞動社會”,機器人接管了所有的工作職位,這些工作原本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他們將我們帶到一個世界:一種超增強的新精英人類,用生物技術和奈米技術實現了對人類未來和生命本身無可置疑的操控。
生物學研究在過去數十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只改變了醫學,而且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開啟了一場深遠的科學文化變革。各門科學在生物學中的融合,是對當今科學正規化下無法跨越的主要障礙做出的反應,同時也是在應對技術進步提速的需求。不過,生物學融入物理王國,同樣也是我們作為人類而言視角的重新定位,並促使我們正視生存的意義,以及我們與宇宙自身執行規律的關係。這些變化帶來的最為重要的一些結果,還沒有在大多數有關技術的公共爭論中得到討論,主要是因為科學家還沒有特別積極地思考這些問題。
可以讓科學家用數學描述生物現象的工具出現,讓開發新型工程能力變成可能,這會帶來一個全新的場景。從積極的一面看,這會促成前所未有的技術與醫學進步;從消極的一面看,這可能會帶來我們生物本身的商品化,在窮人和富人之間造成更深的鴻溝。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作為科學家還是作為人類而言, 我們都渴望新的文化敘事邏輯為我們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帶來新的深度與意義,同時也將我們對技術的應用導向人類進步與提高的未來,而不是高科技的大動亂。
《奈米與生命:奈米技術如何重塑醫學和生物學的未來》,[西]索尼婭·孔特拉 著,孫亞飛 譯,鸚鵡螺丨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0月版。
科學家為新的技術文化而努力
全球化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得以應用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同樣也改變了科學家進行研究的方式,並促使他們以更具協作性的方式融入自己的工作及社會環境。有三個趨勢說明了科學家如何對新技術文化的建立做出貢獻,這將會讓各種科學慎重行事並關注它們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
首先,科學家在預測他們所開發的技術有什麼風險方面處在前哨的位置。實際上,奈米技術科學家作為一個群體,首先擁抱了這個承諾,並且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直在“負責任研究與創新”(RRI)日程裡走在前列。他們的科學與技術擁有強大的潛力,這讓奈米科學家非常關心有益的可能性,但同時也擔心錯誤使用或管理帶來的可能性。奈米科學家開創了技術的可持續發展,並在科學程序中納入負責任的原則。他們透過與社會科學家合作來完成這一點,並透過遊說諸如歐盟這樣的機構以獲取基金,從而解決在科學日常活動中執行RRI的實際問題。
第一個RRI專案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RRI原則目前已經整合到了歐盟支援的科研專案中,強調5個觀點:公眾參與、研究成果分享(線上提供,可以免費或設定其他門檻,也就是現在所熟知的“開放存取”)、性別平等(在研究團隊與受研究人群的組成方面,以及在工作可能帶來的影響方面)、倫理道德,還有科學教育。奈米科學家並不是等著監管者去禁用那些已經造成損失的產品,而是離開象牙塔,積極地和公眾、政治家以及監管機構達成合作,討論潛在風險(例如,毒性及環境毒性)。像Matter這樣的非政府組織擅長與學術圈、公司、國際組織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建立合作關係,從而指導技術去實現更可持續、更具社會責任的創新,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好處。各個中心、專案、監管框架以及撥款,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負責任的科學家推動的,並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來,以確保新的技術會將科學、監管、可持續發展以及管理整合在一起,其中也包括公平問題。很多這樣的工作是從奈米技術中心開始的,其他領域(例如新興的人工智慧研究群體)也可以從奈米科學家的努力中學到很多有關自我調控的經驗。
除了在學術機構工作,科技工作者也發現,越來越難參與那些可以被用來反對民主、公眾與人權的技術。2017年,主流媒體開始報道科技工作者聯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的專題新聞,以及在技術應用引起嚴重道德問題的事件中,他們成功地推動美國科技企業傾聽工人意見的積極主義行動。科技工作者的積極主義,迫使谷歌公司在2018年放棄了向美國國防部提供監控技術的“Maven”專案。科技工作者還在領導一場戰役,反對微軟公司與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的合作,特別是在反映兒童與其父母於美墨邊境骨肉分離的震撼照片被公之於眾以後。
第二個趨勢是公民科學專案的激增。再加上其他領域的創新方案,比如“星系動物園”,他們正和全世界數十萬參與者,在一個此前從未實現的高度上進行學術科研的聯絡。在公民科學專案中,公眾並不只是在計算機上積累必要算力以解決極度困難的問題,從而貢獻時間與運算能力;他們也被鼓勵參與真實的程序以解決科學問題,瞭解科學並與學術圈接觸,乃至成為科學出版物的共同作者。
大量聚集在業餘科學實驗室裡進行實驗的團隊也在激增。
DIYbio.org科研團隊在2008年成立,力圖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富有成效且安全的DIY(自己動手)生物學家團隊”,其使命的核心是堅信生物技術與更廣泛的公眾認知有可能讓每個人受益。
DIYbio.org已經在全世界建立起超過100 個本土團隊,並組織日常的課程、研討會與會議。一家叫“氨基實驗室”(Amino Labs)的公司為業餘科學家提供了工具套件,可用於學習合成生物學的基礎,包括如何提取DNA,以及如何從基因上對細菌進行修飾以合成蛋白質。公民科學家的時代開始了。
或許,所有這些趨勢中最可能帶來的改變,是侵蝕了藝術與技術還有科學之間的界限,這些界限正在從兩邊同時被打破。藝術家與科學家以及技術工程師展開合作。藝術家成了科學家, 科學家成了藝術家。科學與文藝之間這種現代的整合產生了一些作品,越來越多地離開畫廊與研究機構,在一些不尋常的地方尋求和公眾之間的對話,比如街道、醫院、商業中心和酒吧。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它們生根發芽並快速傳播,建立在公眾參與的科學活動的基礎上,例如“肥皂盒科學”(Soapbox Science,以女性科學家為特徵)以及“科學品脫”(Pint of Science),並且經常和公民科學家網路的活動混雜在一起。
一般公眾渴望知道更多,渴望被科學鼓舞,並不在意政治傾向和對社會地位的看法, 而且他們天然認可科學與藝術的同盟。這些活動通常由女性主導,她們有些羞怯,卻又雄心勃勃,希望使之發展成某種隱秘的變革活動。一般在這樣或那樣的背景下,包括髮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女性都將她們的希望寄託於科學與技術,將其作為一條尋求更公平也更有意義的社會的道路。
面對新技術給我們的身體和健康帶來的根本性變化,藝術家和科學家正在對新創作與反思空間的需求做出反應。英國的藝術家索菲耶·萊頓就是一個例子,她開發出藝術品幫助病人和醫生理解醫院裡出現的一些新技術。2016 年,透過將科學、藝術、病患護理和醫學進行融合,她在倫敦的大奧蒙德街醫院建立了一個名為“顯微鏡下”(Under the Microscope)的專案。她的藝術品在與醫師以及研究人員合作的工作室中誕生,她的專案正是基於此去探索兒童及其家長如何理解疾病,還有他們所接受的那些複雜的現代療法。
將新的醫療科學帶給病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管是理解還是塑造新技術的用途都需要新的方法。馬克·阿克利還在為23andMe公司服務的時候就建立了“DNA 韻律”(DNA Melody)公司——23andMe是一家致力於幫助顧客透過分析唾液中的DNA 研究他們的血統的公司。阿克利透過使用不同的節奏、音高、音色與音調,將基因轉化為韻律,從而把DNA片段寫成了樂譜。
這些作品試圖讓我們做好準備,同時也將技術準備好為我們服務,它們不只採取了以經濟為中心的方式,也能促進積極的文化進步。它們致力於探索技術給我們的身份、健康、身體、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我們對於現實的認知帶來的改變。這種活動反映了我們對藝術的自然追求,而藝術是一種理解並創造敘事、隱喻和文化的方式,這會讓我們對自身的命運以及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形成更有建設性也更積極的控制。
電影《別讓我走》(2010)劇照。
我們需要藝術以便將現代世界與我們的傳統、文化以及神話聯絡起來,在歷史中搭建我們的空間,創造一種屬於未來的集體意識。實際上,要想駕馭、重塑、理解技術,乃至用我們共有的人性與歷史價值觀去賦予技術意義,用我們不斷演進的身份去促成科學融合,從而預測並減輕它的威脅,藝術是最好的辦法。
所有這些趨勢都有一個潛在的主題:推動科學家去讓科學實現民主化,去建立與公眾合作的平臺及框架,共同為我們所有人設想更好、更多元也更平等的未來。
技術與平等能夠相互促進,也理應如此
驅動科學家更深入地和社會接觸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是技術在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世界裡帶來的影響;況且,對技術的文化感知就是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正如大多數經濟利益的來源一樣,科學技術帶來的獎勵與收益在我們的社會中是不平衡的。大多數對技術的西方敘事都是它所創造的驚喜、給我們生活帶來的震動,以及對於失業及人員冗餘的恐懼。這種敘事也是從事實中提煉而來,因為技術已經被主要用來控制與開發自然。
如今,我們能毫不意外地預見到,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在讓弱者(以及那些並沒有那麼弱的人)在社會和經濟上變得無足輕重,或者更糟糕的是,讓他們成為一種“飼料”,用於人類生物學本身的反烏托邦式開發。科學技術給了我們提升生活的承諾,同時也消除了大多數人對技術應用與開發僅剩的那一絲“為我所用”的感覺。
科學技術帶給我們的可能性,也許會讓21 世紀成為最好也最讓人興奮的時代,生命因此變得充滿活力——但只是對極少數能夠從中獲益的人而言: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關係優越的,有權有勢的,當然還有富人。收入以及獲得保健與教育機會方面的不平等性,正嚴重威脅著我們這個時代的無數可能性。世界各地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日益感到,如果技術帶來的收益不能被更平均地分享,那麼人類“固有富足”的未來將不會實現。
然而,技術並不是作用於社會的外力。技術的應用,源於科學家、技術工程師、研究基金資助者、監管者、工人、消費者,最後還有生產資料的使用者與擁有者所制定的條件與決策。社會可以決定技術收益的使用與公平分配。如果使用機器人可以為它們的“僱主”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與更高的收益,機器人就會造成失業,但這並不是唯一可能的結果。它們也可以被用來讓我們的生活更舒適,更公平。就像我在幾個案例中簡單說過的那樣,科學家正在更為積極地與社會交流,不只是去創造經濟上的收益,同時也在創造文化價值的收益。技術上的變化可以也應當透過可能性與期望值之間的對話進行調節,而科學家不應該被排除在這一對話以外。
我想說的是,技術與平等能夠相互促進,也理應如此。我們需要政策的創造力,以實現更有預見性和適應力的管理,確保科學技術會被用於減少不平等,而不是成為新的不平等來源。相應地,這樣的管理也需要科學技術將其變為現實。
從我作為一名女性、母親、物理學家與教育工作者的視角來看,觀點是很清晰的:潛力無限。在實驗室裡,我們在奈米技術與生物學結合方面的研究具有國際化與多學科的特徵,這讓所有背景的男女學生都能夠增強他們在科學技術上的創造力,以及他們在社會與工業上的企業家精神。因生物學與奈米技術結合而出現的新材料科學,其很多應用可能都是成本低廉的,而且很容易實現,只需要最少的實驗室基礎設施。在正確的框架下,新技術可以成為減少國家內與國家間不平等的一股全球性作用力。我們應當擁抱這種可能性。
奈米技術科學家已經致力於讓科學工具民主化,以創造可以被全世界的人類使用的、更便宜也更簡單的技術,比如紙帶上的生物感測裝置。這些都是“樸素設計技術”的例子:2009年在劍橋大學成立的樹莓派基金會創造了售價大約35美元的“樹莓派”電腦,已經銷售了1000萬臺;2017年, 媒體釋出了“20美分的紙質離心機”(Paperfuge)的照片,這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工程師用紙張研製的一種離心機,能夠利用陀螺玩具的原理分離血液的各種成分;還有一個案例是摺疊顯微鏡(Foldscope),這是一種用紙疊起來的顯微鏡,成本低於1美元。更好地控制物質,自然會激發人類的本能,製造更便宜也更親民的技術。
與學者和媒體對我們的大部分評論相反,技術本身透過讓產品更優質、更價廉、更易獲取,並啟發科學家追求簡單實用化,自然地促進了平等。需要在政治和經濟上有意識地施加影響,才能構建並維持這種從技術中產生不平等的結構,而不是反過來。
技術的種子已經埋下,它有可能開啟一場成功的變革性創業浪潮。學生們被擾亂經濟體系的機會所吸引,因為這種經濟體系不會給他們提供光明的未來。他們要用技術讓他們的世界變得更好,這不只發生在波士頓、矽谷或牛津。技術可以成為一種解決很多本土問題的實用辦法,不只是在發達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寄望於此。
圍繞生物學的科學融合,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例如,很多亞洲國家(除日本外)並不具備強大的製藥工業,它們都很看好發展醫療技術以突破現狀的可能性。它們預見到在技術上發展甚至稱霸全球的可能性,這將會重塑未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韓國、中國、新加坡等),生物醫藥相關的物理學、工程學、材料科學專案的科研經費,也清晰地反映出這一點。
西方世界對技術的恐懼,還有對未來強烈的悲觀看法,不是正反映了有錢有勢的人擔心在這樣的世界裡失去他們的特權地位,甚至是西方社會對失去文化與經濟霸權的恐懼嗎?難道這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遊戲嗎?那些認為自己有權制造並應用技術的人,同時也在製造著恐懼,以實現對技術的控制,並防止其被濫用。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在縮減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與合作的經費,這可能會威脅到一些主要的工業國家在未來技術中的主導權,上述矛盾的狀況是否強化了當前這一趨勢?
電影《第六日》(2000)劇照。
儘管質詢並調整諸如人工智慧、機器人、生物學及奈米技術之類的技術肯定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但是對於那些主導市場的大公司來說,新技術的很多產品和應用毫無疑問是破壞性的,威脅了它們現有的經濟可持續性與增長性模型,而且是在它們傳統控制區域以外的地方發展出來的。這些公司有能力透過有效地遊說政府,對那些挑戰其控制力的研究與開發踩上一腳剎車。媒體和娛樂工業可以透過創造敘事,讓公眾產生疏離感與挫敗感,使他們反對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專家形成的精英階層,從而轉移他們對實際權力鬥爭的注意力。對技術的恐懼常被用作政治和經濟武器,其威力不亞於技術本身。
創造積極技術未來的願景
如上所述,對於一種也許很快就有能力破壞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術,人們的恐懼與日俱增,而科學家、藝術家與民眾關於這種能力應當如何被控制以創造更好世界——一個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義的世界——的零星嘗試,與這種恐懼共存。
在這個複雜的場景中,我們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懼與努力, 正在奮力孕育出讓我們得以生存的新文化。對於我們有可能定居的未來,我們該如何構建敘事與願景?我們該如何設想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這樣我們就能夠朝著它的實現努力?
西方社會對技術的恐懼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正如瑪麗·雪萊在其著作《弗蘭肯斯坦》(1918 年出版,雪萊時年20 歲)中精彩總結的那樣,出現在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蘊含的苦澀在很多西方人的心裡刻下了很深的與技術有關的傷疤,後來喬治·奧威爾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在預測未來的學術新作品,以及無數反烏托邦未來的文化表現形式中,這些源於盎格魯中心經驗主義的敘事仍然很流行。
其他西方國家對技術具有非常不同的經驗。在我的祖國西班牙,無論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對技術充滿厚愛;無論主人的社會出身如何,屋頂上的一片太陽能板都會被驕傲地展示,作為解放現代化的一種標誌。然而,讓我震驚的是,我經常在英國的農村地區聽到,人們認為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看起來是“可怕的現代化”,覺得它破壞“鄉村生活”的體驗。這不只是出於審美的原因,更是出於對技術的厭惡。英語作為一種全球性語言,對文化和學術寫作擁有主導權,它傳播了一種很特別的看待技術的態度——這由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演化而來。如今,這種負面的觀點又與“不穩定”的文化基因以及大部分存量就業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心態形成共鳴。這種負面預測帶來的問題是我們對未來沒有準備,如果對於我們想要的東西沒有願景,用任何辦法都不能塑造未來。
在那些將科學視為福祉來源的國度裡,社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大為不同。日本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巧妙地駕馭了複雜的地緣政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要歸功於基於技術發展的增長策略,還有可以忽略不計的失業率,以及在工人(大多數是男性)及其家庭中對財富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技術被認為是一種通向更好未來的推動力, 這種思潮不是隻出現在日本,而是在東亞地區普遍擴散。許多現代的流行文化都相信未來人類、自然與技術將和諧地融合在一起,日本的小說中也很少會出現弗蘭肯斯坦式的角色。
儘管當前的日本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和創新的停滯,這源於對移民、性別不平等與極低出生率的恐懼,但其國民對於積極轉型的期望仍然與技術交織在一起。我想和讀者們分享一個來自日本的案例,它是一種進步的、富於創造性的推動力,發現了利用技術產生積極文化的方法。這個榜樣也許能夠啟發我們,讓我們思考自己對未來的願景與夢想,那是一個我們為自己索求的未來。
2001 年,當豬子壽之從東京大學數學工程與資訊物理系畢業時,他建立了teamLab公司。“科技改變世界,藝術改變人類思想……與價值”,這句箴言讓他著迷,於是他致力於創造數字藝術,“為當代社會提供另一種生活方式”。他的夢想是和朋友們一起生活並創作,於是他建立了teamLab。如今,teamLab已經成為擁有數百名“超技術專家”的社團,包括程式設計師、工程師、數學家、建築師、計算機圖形動畫師以及其他專家,他們在位於東京市中心的辦公室裡一起工作,共同從事商業和藝術運作。
轉折點發生在2011 年。這一年,藝術家村上隆邀請teamLab 在中國臺北的Kakai Kiki 畫廊舉辦了一場名為“生命!”的展覽。自那之後,這逐漸成為一種全球現象。teamLab用古代日本的敘事與藝術理念,融合了藝術、技術與自然界。他們利用壯觀的大型裝置,以沉浸和互動的方式打動觀眾,直面傳統思維,同時又紮根在日本古典藝術與傳統作品的理智觀點中。“我要和那些想要進入新世界的人站在一起,”豬子說,“那些有創造力的人,那些想要改變世界的人,是我希望啟發並影響的人。”過去的兩年對於teamLab來說是非常高產的一段時間,它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非常受歡迎的展覽。我熱情地邀請讀者訪問它的網站,如果有機會,還可以參觀一次它的展覽,成為它的觀眾合作伙伴,共同創造體驗。
teamLab的作品回應了技術引起的不連貫感和矛盾感——預期與恐懼的混合體,還有我們的歷史、社會與經濟狀況所帶來的厄運感,以及“只要我們把正確的部分放在合適的位置就能創造美好與歡樂”的願景,它們全都交織在一起。在我們迷茫的當下,teamLab將藝術視野與尖端技術融合,展現了一種美,讓我們擁抱人類作為技術物種時代的來臨。
本文選自《奈米與生命:奈米技術如何重塑醫學和生物學的未來》,較原文有刪節修改,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西] 索尼婭·孔特拉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婷
導語校對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