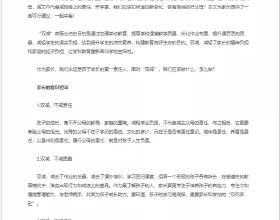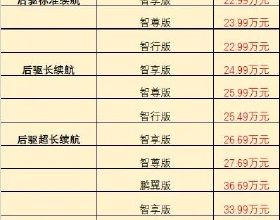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女子被排斥於學校之外。而在近代婦女史上,對女性生活影響最大的因素,莫過於新式女子教育。那麼,晚清時期北京的女子教育是什麼樣的狀況?作為當權者的慈禧太后又起到了什麼作用?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中的《“貴胄女學堂”與晚清北京女子教育》一文,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 | 黃湘金
摘編 | 何也
《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夏曉虹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1
戊戌之後的女學氛圍
在近代婦女史上,對女性生活影響最大的因素,莫過於新式女子教育。今天學者一般將1898年建立的“中國女學會書塾”(又稱“中國女學堂”、“經正女學”)視為國人自辦的社會化女子教育的起點。作為維新運動的產物,“中國女學會書塾”亦因政治鬥爭而終:1900年,經元善通電反對“己亥立儲”,遭清廷通緝,逃亡海外,女學堂主事無人,只得關閉。此後新式女學的命運,成為晚清士人關注女性問題時的重點。
可以確定的是,新式女子教育並沒有隨曇花一現的“中國女學會書塾”而終止。經元善在1902年的演說中便引用佛偈,對此前提倡、主持女學的同道予以“播種者”的身份追認,認為當年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對後來者的跟進,他非常樂觀。而此年《大公報》對女學堂在南方四處開花的描繪,更讓人興奮:“南方通商口岸,自上海開通女學後,經蓮珊太守首倡捐建女學堂之議,自是而蘇而浙、而無錫、而武昌相繼踵起,又膨月張而至於湘粵。女子無不發憤自強,日以講學為事。”現今礙於所見,文中提到的各女學堂之情狀已難考索。
目前可知的在“中國女學會書塾”之後、“癸卯學制”頒行前創辦的女學,較著名的有蘭陵女學(蘇州,1901)、嚴氏女塾(天津,1902)、務本女學(上海,1902)、愛國女學(上海,1902)、城東女學(上海,1903)、宗孟女學(上海,1903)、湖南第一女學堂(長沙,1903)等,多由士紳自發自為倡建。民間有志興學而持觀望態度者當不在少數,則此時政府上層對於女學堂之態度至為重要。而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女學堂的普及情況對全國也具有表率意義。
2
慈禧與“毓坤會”
1902年的北京,僅有教會女校貝滿女學堂、長老會女校、慕貞女書院,並無自辦女學堂。當年曾有滿族官員稟請慶親王奕劻設立八旗女學堂,“慶邸然之。後以見阻於八旗各都統,遂罷是議”。這是我所見到的關於國人在北京自辦女學的最早報導。今天看來,北京風氣遠不如南方開化,京中官員反需借上海出版的《女報》來改變其對“開女智、興女學”的成見。
也是在同一年,《大公報》刊登熱心讀者的白話來稿,建議自上而下推廣女學:太后先在宮中創設女學堂,再明降諭旨,令京中王公大臣、各省文武官員,每家設立女學。不出五年,風氣必然大開,女學堂遍及全國。在此文中,最讓我留意的是對宮廷女學堂的設想:
皇太后先在宮裡,立一座女學堂,考選幾位中國女教習。也不必炫異矜奇,只要通文識字、舉止安詳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學,就求隨時振作鼓勵著點,那風氣自然就開的快了。宮裡的宮娥秀女,共有若干名,開一個清冊,分為幾班,除去當差侍奉的時候,得工夫就按班入學。
就晚清女子教育的實踐來看,地方開明士紳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因而此文對興女學路徑的想象顯得不合實際。不過,作者將推廣女學的起點定位於慈禧太后,也並非全無因由。就現在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慈禧對女報、女學等時新潮流,是以一個開明者的形象出現的。如《大公報》稱由於京官轉呈,慈禧在宮中能夠讀到在上海出版的陳擷芬主編的《女報》(1903年更名為《女學報》)。再加上其自身的性別因素,很容易被設想成為新式女子教育的贊助者、推動者。而《女學報》透露出來的訊息,確實可以坐實這種猜想:
太后為軫念中國女學之不振,乃將平日所覽之《女報》,諭令大公主等各閱一分,並有設立女學堂意,命大公主主其事。俟新建之大學堂工竣,即以現在馬神廟公主府之大學堂作為女學堂。八旗中有志入學者,準來堂肄習。此事原因,實由去年日本內田公使夫人力陳東洋女學之興,故有感慈意雲。
報導中的公使夫人即日本駐華大使內田康哉妻子內田政子,與慈禧關係親密。1902年8月17日日本《報知新聞》曾稱:“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大約1902年慈禧在接見內田政子時,對方談及日本女學之盛,引起了慈禧對於國內女學蔽錮的感觸,因而有意在京城興建女學堂,收錄八旗女子入學,追步日本女學。而在同年,慈禧亦同意了湖北巡撫端方的開女學堂之請,“有飭令鄂省試辦之說”。這當是次年開辦的湖北幼稚園附設女學堂的最早緣起。
至1903年,京城裡已經有了朝廷即將興辦女學堂的傳聞。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總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經回憶,當年內務府大臣誠璋出面請服部宇之吉起草興女學計劃。此舉很可能是出於慈禧的旨意。因為涉及到從日本聘請女教師的問題,這一計劃並未馬上實施。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於京師大學堂校址上建立女學堂的設想並無下文,此處很可能是慈禧心血來潮的衝動。不過,步武日本女學的意趣和視恭親王奕訢長女榮壽公主(即報導中的“大公主”)為女學主事人的安排,已然為後來的“貴胄女學堂”之提議埋下了伏筆。
所謂“貴胄女學堂”,指由皇公貴族開辦,對女性親屬、族裔或秀女、婢女實施教育的學校。宮廷或皇室內的女子教育古已有之,如班昭就曾入宮擔任過後妃的教師,又如宋若昭被唐穆宗封為“尚宮”,“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
但皇室創辦較大規模的學校推行女子教育,在晚清之前未見記載。進入20世紀後,在“興女學”潮流的影響下,先後出現了蒙古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創辦的毓正女學堂與肅親王善耆創辦的和育女學堂。毓正女學堂於1903年12月開辦,1909年停辦。由於地處僻遠,其影響基本僅限於蒙古地區。而據服部宇之吉主編的《北京志》,和育女學堂於1905年開辦。奇怪的是,京城內外的報刊似乎都忽視了該校的存在,就我所見,對此竟無任何記載。彼時被多家報刊跟蹤報導的皇族女學,唯有1905年起倡建的“貴胄女學堂”。而此前倡議的“毓坤會”,則可看作是“貴胄女學堂”興起的先聲。
1904年10月11日,《大公報》刊登了宮廷將設毓坤總學會的訊息:
皇太后命裕朗西之女公子在三海中擇一處開設毓坤文會,並準在外設立分會一節,已見他報。茲據內侍傳說,該文會設在中海,名為“毓坤總學會”,每日講習淺近文法及各國語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晉、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婦、女子均准入總學會聽講。其分會則官紳商民之婦女,凡身家清白,不論已學未學,均可入會聽講云云。果爾,則女學之興盛當不遠也。
1904年初頒行的“癸卯學制”中,唯《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稍帶提及女子教育,但態度十分保守,認為“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其間流弊甚多,斷不相宜”,其意“在於以蒙養院輔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學”。
《大公報》訊息中的“毓坤文會”雖然是學會名義,有人也認為其“僅僅研究語言文字,以備賜宴各國公使夫人之時為之通譯,似於立會之宗旨,猶未窺見其大者也”,但實質顯然是皇族女學,放在其時其地,已算難能可貴。訊息詳細記載了學會創辦人、開設地點、授課內容、學員資格,這都暗示出毓坤文會開辦在即。在“總會”之外設立“分會”、允許民籍婦女入學的設想,顯示出主辦者的宏大氣魄。如能以慈禧為首自上而下地推廣女學,北京女界的沉寂現狀又何愁不能打破?《大公報》難掩興奮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稍後,上海的《時報》對“毓坤會”的訊息進行了後續報導,雲:
探聞近日皇太后因從裕朗西京卿之女公子奏請,擬在南海之內創設女學,賜名毓坤會。凡王公貝勒之福晉、格格,及京員三品以上之命婦、女子均著報名入會,學習東西文。已奉懿旨,特派裕女公子經理其事雲。
毓坤會主辦者和授課內容均沒變動,唯有開辦地點已具體選定了“三海”(南海、北海、中海)中的南海,漢族女性的入學門檻也由“五品命婦”提升至“三品命婦”。課程中開設“各國語言文字”,大異於傳統宮廷女學,頗具有現代意味,其實是與主辦者的個人趣味有關。1903年的《大公報》稱,“裕朗西之女公子,頗得皇太后歡心,不時入內,二人皆衣洋裝”。二人即是容菱(1882-1973)和德菱(1886-1944),通英、法語,曾在清宮中擔任翻譯,頗為慈禧寵愛。而且,在議設毓坤會後不久,容菱、德菱及其母親又擬設八旗女學,“專收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以德菱姊妹主持毓坤會,可謂無二之選。
就在北京女界和報界翹首期盼中,毓坤會卻遲遲未見下文。直到次年初,據《警鐘日報》透露出來的訊息,毓坤會之所以停滯不前,乃是因為慈禧對女學的看法出現了變化:
湖南革命獄始興,學界驟為之暗;上海謀刺案繼起,政界大為之驚。京師則尤甚,有無關係者均視作密切問題。俄使更番警告,聯派黨鹹有戒心。連日樞府與管學大臣互謁密商,頗聳觀德[聽]。各學堂學生驕態銳減,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遊,亦甚寥寥。西后因學堂迭現怪象,意滋不悅。前擬設毓坤會興女學,亦中止矣。
訊息中所涉先後事件,指1903年春開始興起的“拒俄運動”、1904年秋冬在長沙流產的華興會起義以及當年11月上海發生的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前兩事,留日學生和國內新式學堂出身的學生都充當了中堅力量,因而清政府對在校學生的日常活動極為警惕,極易產生過度反應。再加上近臣對當前男女學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動搖了慈禧對於女學的熱忱,毓坤會之事也就意興闌珊了。
1905年5月《大公報》又有“毓坤會”的訊息,但記者語氣已經十分猶疑,在按語中言,“上年即有此等傳說,究竟不知確否”。事實上,德菱在兩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親,離開了清宮。從此在《大公報》上,再無毓坤會的訊息。
3
“貴胄女學堂”考詳
創設毓坤會的倡議就此消歇,但慈禧對女學堂的興趣不久之後又再度高漲,此時不能不提的人物即是端方。1905年7月,端方被任命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之一。在逗留北京期間,利用面見“慈聖”謝恩的機會,端方大力強調女學堂的重要性,頗得慈禧稱允。在致湖北女學生的電報中,他提到自己曾四次晉謁慈禧,“即女學亦經面奏,慈聖亦以為然”。
在兩人的會面中,端方可能還提及皇族女學之事。《大公報》的社論透露,端方“力陳以興辦華族女學校為要”,雖然“群疑眾謗”,但得到了慈禧的支援,“慈聖於此事垂注尤殷,將由內廷撥款,以為天下倡”。稍後的《順天時報》也記載,慈禧對端方之奏請“極為垂意,已飭內務府籌撥經費若干,以為開辦華族女學校之用”。
此華族女學校並未立即興辦,但不久後慈禧授意,“特准將西山旃檀寺改為女學,無論華族編閭皆可就學”。此旨一出,令民間有志入學的女性倍感鼓舞,“太后於今立意,要想倡興女學,正是要使我們中國人要人人發憤,人人好學”。
1905年12月10日晚,《南方報》記者從北京發來電報,稱“兩宮面諭慶邸(按:即慶親王奕劻),仿貴胄學堂例籌辦皇族女學”。可見皇族女學之籌設,前有端方之意見,近則有陸軍貴胄學堂之激刺。慈禧要求仿辦女學,顯有示教育平等之意。而《大公報》1906年初的報導則更加詳細:
聞內廷人云,日前召見軍機大臣時,兩宮垂詢貴胄學堂規模,催飭趕緊開辦。並雲外洋重女學,而中國此等風氣未開,擬俟貴胄學堂辦有成效,再設皇族女學堂,專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入學肄習,以期輸入文明,鹹知愛國等諭云云。
訊息中“專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的學員標準,正與毓坤會一脈相承。另據直隸《教育雜誌》轉錄《津報》的訊息,參與籌辦皇族女學的尚有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夫人、榮壽公主及陸伯英侍郎之夫人等。而訊息所用“貴胄女學堂”的名字,最終為該學堂定名。
在此後關於皇室女學的報道中,慈禧太后一直是最有力的推動者。她在召見學部官員時,便難掩迫切之情:
聞學部尚書曾於日前面奉懿旨,以中國女學尚未發達,亟宜設法推廣,以期家庭教育日漸講求云云。故華族女學之章程近又復提議也。
此條訊息中提及的女學名稱——“華族女學”,較前文中的“皇族女學”略有不同。事實上,“華族女學”即為日本皇室女學之名。1885年11月從日本“學習院”獨立出來的華族女學校,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不久即成為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女子學校,“日本女學校,當以此為翹楚”。華族女學校因此成為中國朝野考察日本教育時必不可少的去處,其學監下田歌子也成為中國女子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清宮倡議皇室女學而擬以“華族女學”名之,可能寓有向其取鏡之意。
更值得關注的是慈禧對端方考察女學報告的反應。1905年12月,端方與戴鴻慈一行出洋考察憲政時,慈禧即命其考察東西洋各國女學,隨時報告。途中學部又奉旨再次電諭其考察女學。1906年4月,《順天時報》有報道,稱:“聞日前端、戴二大臣來有電奏,系陳明美國女學校之章程及一切內容,最為完備,中國女學亟宜仿行。兩宮覽奏,頗為欣悅。現已撥內帑十萬兩,派肅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組織師範女學一所。”
此訊息被多次轉載,影響頗大。《申報》讀者即樂觀地預想此舉之效應:“登高而呼,眾山皆應。女界光明之發現,將普照於中國全境。”聯絡到此前關於皇族女學的報導,在一般讀者看來,慈禧的慷慨很可能是因皇族女學而發。如徐錫麟在寫給黨人的信中,提及“皇太后現捐銀十萬,開貴胄女學堂”,作為其在滿洲人中“可謂通曉時務者”的證據。
次月,慶親王奕劻也有“貴胄女學堂”之奏請,“以便飭令各王府之郡君、格格及滿漢二、三品各大員之女子入學肄業”。而最重要的契機則來自考察憲政歸來的端方。據夏曉虹先生考證,1906年8月13日,慈禧單獨召見歸國不久的端方。端方在召對時,肯定有關於女學數事,因為據幾天後《大公報》報道:“考政大臣端午帥於前日面奏兩宮,請飭學部速立女學堂章程規則,興辦女學,以開風氣。聞已奉旨飭學部妥擬一切矣。”
趁此次朝見機會,端方很可能還遞呈了一份重要奏摺——《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這份由梁啟超捉刀的奏章,其中心議題是:“於京師設立中央女學院,以開全國之風氣,而為各省之模範。”該辦法想必與慈禧此前對於皇族女學的提倡一拍即合,因此很快宮廷中即有“貴胄女學”的訊息傳出:
聞學部人云:本部近日會議設立貴胄女學,所有一切章程均仿照日本華族女學,量為增減。並聞此事之發起,慶邸、澤公及午帥均極贊成,不日當可具摺奏請。
前本報紀端午帥奏請舉辦女學一事,業與榮大軍機商議一切規則,名為貴胄女學堂,其學生以三品以上之大員幼女為合格雲。
經過商議,端方與榮慶最終將其命名為“貴胄女學堂”。以源遠流長的“貴胄”一詞代替“皇族”和“華族”為皇室女學定名,既對應了已經開辦的“陸軍貴胄學堂”,也與日本的“華族女學校”區別開來。關於學生資格,“三品以上之大員幼女”的規定則與前次開設未成之“毓坤會”遙相呼應。
雖然端方對於美國的女學頗有好感,但比較日本和歐美各國的女學情形之後,議設中的貴胄女學堂還是預備借鑑日本的華族女學校。日本華族女學校規模宏大,學制健全,為“天皇及王公大臣,凡華族之女子肄業之所。分為初等小學、高高[等]小學、初等中學、高等中學,凡四科,各三年,以一年為一級,滿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者得入學。”
作為楷模的華族女學校,為擬想中的貴胄女學堂鋪設了美好的前景。而據端方在9月30日外城女學傳習所開學典禮上的演講透露:“皇太后屢次詢及女學,擬開辦一高等之學堂。諸生在此畢業後,即可升入,為皇太后門生,何等體面!”言辭中的“高等女學堂”,因其學生是“皇太后門生”,很可能即指將來的貴胄女學堂——也就是說,預設中的貴胄女學堂除了提供初等教育之外,還會為皇族及平民女子開設高等教育,可見此時慈禧對貴胄女學堂所寄期望之深切。
雖然在朝廷內有慈禧太后、慶親王奕劻和學部尚書榮慶的支援,在地方有端方等大員的倡議,貴胄女學堂的成立卻並不順利。最先遇到的阻力,即來自湖廣總督張之洞。1907年初,他即致電學部,表明他對興辦女學的謹慎態度:“張香帥熱心學務,人所公認。獨於女學雅不謂然,以為中國人民程度尚低,此時倡興女學,未免稍早。聞於日前有電達學部,詳陳此時興辦女學之流弊。未知樞密諸公亦表同情否?”張之洞電文並未直接針對聲勢漸漲的貴胄女學堂,但作為朝廷重臣,其意見不容忽視,此番議論對貴胄女學堂的影響也近乎立竿見影:
聞內廷人云:兩宮每於召見學部堂官時,必垂詢推廣女學辦法,實注意設立貴胄女學之舉。近因某督臣奏陳女學之弊,是以猶疑。日前榮尚書召見時,兩宮與之討論良久,諭以中國風氣尚未大開,欲興女學,必須先訂完善章程,然後再行試辦,逐漸推廣。事宜緩而不宜急,以昭慎重。是以開辦貴胄女學之說已從緩議。
在1906年學部成立之前,張之洞對新式教育相當積極,是倡導改造傳統教育、肯定和推廣新式教育的前驅與重鎮,但在科舉停廢后,面對新、舊學乾坤顛倒的時事,他的辦學方略的主導傾向也從倡行新學轉而為舊學衛道。對於創興女學堂之事,此前的《南方報》稱其“素不注意”。不久之後,慈禧接見某位賢王,問及女學章程和官立女學時,“皇太后黯然不答,恐有不滿意於女學”。
貴胄女學暫緩興辦,可能是慈禧因為張之洞等人的反對而出現了動搖,或是因為朝野輿論而做出的策略性讓步。好在女學堂章程奏定已於時不遠——3月2日,《大公報》登載女學章程“業經議妥,將於開印後入奏”。六天之後,《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正式頒佈實施。而在同一天,《大公報》上刊載的訊息,令關心貴胄女學堂的讀者欣喜不已:
貴胄女學堂事,政府已會同學部妥議,約於春間即可開辦。聞榮壽公主已面奉皇太后慈旨,充當貴胄女學堂總監督。
1904年的癸卯學制中,女學“流弊甚多,斷不相宜”,而此時則認為“女子教育,為國民教育之根基”,“欲求賢母,須有完全之女學”,貴胄女學堂的興辦自是名正言順。
被慈禧指派為總監督的榮壽公主是恭親王奕訢長女,幼年頗得咸豐皇帝喜愛,與志端婚後五年即守寡,長侍於慈禧身邊,“恭謹持正,終身得太后之寵,有時進諫,太后亦多采納之”。有趣的是,類似於容菱、德菱姊妹,榮壽公主對英文亦有興趣。但其任貴胄女學堂總監督一職並未成為定議。不久之後,《申報》刊載訊息,透露此事引起了北洋親貴袁世凱的注意,而他密保推薦的人選,則是京津女界中享有大名的呂碧城。袁氏認為呂“才優品卓,堪充貴胄女學堂總辦之選”。
呂碧城榮膺貴胄女學堂監督之職的最大資本,不為才華出眾,而是她主持北洋女子公學的經歷。北洋女子公學成立於1904年初冬,呂碧城為創始人之一,並主持全校教務。1907年夏,日本國民新聞社社長德富蘇峰參觀天津公立女學堂時,曾對呂碧城大加讚揚。北京報界則稱其為“近日女界中獨一無二的名家”。而且北洋女子公學的學生大多為官宦閨秀,與籌議中的貴胄女學堂性質相似,呂氏自己就曾認為女子公學“有日本華族女學之概”,時人也將其比於華族女學校學監下田歌子。袁世凱對呂碧城的推重,自然不足為奇。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中的《“貴胄女學堂”與晚清北京女子教育》一文,內容有刪減。原文作者:黃湘金;摘編:何也;編輯:青青子;導語部分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