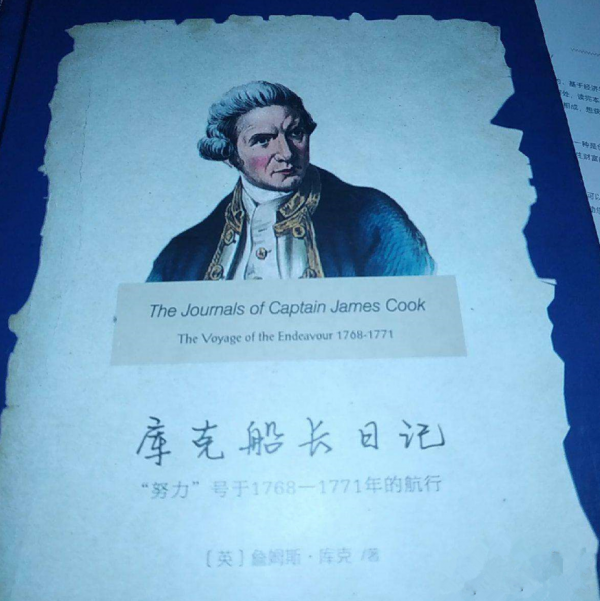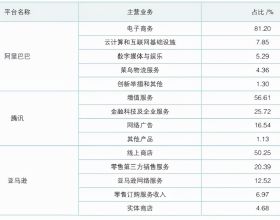說起澳大利亞的起源,在中文網際網路乃至於世界網際網路上,都流傳著一個廣為人知又頗具挖苦意味的段子——這是一個由罪犯所建立的國家。
嚴格來講,這個說法和事實有著些許出入,因為澳大利亞作為獨立主權的“國家”存在是遲至1931年之後的事情,而早在19世紀中葉,英國就已經停止向海外殖民地流放罪犯。
但不可否認的是,澳大利亞作為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和開發,都與英國罪犯流放制度,以及小偷、詐騙犯、殺人犯、造假幣者、愛爾蘭革命分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初的發現
澳大利亞在地理上作為整塊大陸面積廣大,但是因為它的北部海域風高浪急,暗礁叢生,所以長期孤懸海外,並不被舊大陸的人所瞭解。
只是到了大航海時代,歐洲人出於對稱的想象,猜測在地球的南面也會有一塊巨大的陸地,只是這個猜想一直難以得到證實。
即便在1542年的法蘭西王國地圖上,在爪哇島的南方,現在澳大利亞的位置描繪了一大片陸地,但還是很難認為這就是歐洲已經發現澳大利亞的證據,更有可能是臆想和實際的巧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料群島的發現讓歐洲殖民者爭先恐後地趕赴東南亞,積極進行探險和地質勘探活動,這塊巨大大陸在茫茫海洋中的輪廓也就不可避免地變得越發清晰起來。
在16世紀中葉,有多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艦,宣稱自己在太平洋的西南角看到了一塊全新的大陸,其中有一個西班牙船長為之取名為“澳大利亞”,意為“南方的大陸”。
但第一批真正踏上澳大利亞土地進行探險的,既不是葡萄牙也不是西班牙, 而是後來居上的荷蘭。
16世紀中後期,透過艱苦卓絕的鬥爭,荷蘭從西班牙手中獲得獨立,並且躍升為歐洲海上貿易量最大的國家,贏得了“海上馬車伕”的美譽。
同時,荷蘭人趁著葡萄牙被西班牙統治而走向衰落的天賜良機,迅速進入東南亞,很快就在爪哇國建立前進基地,一口氣成立了七個東方貿易公司賺取了鉅額利潤。
支援荷蘭人商業利益的是他們強大海軍與探索精神,他們在17世紀初的海上所向睥睨,而且到處探索,繪製地圖和挖掘航線。
1606年,一艘荷蘭船隻經過託雷斯海峽時,因為要補充補給而首次登陸澳大利亞,之後的數年內,荷蘭人逐漸完成了對澳大利亞西海岸的探索。
同時他們意外發現,如果從非洲好望角直接向東到澳大利亞西海岸,再向北進入東南亞,要比過去從好望角往北沿著亞非大陸海岸線航行快上許多。
這就促使經過澳大利亞的船隻越來越多,所有的歐洲航海家都知道了這裡還有一塊未開發的嶄新大陸。
然而,澳大利亞的發現在之後的半個世紀裡並沒有激起新大陸那樣的殖民浪潮,主要原因是對澳大利亞的探索被認為是“賠本買賣”。
當時主導荷蘭在東方利益的是東印度公司,跟後來英國不一樣的是,荷蘭的這家公司商業屬性更加濃郁,對澳大利亞的探索在當時看起來成本巨大卻不見收益。
大量的沉船事件和被土著幹掉的荷蘭水手讓公司管理層興趣寥寥,他們更願意投入到那些現成的商業模式裡,比如說買賣印度的稻米和中國的絲綢。
即使有少數幾個探險家堅持要求加大對澳大利亞的探索投入,結果只得到了阿姆斯特丹股東們的靈魂拷問:“為什麼要去那些偏僻又無利可得的地方呢?”
還有一封公司高層寄給荷蘭探險家安東尼·範·迪門的信件更是語帶譏諷地指出:
“為公司尋找金銀礦並不是你們的任務······而且老實講,公司已經找到了獲得金銀財寶的途徑,那就是我們在印度洋上的所有貿易。”
澳大利亞就這樣在之後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都被認為是塊貧瘠的化外之地,直到18世紀中葉,一位熱愛寫作的英國船長,透過自己的暢銷遊記作品,才徹底扭轉了這一印象。
庫克船長與澳大利亞
1768年,倫敦的皇家協會向英國海軍申請船隻,要求派人護送前往南半球海洋以觀測“金星凌日”這多年難得一見的天文現象。
英國海軍批准了這一申請,而承擔這次遠航指揮官任務的便是後來鼎鼎大名的“庫克船長”——詹姆斯·庫克。
根據科學計算,金星凌日的最佳觀測點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島,不過對庫克來說,對天文現象的興趣遠不如探索新陸地來得大。
他在1769年6月1日成功完成了護送觀測任務後,就調轉航線往西南方向駛去。
他先是在紐西蘭探險和測繪了半年,然後在1770年決定探索還處於迷霧之中的澳大利亞東岸。
4月20號,庫克的船隻發現了東海岸,30號,庫克和他的船員登陸植物學灣,然後進入了現在的悉尼港。
之後的幾個月裡,庫克沿著海岸一路向北探索,同時他將這片海岸命名為“新南威爾士”。
後來庫克回到了英國,反映他神奇探險見聞的《庫克船長日記》編輯出版,立刻成為了全歐洲的暢銷讀物。
從普通海員到法國國王都被這本著作描繪的傳奇經歷所深深吸引住,庫克的龐大讀者群中還包括了青年拿破崙。
在這本書中,澳大利亞被描繪成了一塊欣欣向榮的土地,庫克寫到:
“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我們用勤勞的雙手將帶來的大部分穀物種植培育,譬如水果、根菜,最後一定會收穫豐碩的果實。這裡一年四季都有取之不盡的草料,即使將所有牛兒趕來也吃不完。”
而除了庫克天花亂墜的描述,促使英國殖民澳大利亞的還有一個重要現實原因,那就是美國獨立。
保皇黨、罪犯和澳大利亞
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好不容易爭取到獨立地位的美國政府立即展開了對國內親英分子和保皇黨的清算,不但沒收財產,而且將他們強制驅逐出境。
成千上萬的人只能逃到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小島上面,還有一些人跟著英軍回到了英國本土,但他們都處境都非常糟糕,沒有了財產,大部分人只能過非常悽苦的日子。
怎麼安置這些因為忠心於英王而陷入如此境地的難民,就成了英國政府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美國獨立導致英國也無法繼續將罪犯流放到美洲。
流放罪犯到殖民地是18世紀以來英國刑罰的慣例,如今美國獨立,本土的犯罪卻不會因此減少,大量等待流放的罪犯塞爆了監獄。
一個誇張的估計是當時有十萬名罪犯被判流放卻無處可去,成了英國政府十分頭疼的一個問題。
一開始,英國想到將這些犯人送去位於非洲的殖民地,然而熱帶氣候讓這些英國的罪犯難以適應,肆虐的瘧疾和熱病等於判了流放者的死刑。
著名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就尖銳地批評道,把罪犯送去非洲還不如直接送上絞刑架,起碼受的折磨還少一些。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提出在庫克所發現的澳大利亞東岸建立安置地,把保皇黨和罪犯都送去那裡。
澳大利亞廣袤富饒的土地足夠他們養活自己,而且還有和印度、中國和日本發展貿易的機會。
這個計劃很快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援,1786年英國在新南威爾士建立的第一塊安置點。
不過跟最開始的設想不一樣的是,這個安置點的首批居民主要是罪犯而不是保皇黨。
因為在英國人看來,讓忠心耿耿的英國公民和犯罪分子享受同一個待遇實在是情何以堪,就像是培根所批評的:“讓人渣和邪惡的罪人成為你的勞動夥伴,是一件可恥不幸的事情。”
首批前往澳大利亞的船隊由英國總督亞瑟·菲利普率領,有11艘船一千多人,刨除了軍人和水手之後,有717人都是罪犯。
他們在1788年1月登陸植物學灣,但出乎意料的是,這裡的土地相當貧瘠並不適合耕種而且滿是沼澤,這讓菲利普大呼上了庫克船長的當。
可人已經距離英國萬里之遙,就此回頭是不可能的事情,眾人只能向北探索。
幸運的是,菲利普等人很快就發現了一處風光綺麗,資源豐富的海灣,這裡綠蔭連綿,擁有定居生存的一切資源,菲利普稱讚這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港灣”,並將之命名為“悉尼”。
英國對澳大利亞的殖民也就由此開始了。
在鞭子和絞索下建設
殖民地開發的最初幾年都一直依賴外界運補物資,如果因為一場風暴讓補給船延期到來,這些殖民者就只能餓肚子。
而且因為首批到達澳大利亞的殖民者中,罪犯的比例是最大的,這就使得他們在監管條件下的勞動積極性很低。
而且菲利普還在報告中抱怨身體健康頭腦靈活的罪犯都留在了英國,送過來的都是一些懶惰且無知的人。
所以他建議應該把自由的權利作為獎勵,授予那些表現積極的罪犯,而且希望英國政府派來更能幹的殖民者,以帶動整個新殖民地的開發。
然而,不只是有能力的一般公民不願意來到荒涼的澳大利亞從頭開始,就連英國的軍隊都不大樂意駐紮這裡。
即便政府以土地作為軍隊定居的獎勵,但新南威爾士的步兵團仍然很不安分,時常爆發騷亂,菲利普之後每一任總督都得處理過這類事件,有一個總督還被軍隊所罷免。
在這樣的情況下,總督們更不敢約束軍人,這使得軍紀越發敗壞,連帶著整個殖民地的風氣也跟著變壞,原本被派來管理犯人的英國軍隊反倒是成為了澳大利亞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另外,因為軍官在朗姆酒的進口和分配上有著職務優勢,他們靠著這一項賺了大筆利潤,並促使了士兵和罪犯沉溺飲酒,酒精氾濫更加重了各種脫序行為的發生。
而光是酒品的生意還不能滿足軍官的胃口,他們開始壟斷其他的商品交易,最後更是直接將手伸向了個人。
大量的罪犯都被安排在了他們的私人土地上進行勞作,英國政府發放的各種補貼也都進了軍官們的腰包。
軍方的權力同樣伸進了法庭,原有的民事法庭幾乎停轉,最重要的裁判權被軍隊拿去,這讓軍官和士兵們更加肆無忌憚地橫行霸道,澳大利亞實際成了一個軍事獨裁的腐敗天堂。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源源不斷的罪犯從英國運往澳大利亞。
這首先是因為當時英國的刑罰在整個歐洲是最為嚴苛的,法官可以隨心所欲地判決重刑犯被流放。
而許多所謂重罪在現在看起來實在荒誕不經,比如無執照賣肉,偷竊牡蠣,在公共場合塗鴉,這些倒黴蛋都跟綁匪和殺人犯一樣被送去了澳大利亞。
除了刑罰過重之外,英國人“奇妙”的商業頭腦也促使大量罪犯被塞進汙濁閉塞的船艙。
當時,承擔運輸任務的船商可以在每個罪犯的人口上得到三十英鎊,這就導致他們拼了命地往船裡塞人,結果就是罪犯的死亡率奇高。
1790年一艘載著502個罪犯的船離開英國,途中死了158人,1799年的另一艘船有300人登船,到達悉尼時已有95人去世,而那些僥倖活下來的犯人,也個個虛弱不堪。
到達了澳大利亞也不意味著從此雨過天晴,上文提到很多罪犯淪為了軍官的農奴,這種現象的根源就就是英國規定。
總督掌握著罪犯的勞動權並擁有其勞動成果,那麼總督將這種權力分配給其他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在這種勞作裡,罪犯所得到的報酬不過是茶葉和菸草,而沒有現金,他們的其他生存需要由殖民當局統一供應,這種生活能達到什麼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殖民地同樣還有針對犯人的刑罰,他們日日夜夜都面臨著鞭子和絞索的威脅,稍不留神就會遭到鞭打甚至付出性命的代價。
愛爾蘭罪犯曾共同發起一次反抗,結果遭到鎮壓後,15個頭目全被吊死,其他人被判鞭刑兩百、五百甚至一千。很多罪犯在中途被打得昏死過去,醒來又立馬被拉去完成剩下的鞭數。
邁向改變的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當局的惡行惡狀最終引起了倫敦政府的注意,尤其是在英國廢除了黑人奴隸制之後,他們也無法接受在澳大利亞的犯人處於另一種的奴隸制中。
1802年之後,英國改為一年兩次由專門的運輸船定期運送罪犯,並在1810年解散了作威作福多年的步兵團,並督促殖民總督進行改革,改善犯人的待遇。
在殖民澳大利亞的前三十年,罪犯能不能重獲自由全憑總督決定,而在1821年之後,總督政府頒佈法令。
一定期限內表現良好便可自動獲得自由公民的身份,即便是被判處終身監禁的重刑犯也可以獲得一定自由權利。
罪犯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甚至有人寫信給遠在英國的未婚妻,要她來澳大利亞結婚並共同生活。
不過,從歷史唯物的角度,真正促使澳大利亞社會改變的根源不在於倫敦和幾個總督的態度,而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最開始因為殖民地開發條件低,人口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澳大利亞連基本的食品都不能自給。
可到了1823年,因為耕地擴大和煤礦開發,殖民地普遍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有人在1826年一次性申請了兩千名罪犯勞動力,讓總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就變得相當珍貴,強制性勞役的生產效率顯然比自由人要低得多,因此罪犯想要重獲自由越來越容易。
這些被釋放的人被稱為“刑滿解教者”,其中一些人成為了牧師、商人、律師、老師乃至於銀行董事,更有幸運兒成為了悉尼的大富翁。
另外,罪犯自身的抗爭也非常重要。
18世紀末,大批參與愛爾蘭起義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亞,這些人能力非凡而且充滿了鬥爭精神,他們很快就把原本一盤散沙的流放犯人們團結在了一塊,並在19世紀初掀起了兩次聲勢浩大的起義運動。
即便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愛爾蘭人堅定的抗爭勁頭還是讓當地的總督和倫敦的政客心有餘悸,徹底廢除罪犯流放制度也就是勢在必行的事情了。
1837年英國議會針對流放制度進行了長達兩年的大辯論,最後在1840年5月決定停止向澳大利亞流放罪犯。
然而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卻想盡辦法延續這一制度,改換各種名目往澳大利亞繼續運送犯人。
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澳大利亞本土的市民社會已經成型,他們迫切地希望拿掉掛在家鄉頭上的這塊“監獄”招牌,更不願意看到罪犯勞動力拉低當地的薪資水平。
所以從墨爾本到悉尼,反對流放制度的呼聲此起彼伏,當地報紙對流放制度口誅筆伐,墨爾本人民更以起義相要挾阻止運輸船入港。
最後在1855年,在經過67年的歷史,流放了十萬人之後,這項充滿著血與淚的殘酷制度在澳大利亞徹底結束。
參考資料
中國知網;試論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建立;王品;200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