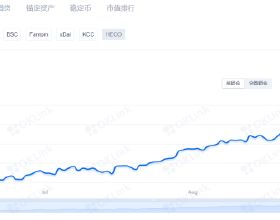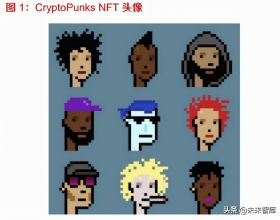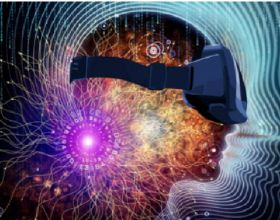從1999年《駭客任務》到2002年《駭客任務:重灌上陣》,再到2003年《駭客任務完結篇:最後戰役》。較於《駭客任務》系列,重啟的《駭客任務:復活》扮演著什麼角色?
2021年《駭客任務:復活》由拉娜華卓斯基獨力執導,電影開始時,基努李維飾演的托馬斯安德森好好地活在某個現實裡。
在這裡,他是一個頂尖的遊戲設計師,因為「駭客任務」線上遊戲大獲成功,主管和母公司催促、緊盯著他設計續集的進度。討人厭的主管是遊戲中史密斯干員的靈感來源,咖啡店巧遇的帥氣人妻是遊戲女主角「崔妮蒂」的原型。托馬斯因精神緊繃痛苦求助心理醫生,過程中一次次閃現似曾相識的畫面,他似乎為自己的作品走火入魔,混淆了現實與虛擬。
尼歐/湯瑪斯安德森、莫斐斯和崔妮蒂的記憶都消失了,他們以全新的身份活在母體中──此刻,有支小隊出動,要扳回應當有的秩序;一群熟悉卻陌生的人,重演無數次的段落,朝向這個曾經存在且依然延展的世界⋯⋯
院線熱映的《蜘蛛人:無家日》以「多重宇宙」的宣稱,將前面幾集一網打盡,所有好人壞人共聚一堂開起大亂鬥派對,在宇宙支線的輻臻點上一起(在湯姆荷蘭所隸屬的宇宙裡)往前再走一點點。但《駭客任務:復活》牽連前面三集的方式,則是另一套邏輯。
對我來說,這次的《駭客任務:復活》並非準備日後進一步擴充出「《駭客任務》宇宙」,而是與之相反的,從後設的角度重新收束、或甚至可說重新終結這個系列。當然,在後設的位置上,每個終結恰恰是新的開啟。
電影裡那個近乎不懷好意、取消又勾連一切的意象,讓人想起尼爾史蒂文森1992年的科幻小說《潰雪》。這部小說中展現了理性所肇致的兩個極端但同時存在的極權與自由社會,曼延的混亂和暴力可以反推回是來自工具理性的影響,但當身處的一切景象都可以用「執行一個計算機程式(所獲得的介面)」來表示,而程式/語言事實上會全新格式化每個人/物件的腦,則我們所在的就是個一切相連結卻漂浮虛無的世界。
尼爾史蒂文森曾認為如「虛擬實境」這類詞彙太笨拙而無法盡其意,他創造了avatar(虛擬化身,也是《阿凡達》片名)和(小說中譯為「魅他域」,也是最近產業熱議的「元宇宙」)這兩個字。
但儘管對這個想象的世界多所批判,《潰雪》中的「魅他域」卻有種出了那裡就不復存在的魅力。如小說中對該時空之自述:
「咒語,一種有魔力的語言。⋯⋯今天人們已不相信有這種東西。除了在魅他域,一處可能還有魔法的地方。這城是由程式碼創造出來的虛擬結構,程式碼也是一種形式語言──電腦瞭解的語言,因此整個城可視為一個巨大的咒語,透過光纖網路不斷將自身表現出來。⋯⋯這是個故事但也是個咒語,是一部自我應驗的小說。」
而這份「當一切都是假的,則置身其中必然全部為真」的拉扯,在史蒂文森的《鑽石年代》更為浸淫。
曾讓影迷沉醉於解謎解密的《駭客任務》三部曲,到了《駭客任務:復活》,那一切卻是被從更高一層往下看的介面;大量插入的前三集畫面回顧、對經典段落的重演所造成的連串déjàvu,並非要召喚影迷回憶,而是在抹消它們,或說是將其降維。
藍藥丸和紅藥丸的選擇已無意義。因為以再後設一層出去的角度看,如果藍藥丸可以幫人深深植入所在的現實,則這段路程也將抵達足以破解這個現實的臨界;而紅藥丸的所謂覺醒,終究會意識到、然後卡在原本被設好的邊界,仍然是個現成的現實──藍紅藥丸只是Möbius strip的迴路入口,無所謂誰才平庸、而何者又是解藥。
簡單地說,《駭客任務:復活》是一部「『關於』《駭客任務》三部曲的電影」,它用這個「關於」去跟三部曲本身進行互動。它既不是前傳、不是後續、也不是番外篇、也不是平行的彼個宇宙,而是:三部曲本身是有邊界的,指出這個邊界,就可以重新再把玩和凝視這個我們原本以為已經通透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