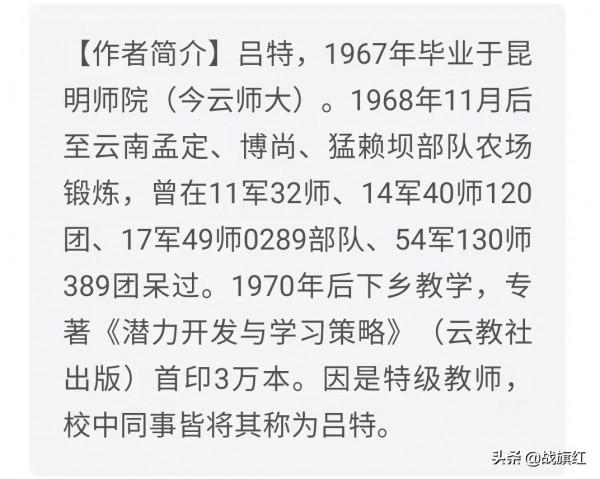大學生連記事45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其意原本是說在固定的軍營裡,每年都有老兵轉業復員退伍走了,又有新兵入營來了,這兵就像流水一樣。但是在特殊的1969年,“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就不再指少數兵員的流動,而是指大部隊浩浩蕩蕩地南來北往,東挺西進的頻繁調動了。
就以眼下我們學生連還住著的博尚軍營為例,頻繁換防的部隊就叫人眼花繚亂。
博尚營房原本是14軍40師所建,120團在完成清剿李彌殘匪任務後,就從1958年初到1968年在博尚駐了10年。
但是在此後的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大部隊的流動就進入新高潮,先後有4個軍的部隊頻繁出入博尚。先是1968年10月14軍到滇南接防的13軍,同時原駐紮在四川西康的54軍調往滇西臨滄接防14軍,11月130師389團來到博尚,40師120團則至玉溪華寧盤溪。
此後未及一年,即1969年11月3日0255部隊(389團)北上去河南,17軍49師在1969年10月18日一號令下發後的第四天,緊急從蒙自到臨滄,該師所屬0289部隊進駐博尚。
同年12月1日,陸軍第11軍在大理成立後,月底0289(17軍49師)部隊又換防至大理州,11軍新建的32師96團亦即0435部隊進駐博尚。我們學生連則劃歸0432部隊(32師)。
一時間,就在博尚這個營區內就有11、14、17、54四個野戰軍的人馬你進我出,我來你往,軍營裡,但見軍號聲聲,哨聲唧唧、戰馬嘶叫,卡車轟鳴,紮實熱鬧了一番。
博尚這營區,佔地面積很廣,一切設施都是按一個團的編制建造的。除了禮堂外,各連宿舍都是清一色平房,連與連之間都有一定的活動空間,房前屋後還有幾塊菜地。營房有序地佈局在四周,大禮堂前有幾塊寬敞的水泥球場。綠化說不上,路兩側的桉樹卻甚為高大挺拔。
其實這博尚鎮說來也很簡單,用四個一便可概括:
一個軍營一條街,一個水庫一條路。
一個軍營不必多說。“一條街”就是博尚街,街算不上長,也就只有200米左右,兩側的房子卻要比孟定街多,設施也比孟定街齊備,而且商店裡的貨物花色品種更是遠比孟定豐富,除糖茶敞開外,鞋襪等日用品也不限購。
“一條路”,就是從水庫與營房間穿過的國道214,又名西景線或滇藏公路(南起景洪,經西藏芒康至青藏界多普瑪)。“一個水庫”,指的就是營房下面的那個水庫。
講風水的人說,這博尚是塊福地,所以部隊把營房建在這裡,其主要依據是博尚“面水靠山”。“靠山”是實,其身後都是緩緩而上的山崗,“面水”卻未必,因為博尚腳下那個中型水庫是1958年大躍進時才興修的,那年頭舉國日夜奮戰,類似的水庫修建了86000座。博尚水庫因源頭有5條河流匯入,庫容很大,水面浩瀚,村民皆沿湖而居,有大群白鷺棲息其間。成了南定河的源頭,既灌溉了農田,又解決了臨滄主城區的生活用水問題。可惜營房和博尚鎮的位置都比水庫高得多,看得見,喝不著,近水不解近渴。當時營區和博尚鎮的生活用水都是從後山深處引下的山泉水,水質上乘,當年就為這水犧牲了一個班的戰士。
博尚後山深處林竹疊翠,有許多箭竹和方竹,心實而皮厚,竹枝紮成的笤帚相當板扎。我們常去砍柴或割竹扎掃帚,途中,在自來水池源頭處豎有一烈士紀念塔,塔上刻寫著的文字大意為:解放初,駐軍和村民飲水困難,部隊特從後山山箐裡埋管將水引下,為防土匪投毒池中,部隊特派一個班去水源處看守,土匪在夜間砍殺了站崗的戰士後,遂將熟睡中全班戰士殺害。碑上刻著犧牲戰士的姓名、籍貫、年齡,大部分戰士都還不到二十!當時我們非常感嘆,就是為這點水,曾經付出了那樣大的犧牲!
在博尚水庫對面有一村子,居然叫“博對門”。1969年11月的一天下午5點左右,博對門突然發生火災,站在營區看得真切,失火的人家就在對面路旁。是時,96團二三十個戰士拎上臉盆衝出營房,我們排也提著水桶向失火處跑去。那“博對門”名副其實,看著就在營房對面,待繞著水庫邊緣跑到那裡竟用了四五十分鐘,終因水火無情而且遠水不解近渴,那村民家剛收回的穀子已全部化為灰燼。那火又甚是兇猛,將石磨都燒裂了。
返回時天已黑定,途中見一戰士攙扶著另一戰士坐在路旁,那戰士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看樣子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是96團的新兵蛋子。那時珍寶島和鐵列克提事件的硝煙未散,核威脅核戰爭一觸即發,全國都在備戰,能夠在1969年入伍的戰士,誰個不是奔著要上戰場去的!單憑這入伍的動機這年輕的戰士就值得敬佩!我們四人輪流揹著他跑了一段,見他的雙手連摟在脖子上的力都沒有,便索性向村民借來一塊門板,四人將他抬著回來。
96團原本是雲南省軍區警衛團,久駐距昆明約20公路的北郊小麥峪,特殊年代與我們學校是對接單位,前兩天在營區見到的x營長等一行,曾在我校搞過支左。這是一支響噹噹的老部隊,據說當年林副曾有一個內部指示,要軍隊的子女下到部隊鍛鍊,他的女兒林曉霖先在54軍並隨部隊來到大理,54軍離開雲南後,林曉霖留在11軍。在博尚的96團裡,據說也有幾個高幹子弟,如當今比較知名的羅援少將就是從這個團出去的。
有道是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為人生的四大喜事。非常巧,我高中二年級時的班長戴崇雲就在這個96團某連當指導員。老鄉,老同學,竟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邂逅相遇,對彼此說來都是件高興的事。自此我常到他們連走動,混熟了,他那些小戰士見了,還將我稱為首長。
他們連常與學生連舉行籃球賽。籃球賽這東西,本是大個欺負小個的遊戲,我們學生連籃球打得好的那幾位個頭都不算矮,見戴崇雲帶著幾位個頭不怎樣的兵來,我道你可別把學生連小瞧了。他不卑不亢道:“待賽了再說。”他那些兵還真厲害,速度、配合、投籃的能力都很強,關鍵是體能好,每時每刻都在跑動,他們很少打陣地戰,幾乎都是快攻,搶到籃板一長傳,就到自己籃下。半場下來,雙方持平。下半場,學生連體力不支,被打了幾個反擊,換了幾次人。當兵的全場下來,幾乎就沒有換過人,依舊那麼快,那身體真是結實,撞上去砰砰直響,就像撞上一堵牆。
學生連以微小的比分輸了,輸得很不服氣,於是擇日再戰,這一次,學生二連的佼佼者悉數出徵,棋逢對手,雙方使出了渾身解數,身體接觸頻繁,對抗近似慘烈,比分交替上升,咬得很緊,以至令人有窒息感。在爭搶籃板球時,雲大化學系一大個動作過大,竟將戴崇雲的牙齒打搖,至今重提舊事,他還憤憤不平。
他們的部隊那時行動詭秘,來無影去無蹤。這場比賽後,我又去他們連走動,整個營房卻是空空如也。本是同居一營的人,竟不知他們何時走了,去了那裡,連個問處都沒有。當時舉國上下都在搞疏散,都在深挖防空洞、防備蘇修對中國的空襲,部隊在一個勁地緊急戰備,不是鑽坑道,就是住在深山老林裡,營房空空蕩蕩實屬正常。
轉眼又是幾個月過去,已經是1970年3月底了,我們再分配的塵埃已定,我特從勐賴壩再返博尚,欲與戴崇雲和他的戰士告別,但營房仍舊空空蕩蕩,是軍人服務社的一熟人指點,方知部隊還住在後山的工事山洞裡。
那後山乃熟悉之地,當即上山,已經走出了很遠,仍不見人影,正納悶彷徨左顧右盼時,忽地從地下鑽出一持槍的戰士。我當即自報家門說明來意,恰好這戰士也知道戴崇雲,他說“首長”已調到團裡了。找到了老戴,經他指點方知道,腳下都是縱橫交錯的工事戰壕,官兵們整個冬天始終吃住在這山間陰暗潮溼的工事裡,已經在野外餐風宿露了好幾個月了,說來真個叫人心酸。
部隊的緊急疏散行動始於1969年10月18日林副的“一號令”,全軍各大單位接到“一號令”後,都不折不扣地進行了堅決貫徹,立馬緊急疏散進入前沿工事。當年林副的這“一號令”在全軍被認認真真地執行了半年之久,引起老人家憤怒的,並非“第一號令”的內容本身,而是發出“第一號令”的林副居然能不經過最高決策者或者與黃總長同在一起辦公的總理知道,就能在一夜之間調動全軍緊急疏散進入臨戰狀態。當然這事說來話就太長了,此處按下不表。
好在,1969年的10、11、12乃至次年1、2月幾個月之內,戰爭並沒有到來。北方部隊裡的一些嗅覺敏銳的人,已從1970年兩報一刊題為《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元旦社論的字裡行間,看出關於戰備工作的論述較之此前的一些提法已經不那麼突出了。也就是說到了1970年的1、2月份,形勢已經明顯地緩和了,看樣子這仗十有八九是打不起來了。
時值隆冬,部隊還凍在野外,官兵們受不了,重型武器裝備也受不了,北方有部隊叫苦不迭,這麼長的時間了,左等右等既不見旨意,又無六部公文叫撤回或者不準撤離的命令,有人竟懷疑上邊是不是把這事給忘了。於是有腦瓜子靈活一點,膽子大一點的部隊主官,便自作主張悄悄班師回營了。據說幾個月後林副知道了上百萬部隊還在野外餐風宿露也覺得奇怪,便問黃總長:部隊可以回營了,為什麼還要繼續疏散呢?黃總長也是語焉不詳。
96團本分質樸,執行命令不打折扣,始終在山間密林中堅持,直待1970年4月春暖花開了,軍委認為部隊再無風餐露宿之必要了,才於24日發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才允許疏散部隊返回營區。而博尚的96團已在野外整整凍了一冬。
【深耕戰爭史,弘揚正能量,歡迎投稿,私信必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