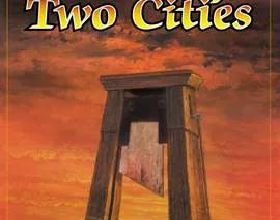“溫一壺月光下酒”,語帶玄機的禪意,醇厚浪漫的意境,中國文人對酒的青睞,真是刻骨銘心。
網上有好事者排出“最愛喝酒的十位大詩人”榜單,按作品中提到酒的詩(詞)句多少,排名榜首的陸游高達1729次,其次是蘇軾738次,隨後是白居易674次,李白213次,最少的杜甫也有183次。雖無從考證,卻足以說明中國文人與酒的淵源。
陸文夫曾歷數酒的好處:“酒可以解憂、助興、催眠、解乏,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活脫脫的“無上妙品”。只是,不知那一壺濁酒成就了多少文人墨客,也不知有多少不朽詩篇對酒之神奇讚美頌揚。
印象中,但凡借酒奮筆疾書者,大多遭逢人生低谷,或仕途不順,或壯志未酬,或悲憤寡歡,故以酒排遣鬱悶,抒發情懷。譬如李白《將進酒》“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聽起來很灑脫,其實是愁得走投無路的自我安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豪情萬丈的曹操生逢亂世,也不得不借酒解憂。
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滿紙豪言壯語,內心卻是生死訣別的悲涼。白居易辭官後寫了一篇自傳,“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迴圈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天席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醉吟先生傳》)。看似超脫,實則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關於酒的喝法,林清玄說:“喝酒是有哲學的,準備許多下酒菜,喝得杯盤狼藉是下乘喝法;幾粒花生米和一盤豆腐乾,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是中乘的喝法;一個人獨斟自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同是喝酒,不同的人終究會喝出不同的人生況味。
我不喝酒,沒有提壺痛飲的資本,更無從體味暢快淋漓的宿醉。可生活中免不了身不由己,即便滴酒不沾,一杯白水相伴,也要等到“聚”終人散。作為看客,見過的喝酒大抵介於“中乘”與“下乘”之間——食客一眾,或知己或同事或故人,或因某種需要集結一處,推杯換盞,海闊天空。末了,杯盤狼藉,各奔東西。酒徒酒鬼從未見過,倒是總有人執念於不醉不休,而酒仙酒聖彷彿只是傳說。
“溫一壺月光下酒”著實令人迷醉,但這迷醉也無力誘發我喝酒的潛能。所到之處,依舊是白水一杯。白水清澈見底、淡而無味,卻蘊含賦予其五味俱全的可能。或許,一杯白水也該有三重喝法,既有平平淡淡的愜意,又有小橋流水的婉約,甚至有大江東去的豪放。
月色撩人,端一杯白水或與吳剛對飲,或用一杯白水的單純去品味浮華人生,去面對世間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