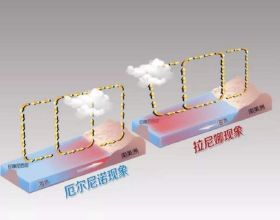意共有著光榮的歷史。1922年,義大利國家法西斯黨上臺。只有意共長期堅持反法西斯立場,其他自詡為共和、民主、自由的政黨莫不屈從於墨索里尼的權威之下。而在墨索里尼的統治垮臺後,又是意共率先組織開展反法西斯武裝鬥爭,並在1944年開始參加聯合政府。
1948年,意共在義大利大選中行情看好。本來,意共已經放棄了武裝鬥爭路線,決意走議會道路,推動國家的民主化發展。但美國中情局出面干預了義大利大選,透過一系列臺上、臺下的運作,讓意共丟掉了大選,之後因為堅持與蘇聯不一致的國際共產主義觀念,強調應選擇多中心(而非蘇方一家獨大),所以奇異地受到了美蘇兩方的共同抑制。意共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逐漸式微,還走向了內部分裂。
義大利共產黨人高唱《國際歌》 全歐洲最浪漫的共產黨_嗶哩嗶哩_bilibili
意共丟掉執政資格的案例,後來還被美國中情局不斷複製,用來打擊盟友陣營以及若干僕從國的左翼政黨,或者實在沒能成功打擊,就明火執仗地採取顛覆。這一案例可以很好地證明,那些寄望於1945年談判而建立起穩定聯合,讓民國時期的中國擺脫戰亂、結束對立、穩步發展的想法,純屬一廂情願。
言歸正傳,義大利國寶級作家卡爾維諾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小說《觀察者》。這本書的篇幅不長,卻意味深長。書作者再三強調故事內容都是真實的,只是人物角色進行了加工。
所評圖書:
書名:《觀察者》
作者:(意)伊塔洛·卡爾維諾
譯者:畢豔紅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主人公阿梅里戈·奧爾梅亞是個意共黨員。時間是在1953年,也就是意共作為反對黨存在的時代,總體上,在都靈為代表的義大利北方地區而言,意共在地方選舉中其實並不構成對主流政黨的威脅。奧爾梅亞被任命為都靈一家投票站的監票員,面對的是一個怪誕的現象:對手黨派為了拉選票,引導成群的殘障人士參加投票。
書中毫不隱晦地說,義大利的各黨派當時要實施一項新的選舉法——“其他人都將其戲稱為《欺詐法》”,也就是獲得50%+1的贊成票的聯盟可以獲得三分之二的席位,這等於左右所有的政治議程。
所以,當時義大利的主流政黨,也就是美國扶持的黨派,竭力拉票:
“每次都有痴傻者,或者即將去世的老人,抑或由於動脈硬化而癱瘓在床的人以及缺乏理解能力的人被帶去投票。在這種情況下,既滑稽又可憐的趣事層出不窮:有的選民吃掉了選票,有的選民拿著選票站在投票的格子間裡,自認為是在廁所裡,於是就用選票解決了生理所需,而痴傻者中最具學習能力的則魚貫而入,同時用合唱的方式重複著名單的序號和候選人的名字……”
阿梅里戈面對的是這樣一個荒誕滑稽的現實,他是一個一絲不苟對待事務的人。雖然意共在當時已經呈現出在義大利政壇的式微態勢,但他仍然有著樂觀主義。
是的,誰能說即將去世的老人,痴傻的人(什麼叫痴傻,痴傻到什麼程度,又有確切的答案嗎?),生病臥床的人,缺乏理解能力的人,為什麼不能投票?義大利輸掉二戰後,擺脫了德國那樣被分割佔領的命運,但這個國家相比過去,在世界、歐洲的政治地位都顯著滑落。美國肆無忌憚地操縱義大利大選,抹黑參與黨派的事情,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健全的、健康的人所參與的義大利選舉,本身的意義也大打折扣,選舉本身淪落成一場行為主義表演,所以,讓看上去滑稽可憐的人們來參與選舉,進行一番“演出”,似乎也是說得過去的。
阿梅里戈面對的選舉,在形式上也不無寒酸。義大利是個很崇尚形式的國家,從古羅馬到近代,再到墨索里尼時期,以至於今天,凡是被認為真而有價值的事物、事件,形式的設定都非常關鍵。儘管如此,阿梅里戈反而認為,民主選舉的“寒酸、暗淡”,這反而帶有崇高性,這似乎更像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崇尚的選舉,“這是誠實而簡樸的道德訓誡,以及對法西斯主義者、那些自以為是者無聲的永久報復”。
雖然小說中的阿梅里戈,以及同樣參與監票工作的其他意共黨員,都明確意識到“資產階級對這間陋室實施的欺騙”,卻仍然堅持履行本質,哪怕是選舉的結果註定被愚弄和操縱。書中,卡爾維諾意味深長地寫道,“他(阿梅里戈)開始會議,將眼前的景象與義大利解放後的氛圍進行對比。回首那幾年,他覺得最鮮活的記憶就是全民參與政治,參與當時的大大小小的問題”……當時的義大利人“似乎一樣貧窮,全都投身於全民事業,摒棄私人事務”,各個政黨的人們都積極參與各種志願活動,誠實地對待民主。
這一切在1948年以後都改變了。民主被絞進意識形態之爭,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棋子,所以敗壞。
阿梅里戈見證的選舉,可以解釋為鬧劇,也可以解釋為民主的本來方式。按照卡爾維諾的闡釋,最符合民主參與者角色的其實就是意共黨員:“一個意共黨員的心中裝著兩個人:一個毫不妥協的革命者和一個喜好競爭的自由主義者”。而站在意共對面的黨派,卻可以為各式各樣的利益訴求而隨時勾連,當然,按照一些美式自由主義政治學者的話來說,利益勾連本身是民主和自由建構的基礎,也無可厚非。
正因為各式各樣的“無可厚非”理由,所以那些半盲的人、失去雙手的患者,就需要由人陪同進入格子間,幫他打鉤。“有了這個巧妙的辦法之後,他們都晉升為完全合法合規的選民”。
《觀察者》僅僅記述了地方選舉投票者的一天日程,其中間歇地也展現了阿梅里戈的愛情——毫不意外,他與她之間的理解也是錯位的。阿梅里戈的女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小女人,只關心阿梅里戈對於她的不夠理解、不夠關懷,而對於民主毫無興趣,對於個人的公民身份沒有一點點的留意,無論是曾經真實享有這種身份,還是1948年後變成了虛假享有。這跟那些半盲的人、在選舉格子間裡大便的人又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某種意義上,卡爾維諾的這本《觀察者》如果是在21世紀的今天首發,將不出意料地引發性別歧視的討伐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