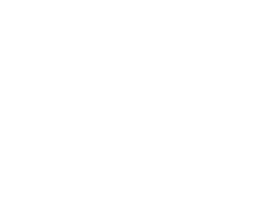1927年春夏之交,讓全美最為震驚的新聞是一樁可怕的謀殺案,它發生在長島的一個普通家庭。
報紙興奮地把案件稱為“窗簾吊錘謀殺案”。
1927年3月20日深夜,皇后區一個寧靜的中產階級社群裡,艾伯特·斯奈德和太太並排睡在他們位於第222號大街家裡的兩張單人床上。
斯奈德太太聽到樓上的走廊裡傳出了動靜,她起身檢視,發現臥室門外有個大個子男人——她對警察說那是個“巨人”。
“巨人”正操著外國口音對另一名男子說話,斯奈德太太在黑暗中看不到另一名男子。
還來不及有所反應,“巨人”就抓住了她,狠狠地毆打她,令她昏迷了整整6個小時。
而後“巨人”與同夥來到艾伯特·斯奈德的床邊,用掛壁畫的金屬線勒死了這個可憐人,還用窗簾的吊錘打了他的腦袋。
窗簾吊錘點燃了公眾的想象力,案件也因此得名。
兩名惡棍隨即將房裡所有的抽屜翻了個遍,帶著斯奈德太太的珠寶逃跑了,但他們在樓下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份義大利語的報紙,為其身份留下了線索。
次日,《紐約時報》對此案興趣頗高,但也困惑不解,它刊登了大篇幅報道,標題是:
美術編輯在床上遇害
妻子被綁,房子被翻!警方認為作案動機神秘
報道指出,來自聖瑪麗醫院的醫生為斯奈德太太做了檢查,發現她身上沒有一個受傷之處可以解釋她為何昏迷了6小時。
事實上,醫生髮現她毫髮未損。
賈斯特醫生試探性地提出,或許她長時間昏迷並不是因為真的受了傷,而是因為事件帶來的心理創傷。
這時候,警探對斯奈德太太產生了懷疑。
首先,斯奈德家完全沒有被人強行闖入的跡象,更何況對殺人越貨的珠寶竊賊來說,這家人太不值一提了。
此外警探發現,在門外發生暴力扭打期間,艾伯特·斯奈德竟然一直在睡覺——這也很奇怪。
斯奈德夫婦9歲的女兒洛林睡在大廳對面的一間房,也沒聽見任何動靜。
竊賊闖入房子,拿出一張無政府主義的報紙整整齊齊地放在桌上讀了一陣,之後才上樓——這似乎也挺奇怪。
最奇怪的是斯奈德太太的床,她半夜裡就是在這張床上醒過來聽見走廊外有動靜才起身去檢視的,但床居然鋪得整整齊齊好像完全沒人睡過似的。
她無法解釋這一點,說是腦震盪害的。
警探們正為這些異常現象感到困惑時,一名警察無聊地掀起了斯奈德太太床墊的一角,發現了她報告失竊的珠寶。
所有的目光都轉向了斯奈德太太。
她躲躲閃閃地迎向他們的逼視,最後崩潰地交代了罪行,但她說一切都怪自己的秘密情人,一個叫賈德·格雷的畜生。
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對賈德·格雷的搜捕行動也正要展開,美國的報民們很快就會異常興奮起來。
20世紀20年代都是報紙的黃金時代。
這10年中報紙銷量達到每天發行3600萬份——相當於平均每戶人家訂閱了1.4份報紙。
光是紐約市就有過12種日報,其他所有提得起名號的城市也至少有兩三種。
不僅如此,在許多城市,讀者還可以從一種徹底改變人們對日報期待的全新出版物裡獲取新聞了,這就是小報。
小報專注於報道犯罪事件、體育新聞、名人八卦,併為這三者賦予了遠超從前的重要性。
正因為有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一起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這樣瑣碎平淡的案件都能成為全國性新聞。
對於傳統的報紙而言,應對方式是讓自己在精神甚至形式上都變得更像是小報。
就連一直以來注重莊嚴與鄭重的《紐約時報》也在這10年裡花了大量篇幅,用近乎狂熱的挑逗語調報道情色訊息。
所以,一旦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這樣的案件出現,所有的報紙全都表現出了同樣的癲狂姿態。
相比之下,犯罪者異常蠢笨、毫無吸引力和想象力這一點反倒無關緊要了。
當時的新聞人達蒙·魯尼恩將其戲稱為“蠢貨謀殺案”。
案件事關情慾、不忠、狠心的女人、一枚用來繃直窗簾的吊錘,這就足夠了,這些就是能讓報紙大賣的東西。
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獲得的報道力度遠超同一時期的其他任何案件,直至1935年才被布魯諾·豪普特曼綁架林德伯格的孩子一案超過。
但就對社會流行文化的影響而言,就連“林德伯格綁架案”也遠遠比不上這件事。
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審訊往往異常快速。格雷和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後不到一個月就受大陪審團提審,站上了被告席。
皇后區的法院大樓是長島市區裡一棟莊嚴的古典風格建築,此刻也瀰漫起了狂歡的氣氛。
來自全美各地的130家報紙派出了記者,連遙遠的挪威也來湊熱鬧。
西聯公司架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電報交換機——比總統就職典禮、職業棒球總決賽上用的還要大。
法院外面,沿途擺起了餐車,紀念品小店以10美分的價格出售吊錘形狀的胸針。
成群結隊的人每天都來看熱鬧,希望能搞到旁聽席的座位。
進不去的人則站在大樓外面眼巴巴地盯著它,迫切想知道樓裡進行的那些自己看不到也聽不到的重要裁決。
富人和時尚人士也紛紛露面,包括昆斯伯裡侯爵,以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妻子。
有幸坐進法庭的人獲允在每天聆訊結束後上前觀看涉事證物:兇手用過的窗簾吊錘、掛壁畫的金屬線、裝麻醉劑氯仿的瓶子。
《紐約每日新聞報》和《紐約每日鏡報》刊登的審訊新聞曾多達一天8篇,如果當天揭露了什麼特別吸引人的細節,比如,露絲·斯奈德在案發當晚穿著血紅色的睡衣迎接賈德·格雷,就會立刻印刷專刊,這陣勢就跟要宣戰了似的。
對那些著急得沒法耐下性子閱讀文字的人,《紐約每日鏡報》在3個星期的審訊期間提供了160幅照片、圖表和其他插圖,《紐約每日新聞報》配圖則達到了200幅。
愛德華·賴利擔任了一陣格雷的律師,沒過多久,他就因為替“林德伯格綁架案”中的布魯諾·豪普特曼辯護而聲名狼藉,但賴利是個不靠譜的酒鬼,案件開審後不久就被解僱了,要不就是他主動辭職的。
在那三個星期中的每一天,陪審員、記者和觀眾都鴉雀無聲,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艾伯特·斯奈德的慘劇。
故事開始於10年前,《摩托艇》雜誌寂寞的禿頂美術編輯艾伯特·斯奈德對辦公室秘書露絲·布朗產生了迷戀。
露絲心氣高,但並不怎麼聰明。她比斯奈德小13歲,對他也不怎麼感興趣。
但兩人約會三四次之後,斯奈德送給她一枚口香糖大小的訂婚戒指,露絲矜持的防線崩潰了。
“我沒法放棄那枚戒指。”她無奈地向朋友解釋。
兩人認識4個月後結了婚,搬進了斯奈德位於皇后區的家。
結婚才兩天,她就跟朋友說自己並不怎麼喜歡丈夫。
10年無愛的婚姻就這麼拉開了序幕。
露絲頻頻獨自外出。
1925年,在曼哈頓的一家咖啡館她遇到了賈德·格雷,格雷是貝安·朱莉緊身胸衣公司的推銷員。
兩人很快有了私情。格雷看起來不像宵小之輩,他戴著粗框眼鏡,體重只有54.4公斤,叫露絲“媽咪”。
在不曾沾染桃色緋聞的世界,他在主日學校教書,在教堂唱詩班唱歌,為紅十字會籌措資金。
因為對自己的婚姻愈加不滿,露絲欺騙不知情的丈夫簽下一份帶雙重賠償條款的壽險保單,萬一丈夫遭遇暴力事件,露絲便可領到近10萬美元的賠償金。
此後,她一直堅持不懈地確保此事發生。
她在丈夫晚上喝的威士忌裡下毒,又在他吃的蛋奶水果點心裡下毒。
當然,記者們對此事也大書特書。
可毒藥沒能放倒斯奈德先生,她便又碾碎了安眠藥放進蔬果汁,並假稱為了健康讓他服了氯化汞,甚至還試著用煤氣燻死他,只可惜,事實證明毫不知情的斯奈德先生堅不可摧。
無奈之下,露絲只好向賈德·格雷求助。
他們一起設計了一場自以為完美的謀殺。
格雷先搭乘火車前往紐約州中部的雪城,入住奧內達加酒店,並確保有很多人看見自己,之後悄悄搭乘返程列車回到城裡。
離開酒店後,他安排了一個朋友去自己的酒店房間把床弄髒,讓房間看起來是有人住過的樣子。
他還留下了信,讓朋友等他走後再寄出。
不在場證據就緒之後,格雷在深夜來到皇后區斯奈德的房子前。
露絲坐在廚房裡等著,穿著那件很快就要出名的紅色睡衣,把格雷放進屋。
按計劃,格雷潛進夫婦倆的臥室,用露絲事前放在梳妝檯前的窗簾吊錘砸碎艾伯特·斯奈德的腦袋。
可惜事情並未完全按計劃進行。
格雷膽戰心驚、試探性地敲了第一錘,反倒驚醒了受害人。
看到一個奇怪的小個子男人站在自己身邊用鈍器敲擊自己的腦袋,斯奈德先生困惑不解,因為疼痛發出了叫喊,也相當有力地給予了還擊。
他一把拉住格雷的領帶,讓格雷喘不過氣來。
“媽咪,媽咪,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快救我!”
露絲·斯奈德從掙扎的情人手裡奪過吊錘,猛地砸在丈夫頭蓋骨上,斯奈德先生便沒了動靜。
之後,她和格雷把氯仿倒進斯奈德先生的鼻孔,用金屬線勒死了他——這兩件事中露絲都幫了忙。
之後,他們拉開整個屋子的抽屜和櫥櫃,讓它看起來像遭了劫。
但兩人似乎都沒想到要把露絲的床弄得像是有人睡過。
格雷鬆垮垮地綁起露絲的腳踝和手腕,讓她舒服地躺在地上。
他還設計了最狡猾的一招:在樓下的一張桌子上擺了份義大利文報紙,好讓警察以為入侵者是外國顛覆分子,就像馬薩諸塞州等著被處決的薩科和萬澤蒂——這兩人都是臭名昭著的無政府主義者。
事情都辦好以後,格雷吻別了露絲,打了一輛計程車進城,搭乘火車回到雪城。
格雷以為,就算自己受到懷疑,警方也證明不了什麼,因為480千米之外的雪城有他確鑿的不在場證據。
遺憾的是,長島的一位計程車司機記住了格雷,因為格雷搭車的車費是3.50美元,卻只給了5分錢的小費,哪怕在20世紀20年代,用5分錢來表示感謝也太小氣了些,所以司機迫不及待地想要指證他。
警方在奧內達加酒店追蹤到了格雷,面對警方的懷疑格雷表現出一臉驚訝的樣子:“這是怎麼回事?我連超速罰單都沒吃過。”
他自信滿滿地說自己整個週末一直在酒店。
不幸但也很有趣的是,他居然把返程的火車票的票根扔在了廢紙簍裡。
一名警察把票根翻檢出來並質問他,格雷立刻招供。
聽說斯奈德太太把罪責都推到自己身上之後,格雷歇斯底里地堅稱她才是主謀,而且,是斯奈德太太威脅自己要向他妻子告發他的不忠,逼迫自己與她合作的。
很明顯,他和斯奈德太太的情分走到了盡頭。
一位叫塞拉斯·本特的記者仔細測量了報紙專欄的尺寸,發現用於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的報道篇幅比“泰坦尼克號”沉沒還要多。
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在一篇文章中發問,為什麼一宗如此平淡又缺乏想象力的謀殺案引發了這麼熱切的關注呢?
可惜他忘了停下來反思一下——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質問他寫的文章啊。
在他看來,此案基本上是“老套主題”的另一個例子:“狼子野心的女人對順從的男人發號施令。”
當時人們幾乎一致認為犯罪的是露絲·斯奈德,賈德·格雷是個上了當的倒黴鬼。
格雷收到了大量滿懷同情的信件,塞滿了皇后區監獄兩間相鄰的號子。
報紙努力想把露絲·斯奈德描繪成一個邪惡的妖婦。
“她天生的金髮呈現出完美的大波浪形狀。”一位觀察家刻薄地寫道,彷彿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證明她有罪似的。
《紐約每日鏡報》說她是“鐵石心腸的女人”。其他刊物稱她為“人面蛇心”的“冷酷女子”,甚至亢奮過度地說出了“北歐吸血鬼”這樣的話。
幾乎所有報道都死盯著露絲·斯奈德致命的美貌,但這要麼是出自幻覺,要麼是選擇性誇張。
1927年時露絲·斯奈德已經36歲了,她身材臃腫,滿臉倦容。她的面板長了斑,總帶著一臉怒容。
坦率些的評論家懷疑她根本就不曾有過什麼吸引力。
《紐約客》的一名記者暗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分析出人們對露絲·斯奈德的興趣到底來自何方……她無法抗拒的魅力恐怕只有賈德·格雷看得見。”
格雷則戴著一副沉重的圓框眼鏡,看起來顯得充滿難以置信的機智、學究氣,比35歲的實際年齡老成許多。
在照片裡,他總是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無法相信自己怎麼落到了這般境地。
為什麼這樁謀殺案吸引到了如此熱烈的關注,在當時就很難說清,現在更是不可能了。
那一年,就在紐約,就有大量其他更“精彩”的謀殺案能夠激起關注。
其一是報紙戲稱的“格雷夫森德灣保險謀殺案”,一個名叫本尼·戈爾茨坦的人制訂了一套計劃,假裝自己在布魯克林的格雷夫森德灣溺水,好讓朋友喬·萊夫科維茨能收到75 000美元的保費,之後兩人對半分。
可萊夫科維茨對此計劃做了一項重大調整:他沒把戈爾茨坦送到新澤西州的海灘上,而是在格雷夫森德灣把戈爾茨坦扔出了船,確保他真正淹死。
戈爾茨坦不會游泳,所以肯定是死了,萊夫科維茨一個人獨吞了所有的錢。只可惜還來不及享受,就被抓住定罪了。
對比來看,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笨手笨腳又老套,再加上兩名被告完全供認不諱,甚至不能帶來精彩的法庭辯論。
一點兒都不誇張地說,它最終還是成了著名的“世紀之案”,對流行文化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影響,尤其是影響了好萊塢、百老匯,以及輕小說的煽情結尾。
可憐的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一案還有另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兇手被抓住了。
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1929年,紐約接到報案的謀殺案有372樁,其中115樁無人被捕,就算抓到了人,定罪率也不到20%。
全美範圍內,按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資料,1927年全美2/3的謀殺案懸而未決。
請注意,最準確的記錄是保險公司留下來的,而不是警察局。
其他一些地方的破案率,甚至連這點可憐巴巴的比例都達不到。在某些年份,芝加哥出現了450~500樁謀殺案,然而成功結案的數量遠遠低於1/4。
總體而言,根據該調查的統計推算,全美的重案犯中10個有9個逍遙法外。
100個兇手裡只有一個被處以死刑。
所以,露絲·斯奈德和賈德·格雷必然是真真正正的無能,才會在作案後被指控、被定罪,最終還被處決。事實也確實如此。
5月9日下午晚些時候,律師做了結案陳詞,12人的陪審團閉門決議。
這12個人全是男性,因為1927年紐約州禁止女性旁聽謀殺案。
1小時40分鐘後,陪審員慢吞吞地走出來宣告判決結果:兩名被告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露絲·斯奈德在座位上痛苦地哭了起來。
賈德·格雷滿臉通紅,狠狠地盯著陪審團,但並無恨意。
斯卡德法官宣佈下週一量刑,這其實只是一種形式,一級謀殺罪的刑罰就是電刑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