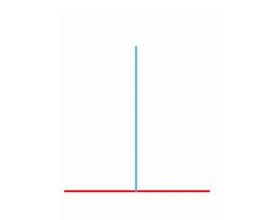美國製度最深層的悲劇是什麼?
一個在源頭上並不完善的制度,卻在憲政的名義下成了神聖至高的理想原則,這就是美國製度最深層的悲劇。
這句話怎麼理解,我們從美國製度的根上來做個分析。
首先,美國是個公司式治理的國家。
從根本上說,整個美國,就是一個由各州聯合而成的“新設合併”公司。
從公司的視角看,有限責任公司一般有兩種管理形式,一為股東管理,二為經理管理。股東管理就是所有股東有管理公司的同等權力。這種管理形式權力非常分散,適合股東人數很少的公司,管理上更為靈活。做一個不嚴謹的比擬,原始部落或小型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就類似這樣一種股東管理制。
但是當公司達到一定規模時,這種管理制度就無法持續了。為應對更復雜的任務、避免股東之間的衝突,就需要將管理權集中起來,實行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股東不再直接插手日常管理,只負責重大事務,如確定和修改規則、聘任經理等,具體日常經營事務都由經理來負責管理。
國家當然比公司要複雜得多,要承擔外交、戰爭、民權、福利等更為棘手和重要的任務,顯然無法簡單套用公司式的經理管理制。“股東”“董事會”與“經理”之間的關係,就這樣是具有公司性質的國家在制度設計中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是美國製憲者的困惑所在。
美國建國之初,制憲者們似乎不太確定應該堅持純粹的“委託--代理”關係,還是模糊“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界限,結果留下了一個未定型的制度基礎,到底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治理結構,對美國而言的確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其實,從歷史上看,公司型治理的國家很多,比如典型的威尼斯、荷蘭,現在也叫尼德蘭,關於這個話題,我們後面找機會專門再講一期。
說回美國。
在公司型國家的漫長演進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主要的制度形式,一種是總統制,另一種是議會制,而美國,則是典型的總統制。那麼,美國總統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制度困境,又是什麼呢?
著名的美劇《紙牌屋》大家都看過吧,看過的朋友一定深有體會,美國的政治最鮮明的特色,就是總統、國會與官僚機構的權力遊戲,而在這個遊戲中,美國官僚制度的困境,逐漸演變成了美國製度的最大困境。
為什麼這麼說?
美國三權分立的公司式國家管理結構中,行政官僚機構,其實有兩個“婆婆”,一個是總統,一個是國會。總統和國會競爭的結果,並不是兩者權力的此消彼長,而是總統和國會對行政機構的權力都上升了。行政機構同時成為了國會和總統的代理人。
表面上看,官僚機構在總統和國會兩個“婆婆”的控制之下,實際上它卻藉著這個結構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官僚機構的權力更加膨脹,變成了我們通常所說地地道道的“兩頭都管,兩頭通吃”。
對於這個困境,有一種解釋,或許可以從美國政治的源頭和底色上找到些許答案。
美國政治的底色是什麼?來看這麼一段話。
與歐洲相比,美國文明的流動性更為典型。“美國是一種新型的貝都因人,他們重視遷移的自由甚於其他任何事物”。“人們不是按照他們的地區和籍貫來劃分,而是按照形形色色的目的和打算來劃分的”。不僅人在流動,政治組織也在相應地迅速變化,美國的首都曾多次搬遷,從宣佈獨立到1812年,原來的十三個州中有八個州變更了首府。”也許義大利黑幫是美國唯一一種依靠傳統和部落式的忠誠來維繫的社群。電影《教父》和《愛爾蘭人》中的紐約義大利黑幫生活,絕不是美國生活的標準模型。
從北美殖民地誕生的第一天起,流動就是這個文明的底色。要真正理解美國製度的性質,必須回到其誕生的時刻。美國製度今天的樣貌,均刻寫在其最初的基因之中。而流動 性感,是這個基因的一個重要片段。
最後我們回頭來看,從公司治理結構中生長出來的美國憲法制度,就像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中被髮射到地球上的“智子”一般,鎖死了美國國家體制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可能。三權分立有其虛假性,也從來沒有以純粹的面貌出現過,但是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則可以成功阻擋任何打通三權、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權威的努力。無論是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還是金融大鱷索羅斯,都呼籲修改這部憲法。另一方面,違反憲法原則的尼克松、打破了美國政治傳統差不多所有規矩的特朗普以及被特朗普稱為腐敗政客的希拉里,口中都須臾不離憲法神話。憲法原旨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以及試圖顛覆者,都不得不拉上《憲法》給自己背書,恰恰說明這個憲法已經成了利益的奴婢。一個在源頭上並不完善的制度,卻在憲政的名義下成了神聖至高的理想原則,於是,也就成了美國製度最深層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