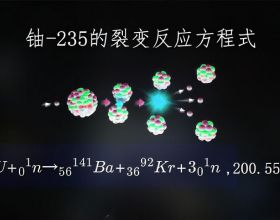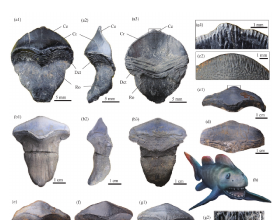“好好吃飯?奢侈。”阿沁低頭苦笑,“我已經三年沒有好好吃過飯了。”
在阿沁看來,食物和熱量,都是她走向好身材的最大惡魔,唯避之恐不及。
“醫生給我的診斷是厭食症,伴隨雙相情感障礙。”
患上厭食症,意味著人生被食物、熱量與身材的博弈佔據,唯一的出口就是,少吃,再少吃。而厭食症患者在接受治療康復後往往會轉向另一個深淵——暴食症。
“因為身體的能量虧空太多太多了,大腦會讓你不停吃,直到吃不下,但也停不下。”
而這一切的開端,都是減肥。
大一時,阿沁一米六出頭的個子,98斤的身材,她很不滿意。“大家都說,女孩子瘦一點好看。”
在大學裡,女生之間不會相互吐槽,但是都會心照不宣地羨慕校道上身材火辣的美女。下定決心減肥變美的阿沁,不是在上課的路上,就是像超人一樣在健身房裡,每天運動達到三個小時,日復一日。但當體重下降到93斤時,就死活不往下掉了。阿沁在網上四處搜尋,瞭解了很多減肥瘦身的知識,明白了減肥不是睡前在床上做兩分鐘瘦腿操就可以,而且在腿上和腰上裹保鮮膜的方法是沒有用的。真正的減肥計劃是像在網上被吹爆的“21天減肥法”那樣,必須精確規劃每天的吃喝,計算每天吃進去的熱量和自己代謝掉和運動產出的熱量,畢竟網上的減肥博主都在說“熱量差才是王道”。
阿沁決定開始從飲食上下功夫,她在網上了解到一款監測和計算食物熱量的App,她開始關注到食物的包裝,像對待學習一樣嚴格。每天吃什麼,吃多少,在阿沁這裡儼然成了一道計算題。
正常的成年女性一日正常活動需要2000卡路里的能量攝入,就算每天不活動,維持生命的基礎消耗也需要1200卡路里。而阿沁給自己設定了500卡的目標,撐死不過800卡的上限。從剛開始的不吃晚飯,到中飯只吃一個蘋果,餐盤上的食物越來越少。“每天吃飯都像在做計算題一樣,在我預計範圍內多吃一顆米,我就會想不開。”
阿沁早早和米飯等主食斷絕來往,零食也一概不碰,且只有哪天吃的熱量比設定的熱量少的時候,她才肯安心睡覺,否則就不會停止運動。
在用App以後,阿沁的體重幾乎每天都能下降。就這樣阿沁的體重降到了83斤,同時她還會收到一些有意無意的誇獎,身邊的朋友都注意到她的變化。
阿沁嚐到了甜頭,決定加大力度繼續減肥。
阿沁漸漸發現,吃飯在生活中真的是一件繁瑣又難以避免的事。同學聚餐、朋友生日、部門團建,都得吃飯。在那樣群體進食的環境中,阿沁感覺十分別扭,一來她不想讓人知道她在減肥,二來又怕把食物吃掉就會變胖。坐在飯桌上,椅子上像是有密密麻麻的針,阿沁坐立不安,總感覺有人想摁著頭讓她吃飯。於是阿沁把能推掉的所有的飯局都推掉,部門團建?免談。朋友生日?買個禮物就行了。平時上課也不再和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飯。大學社交最高效的手段——吃飯,幾乎被阿沁徹底排除在外。她逐漸成為同學眼裡那個獨來獨往、性格孤僻的人。
但阿沁不在乎,她滿腦子只有減肥這一個念頭,她想,“減肥了一切都會變好”。
朋友那一關過了,可父母那一關不是那麼好過。阿沁的父母眼睜睜看著女兒上了一年大學回來從正常的體型變成一個穿T恤彎腰脊樑骨都會冒出來的身板。母親覺得阿沁肯定在大學受苦了。
放假在家,母親變著法給阿沁做好吃的。阿沁不想讓母親傷心,但是又不可能放棄減肥,於是,她撒了謊。阿沁把餐盤端進自己的房間,跟父母說要邊學習邊吃,關上房門,把食物輕聲倒進垃圾袋,再計算好吃飯的時間,等差不多過去後,開啟房門把餐盤端出去,佯裝誇母親飯做得好吃,然後藉口外出遛彎扔掉食物袋,一氣呵成。
但就算阿沁演技再好,母親還是察覺到女兒的異樣,畢竟撒謊次數多了就不管用了。阿沁被強制要求在飯桌上吃完飯,面對眼前的食物,阿沁內心是一萬個拒絕,她早就感受不到吃飯的快樂,餐盤裡的食物是讓人發胖的罪惡卡路里。
阿沁又撒謊了,趁父母盛飯或是喝水的間隙,她把飯藏進口袋裡,藏進袖口裡。真正進到阿沁肚子裡的,只是幾片在水裡涮了又涮的青菜。
長此以往,阿沁的身體開始發出抗議。她的例假停滯了,手上、背上、臉頰兩側因為身體供能不足長了很多汗毛,手臂上出現老人斑,開始蛻皮,頭髮也一把一把地掉。出門在外,阿沁走不動路了,在公交車上,連老人都站起來給她讓座。每一個早晨,阿沁都在噩夢中被冷醒,她的注意力變得難以集中,視線也模糊起來。
阿沁徹底失控了。
父母意識到阿沁病了,帶著她四處求醫。去消化科檢查進食問題,去婦科檢查例假問題,去心血管科檢查心臟問題,又跑去內分泌科、神經外科、臨床營養科、骨科,甚至做了腦電圖和全身CT。
但醫院各個科室都跑遍,依然無果。他們轉而又四處查閱文獻,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爸爸心急如焚,在網上四處查詢,終於在上海找到了一家對症的醫院。
“確診了,厭食症,伴隨雙相情感障礙。”
病危通知書上寫著密密麻麻的字元,“抑鬱症是最諷刺的。”
阿沁的父母雙雙畢業於名牌大學,工作體面,家境優越。“我從小就有很棒的家庭,受到最好的教育。”家裡有溫柔大方的媽媽,大樹般的爸爸,近百歲的外婆得了失憶症,卻一直記得阿沁。
而今,日復一日,針頭來來回回扎進她太細的血管。母親躲在父親身後,在哭。
檢查結果顯示,各臟器衰竭,在病房裡,阿沁不得不靠著瓶瓶罐罐來維持生命。
“那時候感覺到會跟死亡很近,就好像,經常能看到一束光。我覺得我當時活著也是不對的,死了也是不對的,就是不管怎麼做都是會給世界帶來很多麻煩。”
發現阿沁生病後,父親經常呆呆地看著資料表,半年不到就長滿了白髮。母親曾是職場上的女強人,現在拋下工作,像帶孩子一樣,研究起了各種烹飪和營養,手上燙了好多傷,阿沁好心疼。外婆依舊寫著阿沁的名字放生,依舊每天為她念五百遍經文。但那個百歲老人已經認不出眼前的阿沁了,她太瘦了。
電影《To the Bone》劇照
一部分厭食症患者會在治療後轉向貪食症甚至暴食症,阿沁就是如此。出院以後,阿沁的體重長了10公斤。但在長期過度節食後,阿沁的身體出現了報復性補償,彷彿是體內放出了一匹脫韁野馬,她開始了難以控制的暴食。
“我從一開始拒絕吃任何東西,到後來不可控制地想要去吃東西,我不得不面對我曾經最害怕的事情,這種失控的感覺讓我不知所措,我每一天都在崩潰和掙扎裡,重複著。”
長期欠缺營養的身體,徹底從阿沁手上奪過了主動權。最黑暗的一段時間,阿沁不是在吃,就是在尋找下一個塞進嘴裡的食物。一袋子冰淇淋,十人份的盒飯,都是一次性吃完。超大包裝薯片,一吃就是好幾袋,麵包一吃也是十幾個。吃到最後,肚子鼓得像孕婦一樣大,就算呼吸困難還是不想停下,直到精疲力竭,再也嚼不動一口。
“反正肚子已經很難受,想做什麼也做不成了。”阿沁開始自暴自棄,索性將自己變成一個沒有感情的進食機器。
當食慾像脫韁的野獸張牙舞爪時,無論手邊的食物是什麼,都必須馬上塞進嘴巴。手邊的食物塞完了,冰箱裡凍得像石頭一樣硬的披薩阿沁也會拿出來啃,“實在等不到它熱好,那時候,感覺自己不是人。”就連半生不熟的雞肉,她也會塞進嘴裡。媽媽生怕吃出問題,哭著跪下來,求阿沁不要吃。
得了進食障礙,就像是被推進無邊無際的陰影裡,無時無刻不在與食物殊死搏鬥,稍不注意,黑暗就會將人吞噬。
“大家都在鼓吹自律,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格。”即便阿沁想要慢慢戒掉暴食,但無法控制每天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鏡子。這種焦慮就像房間裡的大象,其實每個人都心知肚明,但都在假裝它不存在。
“幸運的是,我暴食後不催吐。”阿沁說,“一旦開始催吐,就會上癮,要走出這個暴食——催吐這個死迴圈會更加困難。但是後來我瞭解到,進食障礙的很多人都走上了催吐這條路。”
在父母的陪伴下,阿沁再次開始治療。
阿沁在網上分享自己的經歷,認識了很多和她有類似經歷的朋友,深陷進食障礙旋渦的他們在分享自己故事的過程中互相治癒。
在這期間,阿沁也發現了海面下沉默的冰山:在微博上組建的互助群,短短几個月成員就突破了一千。並且有很多進食障礙患者認為自己的行為難以啟齒,無處傾訴,也不敢尋求幫助,身邊親人的誤解使他們更加無法接受自己,形成惡性迴圈。“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幸運的,我有理解我病情的父母。”阿沁慨嘆說,“但當下的情況是,很多患者的家裡人根本沒辦法理解這個病,她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來,這是很困難的。”
有很多深陷痛苦的女孩給阿沁發來長長的私信。可聊了十幾頁以後,很多女孩還是放不下減肥的執念,繼續在厭食和暴食、自卑和失控中反覆橫跳。
“我理解這種感覺,作為親歷者,我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阿沁在網上為普通人普及這種疾病的相關知識,也在鼓勵和幫助病友,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怪物”,康復道路上並不孤獨。而她自己也從陌生的網友那裡獲得了很多溫暖關懷。阿沁現如今正堅持站在科普進食障礙的第一線。
“我們一定都會好起來的。”阿沁很有信心。
“人生中有許多比追求美麗的外貌更有價值的事,過多地糾結體重和容貌,會妨礙自己變得更好。放下對於身材和容貌的執念,學會愛自己,欣賞自己,接納自己,這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應該是一門必修課。”阿沁笑著說,“我不確保進食障礙會陪伴我多久,但我已明白自己的舞臺不應該是在體重秤上。”
“那些高大粗壯的榕樹,細密的樹根都是深深扎進地下的裂縫中的。我希望從進食障礙這個裂縫中爬出來的你,也能過上枝繁葉茂的生活。”一個進食障礙病友如是說。
題圖 | 圖片來自《骨瘦如柴(To the Bone)》
配圖 | 文中配圖均來源網路
(文/石也,本文系“人間故事鋪”獨家首發,享有獨家版權授權,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轉載,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