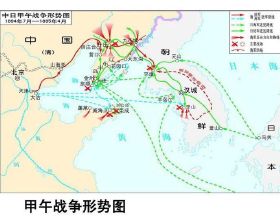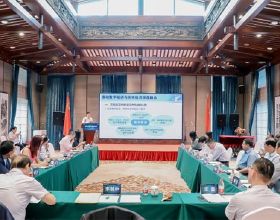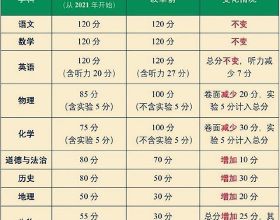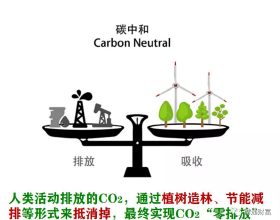童年時,有天新聞聯播說第二天凌晨東北方向有流星雨,部分地區的人肉眼可見。
聽了新聞,我預設把自己劃在“部分”地區。然後懷著興奮的心情等待。心想,我還沒見過流星雨呢,我要看流星雨。
“什麼是流星雨?”我問爺爺。
爺爺說:“夜裡有星星劃過的時候你叫它啥?”
“流星。”我說。
“天上有很多個星星同時往下掉時,就叫流星雨了。”爺爺說。
我聽了心裡緊張起來。又問:“那麼多星星掉到哪裡了?為啥不往我們這裡掉?星星掉下來會成什麼樣?它有多大?它還亮麼?它是圓的麼?”
“星星就是個石頭麼,我們看著亮,掉下來就不亮了,會被風化,要是掉到地上,地上會被砸個大坑,要是掉到我們這裡,莊子怕是都會被一鍋端了,人都全部炸死啊。”爺爺說。
我越聽越緊張,心想流星不往我們這裡掉,也是好事。
“什麼是天文學家?我能當天文學家嗎?我將來要當個天文學家!”我大聲說。
爺爺聽著笑乎乎兒不吭聲。
奶奶撂下笤帚疙瘩說:“你還想上天了。”
瞧,別人是年少輕狂,我在孩童時,就已經輕狂了。
那天晚上,我異常興奮,很晚了都睡不著,想著人要是一夜不睡覺也不犯困就好了。
我讓爺爺把它的電子錶定時放在我的枕頭邊。一邊想著流星雨,一邊擔心電子錶的聲音萬一把我吵不醒怎麼辦?
不知是電子錶的響聲沒把我吵醒,還是爺爺根本就沒有定。總之第二天等我醒來,天都快亮了。
當我跑去爬梯子上房時,心太急,腳在木結上打了滑,跌了一跤。辛虧爬的不高,摔的不重,只在腿上擦破點兒皮。
上到房頂,東北方向都發著魚肚兒白了。
清冽的早晨,天空安靜,四周安靜,星星也不見掉一個,只有北極星和月亮相守。
越等越,連北極星也淡了。
流星看不到,心裡很是不甘,就不願下去,磨蹭著磨蹭著,見初升的太陽冒了個紅尖尖兒出來,像火柴頭頭一樣稀罕,紅紅的一點點兒,慢慢往上鑽。
那是我第一次看日出,那時還是個孩子,只覺得又新奇又神奇,心裡的失落感立馬衝抵了大半。
那個早晨方圓百里霧氣微微,風呼呼呼呼吹過來,樹木就窸窸窣窣晃起來。遠處野狗狂吠,近處喜鵲麻雀成群結隊,它們撲稜來,撲稜去,忽高忽低,興奮嬉戲。
天亮了,公雞打鳴,豬哼哼,羊咩咩,騾子也踢踏踢踏弄出響聲。縱使隔著房頂,我也能想到它要吃的時扭動屁股的那副諂媚矯揉樣。
民以食為天,命也是以食為天。在吃的事情上,它們是默契的,叫喊聲一聲接著一聲,一聲緊似一聲,好像個個兒都是餓死鬼投胎來的,巴巴兒等著人類能快點起來餵它們,如若不然,就吵死你不償命。
生靈醒了,人就醒了。
遠處近處,熊熊黑煙從各家的煙囪裡衝出來,衝破了濛濛藍的天,衝破了畫兒一樣的早晨,也衝破了我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