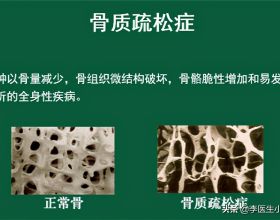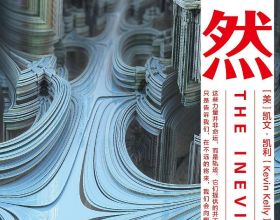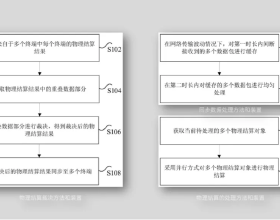這輩子似乎什麼都得到了,齊活兒了;又似乎什麼都失去了,空落落的。
可能這就是人的一生吧,挖東牆補西牆,慾望不止,償還無斷。
①
魯樵28年前本應離婚的。
28年前,他是一家制氧廠的貨車司機。跟廠長打過幾回交道,廠長挺欣賞這小夥兒,對他有種意外的熱情。有天廠長找他聊天,家長裡短聊了一下午,情到深處,廠長忽然問他想不想“坐辦公室”,他說兩年之內可以把他調到辦公室做主任,但是有一件事需要他幫忙,廠長大人在外面把一個姑娘肚子搞大了,讓魯樵娶她,孩子生下來把戶口辦好,就可以離婚。
當時才24歲的魯樵愣了半天。他知道廠長為什麼選他,他老實,話少,又是孤兒,牽扯的人少。其實打心眼兒裡他是瞧不起這種事的,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有離過一次婚的汙點,可他又極想坐辦公室,就像廠長說的,他再去考一個夜校的大學文憑,到時候就是幹部待遇。那個年代,幹部拿的退休金比普通工人多了近一倍。
魯樵回去猶豫了幾天。最終讓他下定決心的是,他無意中看到了那個女人。她從廠長的車上下來,穿一條碎花小裙,鵝蛋臉,眉目含情。他被這從未見識過的美震懾,心中的天秤咣一下垮了。
女人叫青。
趁青肚子還不明顯,魯樵按安排把她娶了回來。廠裡立刻給他分了套間,廠長也沒有食言,青生兒子不久,廠裡就把魯樵調到了總辦。
魯樵在家裡和青說話不多,彼此都很客氣。慢慢地心裡頭竟然有了牽掛,在外面看到好看的頭花衣服什麼的,魯樵順手就買回來了。有時候走在街上,看人家女人不好看還挺心疼,有種“這衣服穿在她身上真糟蹋”的自豪。魯樵偶爾會醒過來不該陶醉,可是越遏制,心裡的那根牽掛擰得越粗。
青在家裡奶孩子,也不揹他。雪白的胸脯袒露在他和嬰兒面前,乳頭已被嬰兒的吮吸重塑,飽滿的一顆,呈出母性的慷慨。每當魯樵覺得自己應該主動迴避時,已經來不及了,都看光了。
很快孩子一歲,魯樵和青商量離婚的事。他倆都有點捨不得,魯樵讓她決定具體日期,青讓他決定具體日期。倆人都不肯決定,空氣凝固在那兒,片刻之後,氣氛裡流動起一股胭脂紅。
②
廠長因受賄被抓就在那期間。得到訊息時,魯樵又懵了一會兒,等他反應過來,看到青在哭。她的肩頭微微聳動,抱著孩子,痴呆了一樣。
魯樵本能地去安慰她。
青一下子抓住他的手腕:“我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
魯樵說:“要不然,你就先跟我過吧……”
當時計劃生育管得緊,他們沒法生二胎。青說:“這不行,對你不公平。”魯樵說:“那你怎麼辦?我在這種時候把你推出去?你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青又哭了。這時孩子已經睡著,她的眼淚把魯樵哄到了床上。那是魯樵第一次深層次地接觸女人。頭一回做得不太好,很快再來,上路得還挺快。女人那柔軟的暖和勁兒,讓他癱了一樣,這婚,不離了。
魯樵跟青的日子過得和和美美。過了一段時間聽說廠長被判刑5年,廠長夫人登門拜訪,說她去探監的時候,她男人說魯樵是他心腹,想見見他,有話跟他說。
哪裡是想見他,是想見青跟孩子吧。
晚上他跟青商量,青說:“不去。”
去就意味著對魯樵的背叛,魯樵摟著她,挺感動。
兩年後聽說廠長因病死在監獄裡,青一次沒去過。
魯樵問她:“你後悔嗎?”
青說:“不後悔。”
魯樵的臉此刻在她飽滿的胸脯間,有句話他一直沒有說出來:這輩子你都是我的了。
③
他們給孩子上戶口,取名魯青。魯樵本來想取“魯愛青”來著,青說,別人喊起來都跟皇上喊大臣似的,不好。青是個賢惠女人,凡事都為家裡著想,為她男人著想。她男人是坐辦公室的,她每天早上把他襯衫熨得鐵平,晚上上床睡覺,幫他拽褲腳。幾年下來,她已經會像家屬院其他的戰鬥婦女一樣搶水池洗衣服,佔繩子晾被子。她還有個絕活兒,曬得一手好醬。黃豆煮熟後用面拌,放涼,包起來悶幾天,悶得長毛再在罐子上蓋塊玻璃在太陽下暴曬,曬出來那個醬汁,煮魚煮豆腐,極香。她拿它賄賂新廠長夫人,把新廠長夫人哄得眉開眼笑。
魯樵從沒想到,他跟青這一恩愛就是幾十年。兒子魯青也爭氣,考上了一本。青從小就教他百善孝為先,教他父親是一家之主。教得好。兒子上班後第一個月的工資給魯樵買了件羊皮大衣。魯樵高興得,穿它出門在外說話嗓門都大了一倍。
前年青的小姨過世,她回老家去奔喪。魯樵本來準備一起去,青不讓。她說單位在改制口上,廠裡工人早就下崗了,現在幹活的都是打工的。魯樵還有幾年就退休,他得好好表現把這幾年扛過去。魯樵一想也是,這麼大年紀了也不好折騰,只要單位一天還沒死,他就得一天緊捧著這吃飯的碗。
就是在那幾天,他碰到了小芸。
小芸28歲,長相比不過青年輕時的一半。但嘴巴巧,推銷起產品來唧唧呱呱說得比唱得還好聽。魯樵被她那薄皮小嘴說暈了,買了個健身器材回來。小芸加他微信,開始哥長哥短地撩,叫他幫忙介紹客戶。
魯樵介紹不來,有點內疚。小芸跟他聊,他只能硬著頭皮應。小芸問他做什麼的,孩子多大,他也得禮貌性地問她做什麼的,結沒結婚。小芸說她以前在東莞做那個,這不被轟回來了麼。魯樵被她的坦誠震驚,又帶著點好奇,問她細節。她什麼都說,毫不遮掩。
青要回來的前一天晚上,魯樵閒著發慌,給小芸打了個電話,約她出來吃飯。倆人都喝了點酒,魯樵走路如拌蒜,跟小芸去了她的出租屋。
第二天早上小芸說家裡空調壞了,魯樵給了她兩千塊錢叫她買個空調。
青回來後,兩口子照常過日子,小芸再發微信來,魯樵都沒回。
④
一個月後,小芸發了條微信來,只有4個字:“我懷孕了。”
魯樵瞅著這4個字,悲喜交加。他忽然發現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這件事,其實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這4個字讓他隱藏二十多年的遺憾一下子破土。
他立刻給小芸打電話,問她真的假的。小芸說是真的,也不要多的錢,兩萬。他不給的話, 她就把孩子生下來。魯樵一下班就衝到小芸家去。他發誓一生守口如瓶的事情,此刻再也沒法堅守。他竹筒倒豆子般把自己和青的事兒跟她講,他說他要這個孩子。這會兒驚呆的是小芸,過半天,她問:“那我生下來你給我多少錢?”
魯樵想了想手裡的財產,單位的房子當年花幾千塊錢買斷了,現在可以賣70來萬,他和青早些年在業餘時間養蜈蚣賺了點錢,還在市郊買了套房,沒有貸款,現在也值8、90萬了。本來攢錢買那套房子是準備給兒子將來結婚用的,現在想想兒子也不是親生的,他還有餘地和青商量商量把那房子賣了。
於是他問:“你要多少?”
小芸說:“瞅你也沒多少錢,你給我30萬算了,算是我同情你,友情價。咱可說好,生下來做鑑定,鑑定是你的你就付錢,把孩子抱走。孩子我可不會管。”
她不管孩子,這又成了問題,他怎麼把孩子帶回家呢?
不管是給錢,還是帶孩子回家,這事兒都得跟青商量。他想了一下,青肯定生氣,但不至於跟他離婚。他老了有退休金,青沒有,到時候只能拿低保。而且這些年青知道對不起他,還從來沒有跟他生過氣。他決定回家跟青坦誠布公的說。
⑤
半夜魯樵才回去。他從來沒有回去這麼晚過,青已經睡了。他小聲喊她:“青兒,青兒?”
青迷糊著哼了一聲:“咋才回來。”
魯樵說:“跟你說個事兒。”
“啥事?明天兒再說不行?”
“你先把棍子找好,把搓板找好,我跪著跟你說。”這油腔滑調的詞兒是他在路上想好的。人好像有種慣性,剛跟嘴巴嘚嘚嘚的人在一塊說了話,轉臉自個兒也沾上點兒浮躁氣兒。
青完全清醒過來,她坐起來問:“哪兒還有搓板?到底啥事兒?”
魯樵深吸一口氣:“我說了啊。”
“說吧。”
魯樵就說了,他把這事怪罪於那天確實喝多了。然後情真意切地表達了自己想要一個孩子。最後他說孩子怎麼安置他都想好了,對外就說是魯青在外面談戀愛生的,女方不要,他兩口子給帶。
“現在私生子也可以上戶口,不用假結婚了。”他委婉提到這二十多年來他們從未提起過的事,他為自己的無恥感到心碎。
青一直不說話。她坐在那兒,呼吸聲逐漸變得很粗很大,猶如風箱。
魯樵等著她發話,時間變得空曠無涯。他也不敢直看她,他偷瞟一眼,錯開,過會兒再偷瞟一眼。青的臉漲得很紅,她需要依靠什麼東西來發洩憤怒,比如撕毀什麼,砸爛什麼,可是絕望又抑制了她。她一動不動地坐著,魯樵卻聽得見那安靜背後的哭泣和咆哮。
過了很久,青說:“我知道你是仗著我不敢和你離婚,可是你這樣汙魯青的名聲,他將來不好找物件。”
她說得很淡,一絲情緒都沒有。她剋制得這樣好,是魯樵萬萬沒有想到的。本來他想如果青跟他吵,他就不甘示弱地吵,把她欠了他所以從兒子身上補回來這種話也撒出來。但她沒有吵,她安靜而理智,他倒說不出狠話來了。
“那……”魯樵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你打我罵我都行。”
青說:“要不然你給魯青打電話,把話都說清楚,問他願不願意。這件事總得他來配合。”
魯樵嚇了一跳:“難道我把咱當年的事說出來?”
“說吧,他也成年了。”
魯樵忽然意識到這麼做的結果,是失去他已經撫養成人的魯青,失去這個優秀得體的青年,一個第一次拿工資就把錢全花在他身上的兒子。
他傻了,他忽然發現自己下午可能腦子斷了電,他一直想著他們欠了他,卻忘了他們也給了他。真讓他跟兒子決裂,他捨得嗎?
青說:“我沒有權力要求你這輩子不生孩子,所以這事,你自己看著辦吧。”
⑥
魯樵沒法收場。錯犯了,醜出了,現在老婆拋給他這麼大一個難題,或者說他自己製造了這麼大一個難題,這盤子餿菜他端不回去。
他求援的目光,都不知道投給誰。
他在床上烙了一夜餅,還是下不了決心。從青的冷漠裡,他也看到世道的殘忍。以前她愧對他,悉心照顧,還給他培養了一個好兒子。現在他想成全自己,對不起,那以前給你的,人家也要悉數收回。
魯樵想了又想,還是捨不得那個未成形的親孩子。第二天早上,魯樵厚著臉皮求青,讓她給兒子打電話,青不搭理他。以前她都是一呼百應的,魯樵知道從此以後再也不可能了。他一咬牙,自己給魯青打電話,用小得發嗡的聲音把這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魯青那邊有點吵,不知道是因為太吵還是因為他不能相信,他在電話裡一直問:“你說啥?你說啥?你說啥?”魯樵卯足了勁兒把事情反覆講了幾遍,魯青終於聽明白了。
“我得跟我媽商量,”最後他說:“我聽我媽的。”
半個小時後,魯青主動打電話過來:“我媽叫我成全你。”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不等魯樵表達愧疚,兒子就把電話掛了。
7,
芸生了個女孩。魯樵把孩子抱回來後,魯青一次沒回過家。他在單位上談了一個烏魯木齊的女朋友,很快就和女孩去了烏魯木齊。賣房子的錢,魯樵給了芸30萬,剩下的全交給青,青馬上帶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和存放她微薄尊嚴的銀行卡,馬不停蹄去了烏魯木齊。
魯青和女友在烏魯木齊買了個房子,青說要跟他們住,他們馬上要結婚,青要給小兩口帶孩子。
“那你還回來嗎?”魯樵問。
“回去。”
“什麼時候回來?”
“老了,帶不動孩子了,就回去。”
“那還得……多少年?”
“混著唄。”青說。她語氣裡是從未有過的無所謂,他們這半生的真情,在他坦白的那天晚上,已全部被勾銷。他經常會想到那個晚上,她目光裡燃燒著彤紅的憤怒,卻又暗含對權術的通曉。那個晚上改變了她,她成了一個與之前完全不一樣的女人。
魯樵一個人帶不了孩子,保姆又貴,他只好提前辦了內退,在家照顧女兒。女兒天天哭,幾乎累斷了他的老腰。鄰居都說,喲,真是模範爺爺。魯樵抱著女兒出去溜達,人人都在重複這句話,女兒聽多了,8個多月的一天,竟然咿咿呀呀地叫了聲“爺爺”。她學會的第一個詞竟然是“爺爺”。
魯樵一時間老淚縱橫。
這輩子似乎什麼都得到了,齊活兒了;又似乎什麼都失去了,空落落的。可能這就是人的一生吧,挖東牆補西牆,慾望不止,償還無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