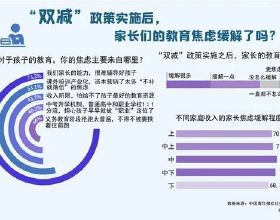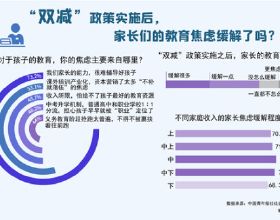殺年豬
歐陽躍親文/攝影
“年豬叫,春節到。”在臨近大年三十的那幾天,農家養壯的豬的尖叫聲開始此起彼伏,這“殺年豬”的情景成為國人春節習俗的重要一幕。
養豬過年,在缺衣少穿的日子裡,農村人家幾乎家家戶戶都要養上一兩頭豬,這也是最為傳統的秋收冬藏的農耕思想的具體體現,因為“殺年豬”的肉就是來年一家人肉食的儲備。
小時候,我家也有養豬的習慣,那時候養的是本地的土豬,我們叫它“米果豬”,個頭不是很大,但肉質鮮美,如今已經見不到那個品種了。
每年過完元宵節,父親就騎上腳踏車,後座上載著裝豬崽的篾籠出發了,早上出發直至下午才載回來活蹦亂跳的小豬崽。說是小豬崽,其實也有十來斤。對這頭關乎全家一年“油水”牲畜的到來,母親一點不敢馬虎。前半個月一日三餐頓頓是米粥和菜葉,即使是以後的日子,豬食標準雖然降低了些,但那些洗鍋的泔水、剩下的飯菜、割來的豬草必須和米糠一塊煮爛後才挑著去餵食,生怕豬崽有個“跑肚拉稀”一命嗚呼。
隨著豬崽的長大,家裡的那點泔水實在難以餵飽那“吃了睡,睡了吃”的牲畜,“打豬草”的重擔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們哥仨的頭上。
“打豬草”實際就是去池塘裡撈水浮蓮、割“革命草”、挖“馬齒莧”扯“蒲公英”這些。最奇怪的是“革命草”為什麼叫這樣的名字,長大後一查資料,才知道是20世紀30年代末日軍侵華時從北美引進的,原是作為馬料加以栽培,可這入侵物種長勢瘋狂,不僅有毒還對生態造成極大危害,似乎要“革”其他水生物種的命。
有一回初冬,我為了扯幾根離岸遠些的“革命草”,腳下一滑連人帶藍栽進了不知道有多深的水裡,連嗆了幾口髒水。好在旁邊有村裡的大人在,連忙生拉硬拽把我救了上來。人雖然沒事,但這一驚嚇讓我病了整整一個禮拜。人都吃不飽的歲月,豬生長得也很緩慢,最少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長成。
“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那時化肥並沒有普及,而種稻種菜的當家肥料全指望豬糞牛糞,農家養牛養豬的另一個主要目的也就是造農家肥。這可苦了我們這些娃,每天清晨吃早飯之前就要扛著鋤頭去田埂上削草皮,傍晚放學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用糞箕把曬乾的草皮挑回來墊平在豬圈牛欄裡。由於家家戶戶的娃都去削草皮,我們削草皮的地方離家越來越遠,晚上把草皮挑回的路途跟著越來越長,每每挑回草皮,太陽都已經下山了。
臨近冬天,我們削草皮的任務更重了。冬天的田埂不長草,儲備草皮的任務就必須在秋天完成,所以我們必須動用家裡的板車來拉草皮。於是乎,我們兄弟三人明確分工,哥負責把田埂上的草皮挑回到砂石村道上,我負責拉弟負責推用板車把草皮運回到豬圈旁並壘成垛。隨著村裡一個個草垛壘起來有一人多高時,冬天已經到了,這些草垛也就成了我們這些娃玩捉迷藏,“槍打鬼子”的“碉堡”。
一年辛苦地伺候,“養尊處優”的豬也長得膘肥體壯,“殺年豬”成為了年末最後的一件大事。
挑好“殺年豬”的吉日,請好屠夫和幫手後,父親在前一天晚上就要揣上一盒好煙,挨家挨戶去登記誰家需要買肉的數量。捨不得一頭豬全醃了,父親估摸著要留下多少作為自家食用的豬肉,多餘的則要賣掉以換些零用錢。
天剛矇矇亮,當母親燒好了一大鍋燙豬的開水時,殺豬的老師傅也到了。他擺好殺豬凳、燙豬盆、豬血盆後,便拽著一根長長的拖豬勾隨著父親和請來的幫手來到了豬圈。
前一天就沒有餵食的豬也許知道“壽終正寢”的時刻來臨,它不停地在豬圈裡打圈圈。可“再狡猾的狐狸也敵不過好獵手”,說時遲那時快,老師傅猛地一伸手,拖豬勾就勾住了豬脖子,悽慘的嚎叫頓時劃破天空。父親和四個村裡的壯漢分別抓住豬腳和尾巴把豬抬出了豬圈,一路飛奔來到殺豬凳前。
撤下拖豬勾,屠夫隨即一手抓住豬耳朵,一腿抵住豬頭,其餘的人分別摁住豬腰、扳住豬腿,扯緊豬尾巴,把豬牢牢按在大板凳上。
在豬還一直狂嚎掙扎的同時,屠夫拿出刀子朝頸部狠狠地地捅了進去,白刀子進去紅刀子拔出時,豬血噴流如注。
等豬不再動彈了,母親馬上把準備好的草紙,到豬的刀口處粘上豬血放到豬圈上,祈禱下一年養豬紅火。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燙豬、刮毛、去頭、開膛、清理、劈半、分塊。
殺豬過程中我們小孩能夠湊上熱鬧的就是踢豬尿泡了。“壞得很”的老師傅為了打發我們走,不讓我們在旁邊礙手礙腳的,就從豬身上割下尿泡扔給我們說:"來,拿著玩去吧!”捧著軟乎乎的尿泡我們幾個小孩就嘻嘻哈哈地踢著玩去了!誰的腳力要是大的話,一腳踢破就會漏出一泡豬尿水,臊得很。
殺完年豬,請吃殺豬飯是農家年味的一道盛宴。老家請吃殺豬飯必須要把爺爺、奶奶、舅舅、大伯、叔叔這些長輩請來,食材則取自剛殺的豬和地裡的新鮮蔬菜。我的印象里老家的豬腿骨燉蘿蔔是最鮮美的一道菜。
不是過年勝似過年,一頓殺豬飯,是親朋好友情感的昇華,是對生活的美好期盼。更是一種過年最快樂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