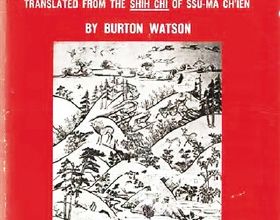淳熙九年壬寅(1182)。陸九淵從四十四歲來到臨安;匆匆已經五年。先生四十八歲了!
五年的京官生涯,使陸子成熟多了。
行都的繁華是孝宗趙昚“假備戰,真議和”的投降路線換來的;加上金朝內部矛盾,二十餘年又無戰事,相對和平時局。在西湖歌舞太平景象中,一方面是統治者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是細民百姓凍餒溝壑。儒者在中間表演,圍繞著“戰”與“和”二字,或陰或陽地暴露了各種靈魂。朝廷為了防止民變,硬手鎮壓,軟手“禮”教。繁瑣講究,花樣翻新。比如:凡地方新任的主要官員,必須用“太平之禮”先當地孔廟,方可就職。皇帝每年閱兵五次,虛張聲勢,只見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隊伍長達二十餘里,花的金銀錢帛以萬計。京城的年年春秋郊祀大禮,用銀如流水,單是擺威風的六軍儀仗隊就有二千二百三十二人。高宗趙構慶壽大典,極盡人間富貴,用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人,正樂一百八十八人。文武百官以至禁衛吏卒都要頭插鮮花朝拜賀壽。有人寫詩:“春色何須羯鼓催,君主壽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真實而又辛辣地記錄了當時的盛況。這些禮儀表面熱鬧,實質上透露了皇家的虛弱,社會的病態。另外,以陳亮為首的東事功學派,除與朱熹論戰外,又掀起“反道學”熱潮,並得到主戰派將領辛棄疾的支援。凡是推崇孔孟者都在反對之列。民族存亡之秋,“事功派”已佔上風,這也許是民族意識的部分覺醒。浙東家家“談事功”、“說王霸”,不說孔孟。朱熹驚呼“可畏!可畏!他與陳亮進行了“王霸義利之辨”。朱門弟子放鬆陸學的進攻,集中火力評“王霸”。但是,“事功派”也喚不醒小朝延,一些保守分子藉故打擊“事功派”,陳亮兩次入獄。在這夾縫中陸九淵堅持儒家立場,雖說他反對程頤派的“正統道學”;但也不允許人反孔孟,尤其是他弘揚的孟軻。他說:“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雲:道學無可攻者,採取了採取袖手中立的態度,但在思想深處有所困惑。官場黨派紛爭傾軋,孝宗亦是孱帝,自己隨時可然也有被打擊的危險。在《與尤延之》信中傾吐了自己的內心:
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著腳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睹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郁度日而已。”(《陸集》498頁)
有人勸他有小人在暗裡虎視眈眈,打他的主意,要防止明槍暗箭,你還是向朝廷請退吧?他憤慨地說:“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陸集》410頁)但是,陸氏看透了朝廷的虛偽,他曾“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陸集》496頁);因此,對“輪對也是勉強,處在“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態中。“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