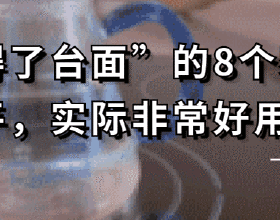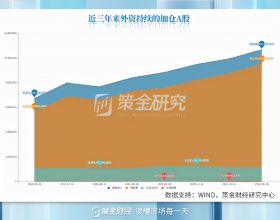本文來源:短史記
文 | 楊津濤
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尚不足一百年。
皇權與龍
在中國早期典籍中,龍通常是作為給神仙、帝王代步的交通工具出現。
如韓非子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在《山海經》裡,有“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又有“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等記述。孔子告訴弟子,黃帝“乘龍扆雲”、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這個時候,龍的地位和馬差別不大,只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①在傳說中,龍是可以被豢養,所謂“古者畜龍,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甚至能被食用。②
秦漢時期,龍的地位得到提升,與帝王身世發生聯絡。
秦始皇有“祖龍”之稱。漢高帝劉邦的出生,則被渲染為“其先劉媼……(被)蛟龍踞其上,已而有孕,遂生高祖”。
但龍與皇權之間的這種聯絡,並不穩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龍並非官祭的物件,而僅充當某種工具。如漢武帝時制定的“郊祀之禮”中,龍乃是車伕和護衛的角色。直到宋朝,宋太宗令“祭九龍”;宋真宗又令“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等諸星在天河內者,凡五十位”,龍才成為地位普通的受官祭者。
再以龍袍為例。元朝以前,龍袍並非只有皇帝能穿。依照禮法,帝王、貴族、高官在衣冠上使用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等12種紋飾,被稱為“十二章紋”。其中日、月、星辰地位最高,歸帝王獨享,至於山、龍等,諸侯、大臣也能使用。梁武帝時有人建議讓王侯用鳳凰代替龍,唐高宗時有人建議用麒麟代替龍,都因阻力過大,最後不了了之。北宋時被迫採用一種折中的辦法,允許正、從一品官員用龍,但只能是“降龍”,把“升龍”留給皇帝。③
龍成為皇家專屬是從元世祖開始的,他下令民間禁止銷售紋龍的布料。元仁宗又下令,官員服飾一律不許飾龍。但元朝規定龍是“五爪二角者”,無論民間,還是大臣都藉機鑽空子,製作或穿著只有四爪的龍紋服飾。遲至明、清,龍紋才被帝王大範圍應用在衣服用品、宮殿裝飾上。一項統計顯示,僅故宮中的太和殿,各種龍紋、龍雕中出現的龍就有13844條。甚至於故宮中的痰盂、燭臺上都繪有龍的圖案。④
龍雖然與皇權的勾連較多,但帝制時代民間百姓對龍的祭祀,卻並沒有以之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俗中,龍往往代表著一種負有具體職務的神祗,甚至以興風作浪的“惡神”的形象出現,而被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所斬殺。
聞一多發明“龍圖騰”
經元、明、清三代帝王強化後,龍成為皇室的象徵。晚清時,出於外交需要設計了黃龍旗,龍進一步成為清朝的標誌。
至於龍變為所有中國人的圖騰,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則是民國之後的“發明”。
1903年,嚴復第一次把“圖騰”這個概念介紹到中國。簡言之,“一大群人,彼此都認為有親屬的關係,但是這個親屬的關係,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認在一個特別的記號範圍內,這個記號,便是圖騰。”⑤
到抗戰前後,圖騰學說盛極一時。知識分子出於救亡目的,急於普及、論證中國的民族概念,以便讓民眾能團結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⑥
起初,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龍僅僅是中國史前眾多圖騰之一。如呂振宇認為,“馬,牛,羊,豬……林,河,山……龍,馮,蛇,風……等”都是中國的“原始圖騰”;在圖騰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的李伯玄,最重視的是鳳圖騰和玄鳥圖騰,龍圖騰僅偶爾提及。姜亮夫較早致力於論證龍是中國的圖騰,其理由是:“夏”字本義“一定是個爬蟲類的東西”,而夏的宗神禹,也是龍蛇一類。但這種觀點,既缺乏說服力,也未造成多少影響力。
聞一多是“龍圖騰”這一概念最重要的發明者。
在《伏羲考》中,聞一多說:龍“是一種圖騰,並且是隻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具體來說,“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做‘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Klan)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
聞一多對龍的定義,雖已成常識,但經不起推敲。如學者施愛東指出的那樣,首先,歷史上的龍紋不斷變化,聞一多描述的龍形象,宋朝才出現。其次,聞一多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隨意拼接、裁剪史料。第三,因材料不足,聞一多甚至常常將假設作為前提,以至《伏羲考》中充滿了“假如”“假定”“也許”“恐怕”……。⑦更為重要的是,聞一多所謂“化合式的圖騰”的發明,沒有人類學理論為支撐。⑧
這些理論漏洞,聞一多本人未必不知道,但他更注重的是現實功效。如其自述,他希望“透過解讀古代神話,讓民眾知道他們有共同的來源,以激發他們的民族意識”,以救亡圖存。至於這種“歷史知識”是否靠譜,則屬次要。
所以,聞一多需要的只是這樣一個結論:
“龍族的諸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的本位文化……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徵。”
不過,即便是“龍圖騰”的發明者聞一多,也對自己的這一發明的現實功效,是否一定良好,缺乏自信。所以,他又非常糾結地寫道:“龍鳳”在帝制時代,已成為“帝德”與“天威”的標記,“一姓的尊榮,便天然的決定了百姓的苦難”,“龍鳳”二字不禁令人“怵目驚心”,所以 ,“要不然,萬一非要給這民族選定一個象徵性的生物不可,那就還是獅子罷,我說還是那能夠怒吼的獅子罷,如果他不再太貪睡的話。”
“龍圖騰”的發明者,對究竟是做“龍的傳人”,還是做“獅子的傳人”,尚在遊移不定。
一曲走紅
聞一多在獅子與龍之間遊移不定時,美國人從背後幫忙推了一把。
《伏羲考》發表於1942年;同年,賽珍珠的小說《Dragon Seed》(龍種)在美國出版,小說描述了中國普通百姓在日軍南京大屠殺後不屈的生存狀態。米高梅公司以高價買下小說改編權,又斥巨資打造場景、服裝、道具,並組建以凱瑟琳·赫本為首的明星陣容,拍攝出了同名電影《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內容基調,受控於當時美國政府最重要的官方宣傳機構“戰時資訊辦公室”,旨在突出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向世界傳播中國抗戰的努力。《Dragon Seed》(龍種)一詞,助力了“龍的傳人”之說在中國知識界的成型。
《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出現,實際上是對晚清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龍”的醜化的一種撥亂反正(譬如,義和團事件後,紐約《世界》雜誌曾發表一幅漫畫,以一隻張牙舞爪的龍,暗示著中國對世界的威脅)。
不過,這種“撥亂反正”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隨著四九年的天地翻覆與冷戰格局的出現,“龍”再度以不友善的形象成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代稱(如1963年9月13日美國《時代週刊》以一艘載滿中國民眾及領袖的破舊龍舟為封面)。只不過,這種形象,在冷戰時期,已不能像抗戰時的《Dragon Seed》那般,被再度反饋給中國。
1978年,侯德健創作歌曲《龍的傳人》,“龍圖騰”終於如決堤之水,被所有中國人所接受。
這首歌被收入各種歌曲集。如1981年中國廣播電視臺編的《臺灣歌曲選——校園歌曲臺灣民歌》,1982年四川廣播電臺編的《廣播歌曲集》,1982年河北省群眾藝術館編的《田園新歌》等等。1988年,侯德健獲邀在春晚上演唱了《龍的傳人》,更是紅遍大江南北。有學者認為:這首歌迎合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心情”,“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共鳴”。⑨
由於侯德健的身份是出走大陸的臺灣歌手,因此“龍的傳人”這個詞在最初具有一定統戰含義,常被用來指稱兩岸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華僑。如1985年《望長城內外——愛國主義隨筆》一書中,說從臺灣駕機回大陸的黃植誠、李大維等是“龍的傳人紛紛回到了龍的故鄉”。後來這個詞在各個場合,都成為中國人的代稱。
略言之,龍最早只是皇權裝飾物(拉車)的龍,後來進化為皇權的象徵(龍袍),再後來被聞一多重新發明,始逐漸成為一種民族圖騰。
註釋
①③施愛東:《龍的政治:從通天坐騎到皇家奴役》,《民族藝術》2011年第2期。本期專題材料、觀點絕大多數來自施愛東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謝;②袁第銳:《“龍的傳人”說質疑》,《社科縱橫》1995年第2期;④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0頁;⑤⑦⑧施愛東:《龍與圖騰的耦合:學術救亡的知識生產》,《民族藝術》2011年第4期。在西方圖騰理論中,圖騰必須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東西,龍顯然不是。圖騰社會中的多數特點也並不適用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尤其是外婚制——同一圖騰的部族間不允許通婚。而在人口眾多的上古中國,顯然是無法實行外婚制的。⑥仲林:《圖騰的發明:民族主義視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⑨張伶俐、吉成名:《“龍的傳人”一說的由來》,《文史雜誌》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