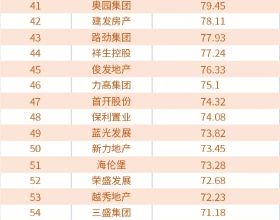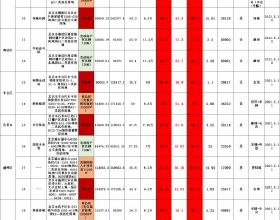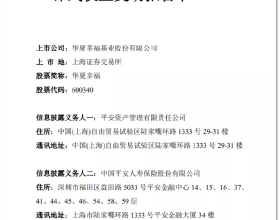|
新鋪古鎮。汪敬淼 攝 |
●丘豔榮
站在新鋪古鎮的青石板路,看著一長溜的“古韻黃”建築典雅明亮地站在石窟河畔,大紅燈籠一字排開,如一隻只時光之眼,齊刷刷地在一樓店鋪伸出的屋簷下張望,一眼千年。是啊,新鋪不新,它已存在千年;新鋪不老,它依然充滿活力。
此刻,我想推開那扇厚重的老木門,踩一踩吱呀作響的舊木梯,探訪一段關於新鋪古鎮的歷史。
依稀記得阿爸對小時候的我說過的新鋪,雖然只有隻言片語。我記住了新鋪水邊的房屋,牆裡面的三合灰攪拌進了紅糖、糯米飯;我記住了新鋪古鎮的河面有千帆百舸,穿梭往來;我記住了曾祖父和祖父從這裡登船遠航下南洋……
新鋪,舊稱蓼陂鄉,望文生義,是不是因為有許多蓼花靠水而居而得名?我不得而知。有記載的是:新鋪是相對“舊鋪”而言的,舊鋪始建於明朝年間,位於現在新鋪鎮的南面約2公里處的象嶺胡坵墩的河邊,因該處地勢較低,常受水浸,後來遷至馬鞍山下的坡地上建店鋪,故名新鋪。
新鋪古鎮前傍溫婉的石窟河,後依連綿的群山,一如明朝詩人朱權筆下的詩句:“遠山凝翠疊青蘿,秋水芙蓉映碧波”。憑欄遠眺,石窟河水平如鏡,不算寬的河面上只有一葉打撈河面垃圾的小舟在悠悠漂流。我想象不出這裡曾經是閩粵贛古驛道(水路)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能容納竹筏、木船、小火輪和重噸大船自由穿梭。照理來說,千年前石窟河的河面一定遠比今天要寬闊。滄海桑田,也是正常。碼頭上拴纜繩的攬樁空空如也,纜樁上並沒有拴著船。如今,它們的裝飾意義遠遠超過了實用意義。
歷史的長河裡,這些纜繩或者曾經拴住過一位叫李綱的千年前的歷史名人,邀請他在新鋪暫作停留。這位李綱,就是留下千古愛國名言的宋代名臣。宋朝末年,北方民族進犯,昏聵無能的宋徽宗倉促讓位欽宗,慌忙出逃鎮江。李綱竭力反對南逃,主張堅決抵抗。他奏言欽宗:“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據他所著的《梁溪先生文集》載,他當年就曾從江西贛州沿新鋪這個古驛道前往潮州府。須臾之間,平靜的河面捲起歷史的巨浪,浪濤拍響這千年以來依然鏗鏘有力、振聾發聵的聲音。
歷史的長河裡,流傳著一個將近百年的故事。1929年紅四軍於10月25日凌晨從蕉城出發進軍梅縣,取道新鋪。紅四軍進入新鋪圩後,朱德嚴令部隊不準驚擾百姓,戰士們全部沿街席地而坐。紅四軍請一名叫陳文明的大膽青年商人沿街敲打銅鑼,口喊告示“我們是紅軍,不是土匪,我們是打土豪的人民軍隊,不欺壓百姓。請大家不要驚慌,照常做生意,我們買賣公平……”躲在家裡、店鋪和山間的民眾不復恐懼,紛紛出山出門開鋪照常生活。得民心者得天下。新中國成立後,新鋪成立了諸多工會組織和商會組織,為祖國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新鋪古鎮最主要的街道是河唇古街。古街寬不過3米,長不過千米,一頭連著歷史,一頭連著現在。熙熙攘攘的古街上騎樓林立,店鋪井然,黃牆黛瓦,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脫脫“吳門四家”筆下的風景畫。然而,街上的汽車摩托、路面上的交通標識,穿著摩登拿著手機掃二維碼付款的顧客讓你一下子回到了現代。偶爾哪一扇窗戶飄出一段二胡演奏的古曲,“不知今夕何夕”的時空錯位感又席捲而來。樂聲繞著古街的雕花窗戶繚繞回旋,如一群忽飛忽落的小鳥,撞擊昨天和今天。
“樓下店鋪,樓上住戶”,是新鋪古鎮千年來延續的風格。白天把店門敞開,將自家制作的簸箕、竹椅、釀粄,煎粄,手工肉丸和滷香雞爪往門前一擺就是臨街旺鋪。無須叫賣,自有赴圩的鄉親各取所需,順便互道幾句家常。當天的貨賣完,該下地就下地,該下棋就下棋,該講牙舍就講牙舍(“講牙舍”,客家話,指閒聊)。晚上,鋪門一關,便把白日的喧鬧、忙碌和繁華隔絕開來,此時,家人閒坐,燈火可親。這樣的生活方式也延續到今天。在這裡,“不夜城”只是概念上的,形式上的,雖然也有徹夜通明的路燈,但路燈和古鎮的節奏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習慣是烙在骨子裡的。路燈的眼早已是朦朧醺然的啦!
於是,便不再執著於遠方的鳳凰古城,同裡古鎮和雲南麗江,就近來新鋪古鎮走一走,剪一段時光,在石窟河看一回日出日落,在河唇街尋一味人間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