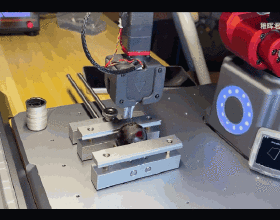號主的話:這篇採訪是摘自《風雲人物採訪記》這本書,譯者是三位從事外事廣播的老前輩。我只是轉載一下,好和之前的那篇採訪霍梅尼的做一對比。這篇採訪寫於1973年10月,和之前的那篇採訪剛好時隔6年。彼時的小巴列維,還是雄心滿滿,一心要把伊朗打造成世界第五強國。可造化弄人,雄心偉業展眼成空。其中是非原因,有諸多學者政客進行過分析,這裡不必贅述。從這兩篇採訪中,可以看出一點兩人個性的不同。關於民主自由、女性權利等西方珍視的價值觀,對待左翼人士和共產黨人的態度,兩人的回答也值得回味。如果有時間,我會把自己的一些讀後感也寫出來,跟大家一起探討。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1919年 10月 26日生於德黑蘭。他的父親於 1925年成為波斯的沙赫(伊朗國王的稱號),和德國納粹保持友好的關係。 1941年,同盟國迫使其父親流亡國外,並說服穆罕默德·禮薩成為沙赫。幾年中,他掌握了所有的權力,推行一項有利於美國的經濟政策,允許多國公司開發國家的資源,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堪忍受他的專制制度和秘密警察的鎮壓。 1978年末,爆發了反抗運動。 1963年因謀反而被流放到國外的霍梅尼回到了波斯,軍隊站到了他的一邊。 1979年,沙赫被迫離開國家,逃往美國,吉米·卡特給予了他政治避難權。為了解決追隨霍梅尼的伊斯蘭學生綁架在德黑蘭使館的美國人質的問題,穆罕默德·禮薩接受了埃及總統薩達特的接待。 1980年 7月 27日,他在開羅去世。
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和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1949 年 11 月。
國王站在他用來做辦公室的華麗的大廳中央等我。我對他接受採訪表示感謝,但他置之不理,只是默默地、非常冷淡地向我伸出了右手。他握手時是失禮的、刻板的,向我讓座時顯得更為刻板。在這個過程中,他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露出一絲笑容。他的嘴唇緊閉,像一扇關著的大門,他的眼神冷淡,像冬天的寒風。也許您會說他一定有什麼我所意料不到的事情要責備我,或者他這種拘謹僅僅是出於羞怯或由於擔心失去國王的儀表。當我坐下來時他也坐下了。他兩腿併攏,雙臂交叉,上身挺直(我猜想這是由於他像塞拉西皇帝一樣總是穿著防彈背心的緣故)。
當我向他敘述我在大門口遭到保鏢們的阻攔,幾乎沒能進來時,他仍然這樣直挺挺地、冷漠地凝視著我。我好不容易才聽到了他的聲音。他說,他對此深感遺憾,但某些偏差的產生是由於過分的忠心。他的聲音既憂鬱又顯得疲勞,幾乎是一種無聲的聲音。此外,他的表情也是既憂鬱又疲勞的。在稠密得像戴了一頂皮帽子似的白髮下面,最顯眼的是他的大鼻子。至於他那裹在灰色的雙排扣上衣裡面的身軀,看來是十分虛弱和單薄的。我禁不住問他,是否身體欠佳。他回答說,很好,從來沒有這樣好過。他說,關於他的健康受到威脅的訊息是沒有根據的。至於體重下降是他本人的願望,因為前一個時期他有點兒發胖。由於開始時的嘗試失敗了,為了活躍談話的氣氛,我當時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氣。現在我想起來了,直到我問他我能否吸菸,並說明我對此已經渴望了半小時的時候,我的努力才算奏效。“您早就可以提出來。我不抽菸,但是喜歡菸草的氣味,煙的氣味。”茶送來了,用的是金盃和金匙。室內的一切幾乎都是金制的:使人擔心把它弄髒的金菸灰缸,鑲有翡翠的金盒子,鑲滿了紅寶石和藍寶石的金制小擺設,還有四角包金的小桌子。在這個既荒唐又令人難以忍受的,充斥著金子、翡翠、紅寶石和藍寶石的光彩奪目的環境中,我待了將近兩小時,試圖去了解國王。後來,當我懷疑自己可能一無所獲時,我要求同他再談一次。他同意了。第二次會見是在四天以後。這一次他對待我比前一次親切些。我猜想是為了使我高興,他繫著一條使人難以忍受的義大利領帶。談話進行得很順利。只是當他擔心在他的警察局的黑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時,他才表現出侷促不安來。我在提問時說到,在尼克松訪問期間,我寫的關於越南的書被德黑蘭的書店列為禁書,引起了他的擔心。剎那間,他被這個訊息震動了,就好像他的防彈背心被匕首捅穿了一樣。他的目光變得不安和含有敵意。天哪,難道是一個危險分子嗎?過了幾分鐘,他才決定以唯一可行的辦法來擺脫他的這種窘態。他那過分的威嚴收斂了,露出了笑容。在微笑中,我們談到了他所信奉的專制政權,他同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以及他的石油政策。是的,我們什麼問題都談到了。我只是在回去以後才發現,我們唯一沒有談到的是他的狂妄。人們認為是這種狂妄使他產生了苦惱,而他內心的殘忍似乎也是由這種狂妄產生的。我還發現我對他這個人瞭解甚少,也許比以前瞭解得更少了。儘管經歷了三小時的問答,此人對我仍然是個謎。例如,他到底是白痴呢,還是個聰明人?也許像布托一樣,他是一個集中了各種自相矛盾因素的人物,是一個可供你探究的謎。例如,他相信夢是一種預兆,相信幻象和一種既幼稚又神秘的謬論,可是一討論到石油問題又像一位專家(他確是一位石油專家)。又例如,他像專制君主那樣統治他的國家,但在向他的臣民講話時,卻又使用相信人民和熱愛人民一類的字眼。他領導了一場白色革命,似乎為掃除文盲和反封建制度做了若干努力。他認為衡量女人的標準應該是她們動人的美貌,認為女人不會像男人那樣思維,然而他卻在一個女人還戴著面紗的社會里命令姑娘們去服兵役。那麼這位 32年來一直穩固地坐在世界上最發燙的寶座上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究竟是何許人?他屬於飛毯時代,還是計算機時代?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還是阿巴丹油井的附屬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會厚顏無恥地撒謊:當我的採訪記發表後,禮薩·巴列維讓伊朗駐義大利的大使出面,否認他曾向我講過要提高石油價格的話,而在幾星期後,他卻又提高了石油價格。我還知道他是一個陰險的獨裁者,受到人民對一切陰險的獨裁者必然懷有的憎恨。伊朗的監獄裡擠滿了政治犯,為了解決擁擠的問題,他不得不每隔一個時期就槍斃一大批人。
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和法拉赫·迪巴皇后與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第一夫人。1973 年 7 月。
法拉奇:陛下,首先我想談談關於您和您的國王職業。現在世界上剩下的國王已寥寥無幾,而我總是不能忘卻您在一次談話中說過的話:“如果我能夠從頭做起,我願當小提琴手或外科醫生、考古學家、水球選手……什麼都可以當,就是不當國王。”
巴列維:我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但是,如果我說了這樣的話,那是為了說明國王是一種令人頭疼的職業,因此往往身為國王而討厭當國王。我也是這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會退位,因為我對自己是一個負有什麼使命的人和我所做的事情充滿信心。請注意……當您說當今只剩下寥寥無幾的國王時,您暗示了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有一個,即:沒有君主政體就會有無政府主義、寡頭政治或獨裁政權。無論如何,君主政體是唯一可能治理伊朗的方式。我所以能夠為伊朗做點事,甚至做很多事,應歸功於我是國王這一事實。幹事情需要權力,但使用權力時不必徵得任何人的同意,不必向任何人徵求意見,決定問題也不必與任何人討論……當然,我可能犯錯誤,我同樣是凡人。但是我知道我肩負著需要我去徹底完成的使命,我打算在不放棄我的王位的情況下完成我的這個使命。很明顯,我不能預卜未來,但是我深信伊朗的君主政權將比你們的政權更持久。或者,我應該說,你們的政權長不了,而我們的政權將能持久。
法拉奇:陛下,有多少次他們企圖殺害您?
巴列維:正式的有兩次。再說……只有真主才知道。那又怎麼樣呢?我並不為可能被謀害而憂心忡忡。真的,我不去想它。過去曾經想過,那是 15年或 20年前的事。我曾警告自己說:“啊,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也許有人要謀害我,要暗殺我。啊,為什麼乘那架飛機?也許有人放了炸彈,在飛行途中把我炸死。”現在我不再這樣想了。我再也沒有怕死的念頭,這與勇氣無關,也不是為了挑戰。這種平靜來自一種宿命論,來自盲目的信念。我相信在我沒有完成我的使命以前不會發生任何不幸的事情。是的,我將一直活到完成了我應該完成的使命的那一天。那一天將由真主來決定,而不是由那些要殺害我的人來安排。
法拉奇:陛下,那麼您為什麼如此憂鬱?也許我錯了,但是您看來總是那樣憂傷和悶悶不樂。
巴列維:也許您觀察對了。在內心深處,我也許是一個憂傷的人,但我認為我的憂傷是神秘的,這種憂傷是由我的神秘的一面決定的。鑑於不存在任何會使我憂傷的理由,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解釋。作為一個人,或作為一個國王,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我確實得到了一切。我的生活簡直美極了。世界上不會有人比我更加幸福,然而……
法拉奇:然而,在您臉上露出一絲歡樂的微笑要比在天上出現一顆流星更為難得。陛下,您從來不笑嗎?
巴列維:只有當我遇到可笑的事,而且確實是十分可笑的事、真正可笑的事時,我才笑。這樣的事是不會經常遇到的。不,我不是對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發笑的人,您要知道,我的生活始終是那麼艱難,那麼勞累。您只要想一想我最初執政的 12年忍受的一切就行了。 1953年羅馬……摩薩臺……您記得嗎?我這裡並未涉及我個人的痛苦,我指的只是作為國王的痛苦。當然我也不能把個人和國王分開。但在考慮個人以前,首先應該考慮到我是一個國王。而作為國王,他的命運是受他所要去完成的使命所支配的。其他的一切都無關緊要。
法拉奇:天哪!這肯定是一件極為令人煩惱的事。我的意思是說,當國王一定會感到十分孤獨。
巴列維:我不否認我的孤獨。十分孤獨。作為一個國王,不能向別人傾吐他的肺腑之言或道出他胸中的謀劃,他必然會感到十分孤獨。但是我也不完全孤獨,因為陪伴我的有其他人看不見的力量,我的神秘的力量。我從中得到啟示,宗教的啟示。我非常虔誠。我相信真主,而且我一向認為,如果不存在真主,那麼就應該創造一個真主。啊!我為那些可憐的不信真主的人感到惋惜。人活著不能沒有真主。從我 5歲那年起,也就是從真主向我顯聖那時起,我就和真主共存。
法拉奇:陛下,顯聖?
巴列維:顯聖,是的。顯聖。
法拉奇:是什麼東西?是誰?
巴列維:是穆罕默德。啊,您竟不知道這件事?這使我感到很驚訝。關於我遇到了真主顯聖的事,盡人皆知,而且在我的自傳中也有所記載。在我幼年時,我遇見過真主顯聖,共兩次。第一次在我 5歲的時候,另一次在我 6歲的時候。第一次我見到了我們的阿里·穆罕默德。根據我們的宗教,他已經死去,但他要在拯救世界的那天重返人間。一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摔倒了,快要撞在一塊岩石上,這時,他擋住了岩石,使我得救。我知道我為什麼能見到他。那不是在夢中,而是在現實中,是在現實生活裡。我說明白了嗎?當時陪同我的人什麼也沒有看見。除了我以外,誰也不應該看見,因為……啊,我擔心您不明白我所講的。
法拉奇:事實是,陛下,我一點也不明白。我們一開始談得很好,而現在……這個關於顯聖的故事……我不明白就是了。
巴列維:那是因為您不相信。您既不相信真主也不相信我。很多人不相信這件事。我的父親也不相信。他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他總是譏笑這件事。許多人還畢恭畢敬地問我是否懷疑過這可能是幻覺,是孩子的幻覺。我回答說:不,不是幻覺,因為我相信真主,相信我是被真主選擇來完成某項使命的人。我看見的真主顯聖,是拯救國家的奇蹟。我實行君主政體拯救了國家,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我身邊有真主。我的意思是,不應該說我為伊朗做的好事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儘管我可以這樣說,但是我不願意這樣說,因為我的背後還有別的人,有真主。我說清楚了嗎?
法拉奇:陛下,沒有。因為……總之,您只是在童年時遇到過真主顯聖嗎?成年後是否也遇到過?
巴列維:只是在童年,我已經說過了。成年後我再也沒有遇見過真主,只是夢見過。每隔一年或兩年夢見一次,有時七八年夢見一次。比如我曾經在 15年中做過兩次這樣的夢。
法拉奇:陛下,什麼夢?
巴列維:宗教的夢,是根據我的神秘主義做的夢。夢中,我見到了要在兩三個月以後發生的事。後來,事情真的如期發生了。至於是什麼樣的夢,我不能告訴您。不是關於我個人的夢,而是涉及伊朗國內問題的夢,因此是國家機密。要是把夢改稱為預感也許您更能明白。我也相信預感。有些人相信轉生,我相信預感。我不斷產生預感,它像我的直覺一樣強烈。那一次,當有人在距我只有兩米的地方向我開槍時,也是直覺救了我。當兇手開槍時,我本能地做了一個拳擊動作。由於在槍口就要對準我的胸膛的一剎那我移動了一下身子,子彈只打中了我的肩膀。這是一個奇蹟。我也相信奇蹟。您再想一想另外一次,我被五顆子彈打傷,一顆打在臉上,一顆打在頭部,兩顆打在身上,而最後一顆子彈由於扳機失靈而留在槍管中……應該相信奇蹟。我多次遭遇過飛機失事,但我總是安然無恙:那是真主和穆罕默德創造的奇蹟。看來您不相信。
法拉奇:不僅不相信,而且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把我弄得非常糊塗。陛下,這是因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出乎我預料的人物。我對這些奇蹟和顯聖一無所知……我到這裡來是為了談論石油、伊朗和您……還有您的婚姻,有關您離婚的問題……這不只是為了換換話題,而是因為那些離婚的經歷都是非常戲劇性的。陛下,是嗎?
巴列維:很難這樣說,因為我的生活是由命運支配的。當我不得不傷害我個人的感情時,我總是以命中註定要痛苦的想法來自我安慰。當一個人要去完成所肩負的使命時,他不能違抗命運。對一個國王來說,他的個人感情算不了什麼。一個國王從來不為自己哭泣,他沒有這個權利。國王首先考慮的是責任,而這種責任感在我身上是如此強烈,以致當我的父親叫我“去娶埃及的法齊婭公主為妻”時,我根本沒有打算提出異議或者託詞“並不認識她”。我馬上表示同意,因為立即加以接受是我的責任。決定這一點的因素是,你是否處於國王的地位。如果是,那就應該承擔國王的一切責任和重擔,而不能屈從於遺憾和奢望以及凡人的痛苦。
法拉奇:陛下,我們且不談法齊婭公主,我們來說說索拉婭公主。是您自己選中她為妻子,難道遺棄她對您不痛苦嗎?
巴列維:嗯……是的……在一段時間內,是痛苦的。我甚至可以說,在一段時間內它是我生命中最不愉快的事情之一。但是理智很快佔了上風,我問我自己:為了我的國家我應該做什麼?回答是:再尋找一位能與我休慼與共並能使王位繼承人得到保證的新娘,也就是說我的情感從來不放在個人的事情上,而只傾注在王室公務上。我一向教育自己做一個不關心自己,只關心國家和王位的人。我們不要再談論那些事,比如有關我的離婚。對那些事我不感興趣,根本不感興趣。
法拉奇:陛下,當然是這樣。可是為了澄清問題,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您提出。陛下,您又娶了一位妻子,是真的嗎?自從德國報紙刊登這條訊息以來……
巴列維:是誣衊,不是訊息。某巴勒斯坦報紙出於明顯的政治目的首先刊登了這個誣衊性報導,接著法國報刊也廣為報導。這是愚蠢、卑鄙和可憎的誣衊。我只告訴您一點,那張被說成是我第四個妻子的照片是我外甥女的照片,也就是我孿生妹妹的女兒的照片。我的外甥女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兒子。是的,一些報刊為了詆譭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它們這樣做得到了一些肆無忌憚、毫無道德的人的支援。是我要求在法律上規定男人只允許娶一個妻子,他們有什麼理由說我又娶了妻子,並且是秘密地娶了妻子呢?簡直不可思議,不能容忍,太不光彩了。
法拉奇:陛下,可是您是伊斯蘭教徒。您的宗教允許您在不廢黜法拉赫·迪巴王后的情況下,再娶一個妻子。
巴列維:是的,是這樣。根據我的宗教,只要王后同意,我可以這樣做。老實說,應該承認存在某些情況……比如妻子病了,或者她不願盡妻子的義務,給丈夫帶來不愉快……只有偽君子或者幼稚的人才相信這是丈夫所能忍受的。在你們的社會里,如發生此類情況,難道丈夫不去找一個或幾個情婦嗎?而在我們的社會里,只要取得第一個妻子和法院的同意,丈夫就可以再娶一個妻子。需要這兩方面的同意,這是我的法律的規定,否則,丈夫是不能再結婚的。為什麼我,偏偏是我要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偷偷地去結婚?跟誰結婚?跟我的外甥女?跟我妹妹的女兒?聽我說,如此庸俗的事,我連談都不願談。我不同意再談論這件事。
法拉奇:好吧,我們不再談論這件事。我們就說您否認這一切,陛下……
巴列維:我什麼也沒有否認。我都懶得否認。我不願在一項闢謠宣告中提及我。
法拉奇:什麼?如果您不否認,人們會繼續說這確有其事。
巴列維:我已經透過我的使館否認了。
法拉奇:沒有人會相信。陛下,必須由您自己來否認。
巴列維:可是親自否認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失身份,將冒犯我的尊嚴,因為這件事對我一點也不重要。您認為像我這樣處於萬人之尊的君主,像我這樣一個日理萬機的君主,不顧自己的身份親自去否認與他外甥女結婚的事合適嗎?討厭!討厭!您認為一個國王,一位波斯的皇帝,把時間浪費在談論某些事情上,浪費在談論妻子、女人問題上合適嗎?
法拉奇:奇怪,陛下,如果說,人們常常把他與女人聯絡在一起的那位君主恰恰就是您,那麼我現在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女人在您的生活中是否絲毫沒有地位?
巴列維: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您的觀察是正確的。因為在我生活中佔重要地位的事情,在我身上留下痕跡的事情,不是我的婚姻或女人,而是與此迥異的其他事情。女人,您知道……好吧,我們就這樣說吧,我不低估她們,實際上她們在我的白色革命中受益最多。為了使她們在社會中平等地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我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我甚至讓她們服役,在軍隊裡受訓六個月,然後把她們送到農村去從事掃盲工作。請不要忘記,我是在伊朗摘掉婦女面紗的人的兒子。但是,如果我說我受她們中間某一個人的影響,那麼我是不真誠的。沒有人能影響我,沒有人,女人更不能影響我。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有美麗、可愛和保持女性美的女人才有她們的地位……拿爭取女權運動來說,這些女權主義者想要什麼?你們要什麼?你說要平等。啊!我不想顯得無禮,但是……在法律上你們得到了平等,但是對不起,在能力方面同男人仍然不一樣。
法拉奇:陛下,不一樣嗎?
巴列維:不一樣。你們中間從來沒有產生過米開朗琪羅或巴赫,甚至沒有出過名廚師。如果你們對我說這需要機遇,我就回答你們:開什麼玩笑?難道在歷史上缺少產生一個名廚師的機遇嗎?你們成不了大事,成不了!請告訴我:在您的採訪過程中,您認識了幾個善於統治的女人?
法拉奇:陛下,至少是兩位:果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
巴列維:嗯……我能說的唯一的一點是,一旦女人當政,她們就比男人強硬得多,殘酷得多,更加嗜血成性。我說的是事實而不是看法。當你們手中有權時就喪失良心。您想想卡特琳·美第奇,俄國的葉卡捷琳娜,英國的伊麗莎白。更不用說你們的盧克雷齊婭·博爾賈和她的毒藥、陰謀。你們詭計多端,一肚子的壞水。你們都是這樣。
法拉奇:陛下,我感到很驚訝。記得您做過這樣的決定:如果王儲在成年前登基,那將由法拉赫·迪巴王后攝政。
巴列維:嗯……是這樣……是的,如果我的兒子在達到規定的年齡以前就當國王,那麼法拉赫·迪巴王后將成為攝政者。但是她應同一個顧問機構商議事情,而我就沒有義務需要與任何人進行這種商議,我也不和任何人商議。您看到了兩者的區別了嗎?
法拉奇:看到了。但是您的妻子有可能攝政,這是事實。陛下,您既然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就意味著您認為她有能力攝政。
巴列維:嗯……不管怎樣,這是我在作出決定時的看法……我們在這裡不是僅僅為了談論這件事,是嗎?
法拉奇:當然不是,陛下。何況我還沒有開始向您提出我最迫切需要知道的事。例如:當我試圖在這裡——德黑蘭談論您時,人們驚恐萬狀,默不做聲。他們甚至不敢提您的名字,陛下,這是為什麼?
巴列維:我想是由於過分的崇敬。事實上,他們見到我時並不這樣。那次我從美國回來,乘坐了一輛敞篷汽車穿過德黑蘭城,從機場到皇宮,至少有 50萬狂熱的群眾夾道歡迎我。他們高喊萬歲,高呼愛國主義的口號,一點兒也不像您所說的那樣默不做聲。自從我擔任國王以來,也就是從我的汽車被人們抬了五公里的那一天以來,情況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是的,從我的住處到我去宣誓忠於憲法的大廈之間有五公里的路程。我坐在那輛汽車裡,汽車開動了幾米以後,人們就像抬轎子那樣把汽車抬了起來,一直抬了五公里。您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想說大家都反對我?
法拉奇:上帝不允許,陛下。我想說的也就是已經說過的:在這裡,德黑蘭,人們是那麼害怕您,以至不敢提您的名字。
巴列維:他們為什麼要同一個外國人談論我?我不清楚您講這話的意思是什麼。
法拉奇:陛下,我講的是事實。很多人把您看做獨裁者。
巴列維:那是《世界報》說的。這種說法對我有什麼關係?我為我的人民工作,而不是為《世界報》工作。
法拉奇:是的,是的,但是您否認您是一位專橫的國王嗎?
巴列維:不,我不否認,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專橫的。但為了實行改革,你不得不專橫。特別是在一個像伊朗這樣只有 25%的人能看書寫字的國家裡進行改革更是如此。不要忘記這裡文盲多得駭人聽聞,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說的還不是徹底掃除一切文盲,我說的只是在 50歲以下的人中間掃除文盲。請相信我以下的見解:當一個國家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既不會看書也不會寫字時,那麼改革只能在最嚴厲的專橫方式中進行,不然就會一事無成。如果我不嚴厲,那麼我甚至無法進行土地改革,而且我的整個改革計劃將無法實施。而一旦計劃落空,極左派就會在幾小時內消滅極右派,不僅如此,白色革命也將宣告破產。我這樣做事情都是不得已的。比如命令我的軍隊向反對分配土地的人開槍。為此有人說在伊朗沒有民主……
法拉奇:陛下,有民主嗎?
巴列維:我向您保證有民主,我向您保證從很多方面來說,伊朗要比你們這些歐洲國家民主得多。除了農民是土地的主人,工人參加管理工廠,大的企業屬於國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以外,您應該知道,這裡的選舉從村莊開始,並且在地方、城市和省的各級機構中進行著。是的,在議會里只有兩個黨。但是這兩個黨都接受我的白色革命的 12條,那麼還需要有多少黨來代表我的白色革命的思想?此外,這裡僅僅兩個黨就掌握了足夠的選票:少數派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如此的可笑,以至不可能選出一個代表來。不管怎樣,我不願意少數派選舉代表,就像我不願意共產黨存在一樣。在伊朗,共產黨員是非法的。他們一心想搞破壞,破壞,破壞。他們向其他人表忠心,而不向他們的國家和國王表忠心。他們是叛徒,如果我允許他們存在,那我簡直是瘋了。
法拉奇:陛下,也許我沒有說清楚。我指的是我們西方人所說的民主,也就是指我們的那個政權,它允許人們自由地思考問題,並且建立在少數派也有其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基礎上……
巴列維:我不要這樣的民主!您還不明白嗎?我不知道這樣的民主對我有什麼用!我把它贈送給你們好了。你們可以把它珍藏起來,明白了嗎?你們的絕妙的民主!再過幾年你們將發現你們那絕妙的民主會走到哪裡。
法拉奇:是的,也許有點混亂。但是,這是尊重人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巴列維: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民主,民主!讓 5歲的娃娃去罷工,去遊行,這是民主?這是自由?
法拉奇:是的,陛下。
巴列維:我看不是。我再請問您:最近幾年來,在你們的大學裡究竟唸了多少書?如果你們的大學裡繼續不念書,那麼你們怎麼能跟上技術發展的步伐?由於缺少知識,你們不會成為美國的奴僕嗎?你們不會變成三等,甚至四等國家嗎?民主,自由,民主!這些詞意味著什麼?
法拉奇:陛下,請原諒,如果您允許我解釋的話,我認為這些詞意味著:當尼克松來德黑蘭訪問時,不從書店裡拿走某些書籍。我知道我寫的關於越南的書在尼克松來訪時被從書店裡拿走,在他走後又被放回去。
巴列維:什麼?
法拉奇:是這樣,是這樣。
巴列維:但您不是黑名單上的人吧?
法拉奇:在德黑蘭?我不知道。也許是的。我的名字被列入了所有的黑名單。
巴列維:嗯……因為我在王宮接見您,就在這裡,坐在我的身邊……
法拉奇:陛下,您這樣做是非常客氣的。
巴列維:嗯……當然,這證明這裡有民主、自由……
法拉奇:是的。但我想問您一件事,陛下。我的問題是:如果我不是義大利人而是伊朗人,如果我在這裡生活,按我現在想問題的方式去想問題,按我現在寫文章的方式去寫文章,也就是說批評您,那麼您會把我投進監獄嗎?
巴列維:有可能。如果您所想的和您所寫的東西不符合我們的法律的話,您就要受審。
法拉奇:是嗎?還要被判刑?
巴列維:我想是的,這很自然。就我們之間來說,我認為您要在伊朗批評我和攻擊我是不容易的。您為什麼要攻擊我,批評我?因為我的對外政策?因為我的石油政策?因為我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因為我允許工人可以得到 20%的紅利?允許他們可以購買 49%的股份?因為我對文盲和疾病進行了鬥爭?因為我使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前進了?
法拉奇:不,不。陛下,不是因為這些。我要攻擊您的是……讓我想一想,對了,是因為在伊朗,學生和知識分子受到鎮壓。有人告訴我,由於監獄裡擁擠不堪,不得不把抓來的人關在兵營裡。是真的嗎?目前在伊朗有多少政治犯?
巴列維:確切的數字我不知道。這要看您指的政治犯的含義是什麼。如果您指的是共產黨員,那麼我並不把他們看做政治犯,因為根據法律,共產黨員是非法的。因此,對我來說,共產黨員不是政治犯而是普通罪犯。如果您指的政治犯是那些因搞暗殺,從而使無辜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受到傷害的人,那更明顯,我也不把他們看做政治犯。實際上我對他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我一向寬恕企圖謀害我的人,但是我對你們稱之為游擊隊員的罪犯或賣國賊不發任何慈悲。他們是一些既會殺死我的兒子,又會陰謀破壞國家安全的人。這樣的人應該被消滅。
法拉奇:您把他們槍斃了,是真的嗎?
巴列維:那些殺了人的傢伙,當然要槍斃。但槍斃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而是因為他們是恐怖分子。共產黨員只是被判幾年到很多年的徒刑。哦,我能想象你們是怎樣看待死刑這類事的。但是請注意,怎樣看待事物取決於人們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文化程度和所處的環境。不能認為在一個國家行得通的事在所有的國家都行得通。把一顆蘋果的種子種在德黑蘭,然後再把同一個蘋果中的另一顆種子種在羅馬,在德黑蘭長出來的蘋果樹同在羅馬長出來的蘋果樹絕對不會一樣。在這裡槍斃一些人是對的,是必要的。在這裡發慈悲是荒唐的。
法拉奇:陛下,在聽您談話的過程中,我一直有個疑問:您對阿連德的死是怎麼看的?
巴列維:我認為他的死給我們上了一課。如果誰想真的乾點事情並希望取得成功,那就必須明確地站在這一邊或者那一邊,採取中間路線和妥協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要麼當革命者,要麼尋求秩序和法律。想要儲存秩序和法律就不能成為革命者,容忍更不行。如果阿連德要以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治理國家,那麼他為什麼不重建社會秩序?當卡斯特羅上臺時,至少殺了一萬人。而你們卻對他說:“好樣的,好樣的,好樣的!”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真是好樣的,因為他還在臺上。但是,我也在臺上,我想繼續留在臺上以說明依靠強力是可以幹很多事的,甚至可以證明你們的社會主義完蛋了。陳舊,過時,完蛋了。 100年前人們談論社會主義,是 100年前寫下的東西。今天它已不符合現代技術的要求。我在這方面乾的事要比瑞典人多。難到您沒有看見,在瑞典,社會黨人也在喪失地盤嗎?啊,瑞典的社會主義……在那裡,森林和水源還沒有國有化,而我已經做到了。
法拉奇:陛下,我又不明白了。您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您是社會主義者,而且您的社會主義要比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主義更先進、更現代化?
巴列維:肯定是這樣。因為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保障那些不勞動的人到月底照樣跟勞動的人一起領取工資的制度。而我的白色革命的社會主義是刺激勞動的。這是新穎的、有獨到見解的社會主義……請相信我:我們伊朗要比你們先進得多,我們確定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向你們學習。關於這些事,你們歐洲人從來不予報道。國際新聞界滲透了如此之多的左派,所謂的左派。啊,這些左派!他們甚至腐蝕了神職人員,甚至腐蝕了神甫們!連神甫們也成了只搞破壞的搗亂分子。他們除了破壞,還是破壞!甚至在拉丁美洲國家,在西班牙也是如此!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濫用自己的教會,自己的教會!他們談論不公正、平等……啊,這樣的左派!等著瞧吧,看他們會把你們引向哪裡。
法拉奇:陛下,我們再來談談您吧。在那憂傷的面孔背後,您是那樣寸步不讓,那樣強硬,甚至無情。說到底,您與您的父親是如此的相像。不知您父親對您的影響有多大。
巴列維:沒有任何影響。我的父親也不能影響我。我已經對您說過,沒有任何人能影響我!是的,我與我父親在感情上聯絡很密切。是的,我很欽佩他,僅此而已。我從來沒有企圖抄襲他的經驗,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我想這樣去做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而且我們所面臨的歷史條件也很不相同。我的父親是從零開始的。他上臺時,國家一無所有,甚至不存在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邊界問題,特別是與俄國人之間的邊界問題。我的父親能與各國都保持睦鄰關係。說到底,當時唯一的威脅是英國人,他們於 1907年同俄國人瓜分了伊朗,希望伊朗成為介於俄國和屬於英國的印度帝國之間的一塊不屬於任何人的領地。後來英國人放棄了這個計劃,這對我父親來說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我,而我……我不是從零開始的,我有王位。但是,我剛登基便發現我得去領導一個被外國人佔領的國家。我那時只有 21歲。 21歲很年輕,很年輕!此外,我不僅要留神外國人,而且要對付一個由極右派和極左派組成的第六縱隊。為了向我們施加更大的影響,外國人制造了極右派和極左派……不,對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也許我比我的父親遇到的困難更多,這還不包括一直持續到幾年前的冷戰時期。
法拉奇:陛下,您剛才提到了邊界問題。如今誰是您最糟糕的鄰居?
巴列維:很難說,因為誰也說不準誰是我最糟糕的鄰居。但是我可以回答您,目前是伊拉克。
法拉奇:陛下,您把伊拉克當做最糟糕的鄰居使我很吃驚,我本以為您會提出蘇聯。
巴列維:蘇聯……我們與蘇聯保持著良好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我們與蘇聯之間鋪設了一條天然氣管道。總之,我們賣給蘇聯天然氣,蘇聯向我們提供技術人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與蘇聯之間存在的還是老問題。與俄國人打交道,伊朗必須記住,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不要成為共產黨國家。沒有人會瘋狂和天真到否認俄國帝國主義的存在。儘管在俄國很早以來就存在著帝國主義政策,今天,它比過去具有更大的威脅性,因為今天它與共產主義的教條聯絡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說,對付單純的帝國主義國家要比對付既是帝國主義又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容易。在蘇聯存在著被我稱為鉗子形的策略。透過波斯灣到達印度洋是他們的夢想。而伊朗則是捍衛我們的文明和尊嚴的最後堡壘。如果他們要攻打這個堡壘,那麼我們的生存將取決於我們的抵抗能力和決心。抵抗的問題今天就已經擺在面前。
法拉奇:今天,伊朗在軍事上已很強大,是嗎?
巴列維:很強大,但是還沒有強大到足以頂住俄國人的進攻。這一點很明顯。比如說,我們沒有原子彈。但是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覺得我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它。是的,我說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只可能因地中海而爆發,我卻認為更可能因伊朗而爆發。啊,更可能是這樣!事實上是我們控制了世界能源。石油不是透過地中海而是透過波斯灣和印度洋被運往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蘇聯攻打我們,我們就抵抗。我們很可能被打得無法招架,於是那些非共產黨國家絕不會袖手旁觀,他們會進行干預。這樣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顯然,非共產黨世界不能同意伊朗的消失,因為他們明白,丟了伊朗意味著丟失一切。我講清楚了嗎?
法拉奇:非常清楚,陛下,也非常可怕。因為您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時,似乎在談一件即將發生的事情。
巴列維:我像談論一件很可能發生的事情那樣談論它,但希望它不發生。我認為即將發生的不測事件倒是一場與某鄰國之間的小型戰爭。歸根結底,我們在邊境上有不少敵人,不僅僅伊拉克在擾亂我們。
法拉奇:陛下,您的好朋友,也就是美國,卻與你們相隔萬里。
巴列維:如果您問我誰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的回答是:美國是其中之一。因為美國不是我們唯一的朋友,很多國家對我們表示友好和信任,他們深信伊朗的重要性。但是美國最理解我們。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在這裡有很多利益。經濟利益是直接的,政治利益是間接的……我剛才說過,伊朗是關鍵,或者說是世界的關鍵之一。此外,美國不能閉關自守,不能回到門羅主義。它不得不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因而不得不關心我們。可是這絲毫沒有損害我們的獨立,因為眾所周知,我們與美國的友誼沒有使我們成為美國的奴隸。決定都是在德黑蘭作出的,不是在別的地方,比如說不在華盛頓。我與尼克松關係融洽,就像我過去與美國曆屆總統關係融洽一樣。如果我確信他把我當做朋友,當做一個在幾年內將成為世界列強之一的朋友,那麼我將繼續與他保持融洽的關係。
法拉奇:美國也是以色列的好朋友。近來您對耶路撒冷表現得很強硬,而對阿拉伯國家就不太強硬,您似乎想與他們改善關係。
巴列維:我們的政策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的。我們不能同意任何國家——這裡說的是以色列——使用武力來吞併別國的領土。我們不能同意,因為如果對阿拉伯人採用了這個原則,有一天這個原則也可能被應用到我們頭上來。您會說邊界線的改變往往靠使用武力和發動戰爭。我同意這樣說,但這不能當做有效原則來應用。此外,伊朗接受了聯合國 1967年透過的決議,如果阿拉伯人對聯合國失去了信任,那麼怎麼能使他們信服是失敗了呢?怎麼能阻止他們進行報復,甚至使用石油武器呢?石油會使他們衝昏頭腦。石油已經開始在衝昏他們的頭腦。
法拉奇:陛下,您站在阿拉伯人一邊,卻又向以色列人出售石油。
巴列維:石油由石油公司向所有的人出售。我們的石油哪裡都去,為什麼就不能去以色列?如果去了以色列與我又有什麼相干?該去哪裡就去哪裡。至於說我們與以色列的關係,眾所周知,我們在耶路撒冷沒有大使館,但是在伊朗有以色列的技術人員。我們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在對外政策上,我們的立場是非常獨立的。
法拉奇:這樣的立場是否預示著不久伊朗和以色列將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
巴列維:不。更確切地說,在以色列軍隊從它佔領的土地上撤離的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我們是不會建交的。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我只能說如果以色列人想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他們就沒有其他選擇。不只是阿拉伯人為了軍火花費了大量錢財,以色列人也一樣。我不認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會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此外,在以色列也出現了新的現象,比如說罷工。以色列在剛剛建立時所抱有的那種驚人和可怕的精神能持續多久呢?我指的主要是以色列新的一代人和那些為尋求不同待遇而從東歐移居以色列的人。
法拉奇:陛下,您剛才說的一句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您說伊朗很快會成為世界列強之一。您指的是不是經濟學家們關於伊朗將在 36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預言?
巴列維:說將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許誇大了。但是,如果說將躋身於世界五大強國之列,就一點也不誇大。伊朗將處在與美國、蘇聯、日本和德國一個水平上。我沒有提到中國,因為中國不是個富國,如果 25年後她的人口將達到預計的 14億,那麼她不可能成為富國。而 25年後,我們的人口最多達到 7千萬。啊,是的,等待我們的是財富和力量,不管共產黨人怎麼說。我打算實行計劃生育,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我要達到的目的。我們不能把經濟同其他方面分開。如果一個國家經濟上富裕的話,它的其他方面也會富起來,在世界上也有力量。說到經濟,我指的不是石油。我指的是包括從工業到農業、從手工業到電子工業的綜合經濟。我們從生產地毯轉為生產計算機,結果是我們既保留了地毯又增加了計算機。我們仍然用手工生產地毯,但是也用機器生產。另外我們還生產割絨地毯。我們每年把生產翻一番。還有很多數字說明我們將成為世界強國。例如十年前,當我的白色革命剛開始時,學校裡只有一百萬學生,而現在有三百萬,十年後將增加到五百萬、六百萬。
法拉奇:陛下,您剛才說不僅僅指石油。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們所以有計算機是因為你們有石油,你們所以能用機器織地毯是因為你們有石油,你們明天將得到財富也是因為你們有石油。我們最後來談談您在石油問題上採取的政策以及與西方的關係好嗎?
巴列維:很簡單。我有石油,但是我不能喝石油。然而我知道我能在不對別國進行訛詐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它,而且我也試圖阻止其他人利用石油在世界上進行訛詐。因為我選擇了一視同仁地向所有人出售石油的政策。作出這樣的選擇並不困難,因為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要站在向西方進行訛詐的阿拉伯國家一邊。我已經說過,我的國家是獨立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國家是伊斯蘭國家而不是阿拉伯國家。因此,我不能服從阿拉伯人的利益,而要做有利於伊朗的事。此外,伊朗需要錢,用石油可以換來很多錢。我與阿拉伯人的不同點就在這裡。因為那些聲稱“不再向西方出售石油”的國家,已經不知道怎樣才能花完自己的錢,他們不為將來擔憂。他們往往只有六七十萬人口,而在銀行裡卻有無數的存款,以至於不從油井裡抽一滴油、不出售一滴油也能活上三四年。我可不一樣。我有 3150萬人口,並且要發展經濟,要完成改革計劃,為此我需要錢。我知道錢的用處,我不能不開發石油,我不能不把石油出售給一切人。
法拉奇:而卡扎菲稱您為叛徒。
巴列維:叛徒?我這樣一個掌握了伊朗石油的命運,已控制以前完全屬於外國石油公司的 51%的石油產品的人是叛徒?我不在乎卡扎菲先生對我的汙衊……要知道,對那位卡扎菲先生不能認真。我只能祝願他能像我為我的國家效勞那樣為他的國家效勞,我只能提醒他不要大喊大叫地聲稱利比亞的石油只能開採 10年了。我們的石油倒是至少還可以延續 30到 40年,也許 50年、 60年,這取決於能否再發現新的油田。即使沒有發現新的油田,我們照樣能很體面地活下去。我們的產量眼看在往上升。到 1976年,我們每天能開採 800萬桶。 800萬桶是很多很多的了。
法拉奇:陛下,可是您結了很多仇人。
巴列維:這個我不知道。石油輸出國組織還沒有作出不向西方出售石油的決定,我的不訛詐西方的決定很可能會使阿拉伯國家仿效我。如果不是所有阿拉伯國家,至少也會有一部分阿拉伯國家,他們如果不是馬上,也會在不久的將來仿效我。有些國家不像伊朗那麼獨立,他們沒有伊朗所擁有的那種專家,他們背後沒有像支援我那樣支援他們的人民。我能發號施令,他們卻不能。要擺脫幾十年來一直壟斷一切的公司而直接出售石油是不容易的。如果阿拉伯國家也按照我的決定去做……啊!要是西方國家只是買方,而我們是直接的賣方那就簡單多了,也更有把握了!那就不再存在不滿、訛詐、怨恨和敵視……是的,完全有可能讓我來做個好榜樣。不管怎樣,我將繼續走我的路。我們的大門對所有願意與我們簽訂合同的人敞開著,很多人已經向我們提出要求,他們中間有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荷蘭人和德國人。他們本來很膽怯,現在越來越大膽了。
法拉奇:義大利人怎麼樣?
巴列維:目前我們沒有向義大利人出售很多石油,但是我們卻可能與義大利碳化氫公司簽訂一項重要協定,我想這是不久的將來的事。是的,我們能成為義大利碳化氫公司的極好夥伴,而且我們與義大利的關係一向很好,從馬泰[ 7]時代開始。不就是我在 1957年與馬泰簽訂的合同第一次打破了外國石油公司開採石油的老框框嗎?我不知道別人怎樣談論馬泰,但是我知道,只要說到他我就不能客觀。我太喜歡他了。他是一個偉大的好人,是一個有遠見的人。的確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法:所以有人殺害了他。巴:也許是這樣,但是他不應該在天氣那樣壞的情況下乘坐飛機,米蘭的霧在冬天是很重的。而石油真可能是禍根。也許不是天氣的原因。不管怎麼說是一件憾事,對我們也一樣。好了,我不是說馬泰的死造成了我們與義大利碳化氫公司關係的中斷。不,不,現在我們正準備簽訂重要協定。即使馬泰在,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多,因為我們目前打算做的已經達到了最高限度。但是,如果馬泰還活著,這個合同幾年前就會簽訂。
法拉奇:陛下,我想結束並弄清楚前面談到的那個問題。您是否認為阿拉伯國家最後會把他們中止向西方出售石油的威脅變成事實?
巴列維:這很難說。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可能是輕率的舉動,都存在估計錯誤的危險。但是我傾向於作否定的回答。中止向西方出售石油,放棄這方面的財源,要作這樣的決定對他們來說是很艱難的。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奉行卡扎菲的政策。如果說有人不需要錢,那麼也有人很需要錢。
法拉奇:石油價格會上漲嗎?
巴列維:當然要上漲。啊,當然!當然!您可以公佈這個壞訊息,並且說明這是來自可靠方面的訊息。關於石油我瞭解一切,一切。真的,這是我的特長。作為專家我可以告訴您:石油價格必須上漲,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但是,這是你們西方國家所希望的解決辦法,如你們更樂意的話,也可說是你們高度文明的工業社會所要求的解決辦法。你們把小麥的價格提高了 300%,還有糖和水泥也一樣。石油化工產品的價格漲到了天上。你們從我們這裡購買石油製成石油化工產品,然後再以你們所付油價的 100倍將它們賣給我們。你們讓我們付多得多的錢,付多得驚人的錢。所以今後你們多付點錢買石油是應該的。譬如說……增加 10倍。
法拉奇:增加 10倍?
巴列維:但是,我再說一遍,是你們迫使我們提高價格的!當然你們有你們的理由。但是對不起,我也有我的理由。再說,我們的爭吵也不會是永遠持續下去的。在 100年內,關於石油的故事將會結束。對石油的需要與日俱增,而油田將會枯竭。你們很快就得去尋找新的能源。原子能,太陽能,誰知道。解決的辦法將會有很多,一個辦法不夠。例如:應該採用由海浪啟動的渦輪機,甚至連我都打算建造用來淡化海水的原子裝置。或者再往深處開採,到一萬米深的海底下面去尋找石油,到北極去尋找石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已經到了尋找補救辦法的時候了,不應該再像過去那樣浪費石油了。現在像我們這樣使用石油,也就是消耗原油,簡直是犯罪。要是我們設想一下,不久就要沒有石油了,要是我們能把它製造成上萬種石油製品,也就是石油化工產品,那麼……每當我看到不顧一切地用原油發電從而糟蹋了它的價值時,就會感到十分震驚。啊,當我們談論石油時,最重要的不是談其價格,不是談卡扎菲的禁運,而是應該懂得石油並不是取之不盡這個事實,在其耗盡以前,應該發掘新的能源。
法拉奇:這個該詛咒的石油。
巴列維:有時我覺得並不盡然。關於該詛咒的石油,人們已經寫過很多文章,請相信這一點:當你有了石油,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又是很麻煩的事,因為它代表一種危險。世界會因為這個該詛咒的石油而發生爆炸性的事件,即使像我這樣與威脅作鬥爭……我看見您笑了,笑什麼?
法拉奇:陛下,我笑是因為您一講起石油就完全變了。變得興奮、激動、全神貫注,變成了另一個人,陛下。而我……在離開這裡的時候,還是不理解您。從某一方面看來,您是這樣古老,而從另一方面看,您又是這樣現代化……也許東方和西方兩方面的因素都集中在您身上……
巴列維:不,我們伊朗人與你們歐洲人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婦女戴面紗,你們也有你們的面紗,是天主教會的面紗。我們的男人有很多妻子,你們也一樣,男人有被你們稱為情婦的妻子。我們相信顯聖,你們信奉教義。你們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我們並不覺得低人一頭。別忘了你們所有的一切是我們 3000年前教給你們的……
法拉奇: 3000年前……陛下,我看見您現在也笑了,不再那麼憂鬱了。啊,真遺憾,關於黑名單的事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
巴列維:您的名字真的在黑名單上嗎?
法拉奇:陛下!如果連您這樣一個洞悉一切的王中之王都不知道,那該怎麼說呢!但是我已經告訴您,也許是這樣,我的名字上了所有的黑名單。
巴列維:遺憾。但是沒有關係,即使您的名字上了我的當局的黑名單,我把它列在我心中的白名單裡。
法拉奇:陛下,您使我害怕。謝謝,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