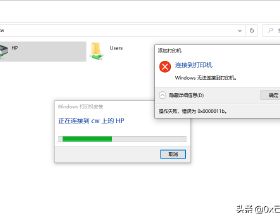很勵志的一句話,做啥事都不要急於求成,因為播種和收穫不在一個季節。中間隔著一段時間叫堅持!
我家很窮,但小時候我卻被白膘子肉膩著了
我叫孫立。是山東省煙臺人。
我出生於1972年。我有奶奶,兩個姐姐,一個妹妹。
我的出生滿足了父母的求兒夢,我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六歲那年過年,家裡破天荒割了兩斤白膘肉,那肉幾乎都進了我的嘴裡。因為太油膩,我吃壞了肚子。再後來別說吃了,看見白肉就噁心的想吐。
我父母是老實的有些窩囊的莊稼人。
除了七個人的口糧地,父母還花很少的幾個錢,包了一片地,我記得從溝底到坡頂全是我家的。
從春忙到秋,收穫的半坡莊稼賣不了幾個錢。
除了必要的小麥玉米,地裡大都種著花生和地瓜。
地瓜蔓花生蔓是粗飼料,地瓜和豆餅是精飼料。我媽餵養了一頭老母豬,老母豬一年能下三窩豬崽。
這些豬崽是一家七口人的全部開銷。
八年級放寒假,我陪父親去賣過一次豬崽。
一隻小豬大約20多斤,太少賣虧了,太大沒人要。
早上四點左右,那乾冷的天凍碎骨頭。
母親溫一鍋精飼料給小豬吃,就為了虛長兩斤秤。
我和父親一人一輛大金鹿腳踏車。
大金鹿腳踏車的後座,又寬又結實,父親把扁筐綁上,把豬仔放進去,上面用尼龍網攏住,最後搭上破棉絮或者破麻袋給豬仔取暖,它還有一個作用是給豬崽一個黑的環境讓它安靜。
騎行約二十里,到了一個大集市,這買的賣的人多,出手快,價錢也高點。
看皮毛,問價錢,稱重量。
肚子太鼓,買家認為你太那個,就會哼著鼻子走開。
肚子癟了,賣相差,也不好出手。
還好臨近中午,三隻小豬仔全部出手了。(有賣不了再馱回去的時候)
我的手腳早凍得不是我的了,我用嘴給手上哈氣,手凍成了胡蘿蔔冰棒,我眼睛凍出了淚,儘管我全副武裝了。
再看父親,他棉帽子下的耳朵尖凍破了皮,血水凝結成了冰。清鼻涕流出隨意滴下來,他用手一抹,擦在鞋底上。
這些記憶刻進我的骨頭裡。我要感謝我的父親沒有因為我是獨苗溺愛我。
“我不要種一輩子地!我要上學!”在得知我沒有考上高中時,我把自己塞進套間屋的炕旮旯裡。炕的四周全是糟七糟八的傢什,只剩下我一個人睡覺的地。
也許是智力的問題,我的兩個姐姐都初中畢業。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學習上,還是差個十多分沒有考上高中。
我的哭聲讓父母除了難過還有自責。父親找到在鎮上工作的一個遠房親戚,求爹爹告奶奶,晚上悄悄給校長送了兩大桶花生油,我這才得以上了高中。
在以後幾年裡,這個遠房親戚家裡的食用油,被我家給承包了。
要做就做別人做不了的,別人玩不轉的
那時上高中要叫號,我排最後一名44號。
如果上課提問,叫到我44號,要麼是問題太簡單,要麼是老師想殺雞給猴看。
44號的自卑伴隨了兩個月,在期中考試時,我的排名前進了8名,變為36號。這時候,同學和老師間已經熟悉,很少叫號了,但叫44號的聲音,時常在我耳邊縈繞。
36,27,10數字越來越好看些。雖然我盡了八荒之力,但還是考了個大專,但對父母來說,這已經是光宗耀祖了。
因為我家祖上輩輩世世沒出過讀書人。
1989年,我就讀於濟南的一所院校學習機械設計製造。
我很用功。父母看見有身份人臉上露出的幾乎是獻媚的傻笑,和彎腰勞作的體態,讓我有了給父母臉上爭光的志氣。
因為已經在底層,抬起頭就是揚眉吐氣。
在我上大學期間,奶奶生病住院半年後去世,本來就很貧困的家雪上加了霜。
最疼我的大姐出嫁了,沒啥體面的嫁妝。
後來我才知道,她在我上學的幾年裡,一直偷偷拿錢回孃家補貼家用。
我92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市屬的五金總廠。總廠下設五個分廠,我負責鋸片廠的機器除錯和維修。
鋸片的刀頭是金剛石和各種重金屬粉末合成的。切割不同材質的石頭需要不同的刀頭,不同刀頭需要粉末的比例和金剛石的含量不同。
這些配方掌握在分廠廠長手裡。
每逢週一,廠長都要把自己關進鋸片廠寫著“閒人免進”的屋子裡,根據產品需求調配金剛石與合金的比例。
越是神秘,越顯示出他的重要性,因為即使總公司的高層,也對我們廠長禮讓有佳。
我父母一輩子都在做最辛苦,勞動力最低下的苦力,他們的生活狀態告訴我,要想有一番作為,就要做別人做不了的,離了你玩不轉的。
人一旦有了目標,就覺得每一天都是充實的。
在以後十多年的工作中,我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就像學徒偷偷跟大師傅學廚藝,多聽多記多琢磨演算,就會把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總之最後我掌握了金剛石鋸片刀頭的配方技術。
很勵志的一句話,做啥事都不要急於求成,因為播種和收穫不在一個季節。中間隔著一段時間叫堅持!
要努力但不要著急,繁花似錦和碩果累累都需要過程。
父母的日子好過些,就想盡辦法彌補沒有嫁妝的姐姐
93年我二姐出嫁時,家裡條件稍好些,但因為要攢錢給我娶親,二姐也沒啥陪嫁。
那時候,煙臺蘋果已經很有名了,父母也和大多數家庭一樣,在田裡栽上了蘋果樹苗。
94年我認識一個女孩,她很漂亮,通情達理又善解人意。她也看上了我的忠厚老實和我的能力。就這樣,我們相戀了,沒有海誓山盟,也沒有常人所想象的浪漫,我們的情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第二年,父母在村裡花4000元給我買了一幢八成新的四間房,重新刷了白牆,鋪了水磨石地面。
96年我結婚了。父母為我擺了三桌酒席,花光了他們的全部積蓄。
結婚後,我們在城裡租房子住。婚前老婆就說服了她的母親,她向岳母保證,說我一定會讓她住上最舒適的新房。
我做到了。那時候在縣城買七八十平的房需五萬元左右。我存下我的工資,老婆的工資零用 ,我用三年時間,沒有用父母一分錢,買了第一套房。
我讓父母住進了我在農村結婚的新房,這也是我沒有阻止他們在農村買房的原因。想起那套間的旮旯,我就覺得,父母也該住的寬敞明亮些。
父母在村裡的人緣好起來,我成了別人父母眼裡的好孩子。
轉年,我的兒子出生了。有了孫子父母的底氣足了,他們不笑不會說話了。
我要父母進城帶孩子,可他們不願意,他們給的理由說服了我:“孩子讓你丈母孃給你帶,她一個人需要伴。”
父母也放不下那已進入盛果期的果園。
平時蘋果樹澆水打藥,大多是二姐夫在幫忙。他在離家不遠的單位上班,三班倒,有空閒。
秋天賣了蘋果,父母就會拿出兩千元給二姐,算是勞動補償。
98年,妹妹出嫁時,家裡的經濟條件有了大改觀,陪嫁了摩托,冰箱、彩電…妹妹可謂是風風光光出嫁。
妹妹的風光出嫁,讓父母覺得虧待了大姐二姐,在果園有了收入後,他們“巧設名目”,以“勞務費”、“摩托車油費”…給兩個姐姐錢。
母親說:“我們能動彈時,顧兒也要顧閨女。老了,躺炕上要依仗兒子,也要指望閨女。”
母親跟老婆說要給我們點錢,說當初我們買房他們做父母的應該贊助點。被老婆笑著拒絕了。
老婆說:“咱媽一輩子手裡沒存過錢,有倆錢就不知咋花了。”
我聽了既心酸又欣慰。
我想對父母說,爸媽好日子才剛開始呢!
我承包了鋸片廠,我把親戚和鄉人招進廠裡
因為我的勤奮,得到領導的重用,在2000年工資已經三千多元了。
那年我擔任了鋸片廠負責技術的副廠長。
2004年,各個分廠對外承包,原廠長以為他掌握了金剛石配方,鋸片廠就非他莫屬。沒想到殺出一個我,我無形中替公司清除了一個趾高氣揚不把總公司領導放在眼裡的人。
聽說我承包了工廠,老家的人拐彎抹角的聯絡到我的父母,希望我能給他們的子女安排工作。
我的父母儼然成了香餑餑,每次回去,車子沒挺穩,就有鄉鄰敲玻璃窗,他們臉上寫滿了熱情。
我安排了幾個人進了廠,我成了鄉親們眼裡的貴人。
我的妹妹是我主動把她叫到廠裡的。
我告訴妹妹,你每天只需不間斷地各個車間走動,你廠長妹妹的身份,會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後來,我大姐家的大外甥沒考上高中,也到了廠裡,負責跑業務。都是窮孩子,他們很知足,也很勤奮。
我老婆家的兩個親戚也陸續來廠裡上了班。
我不能 把父母留在農村,我要讓他們過上城裡人的好日子,我有了買房子的打算。
那些年建築業好的不得了,我也分得一杯羹,我的住房由兩室換成四室。
我把原來住的三樓留給父母。他們更喜歡獨居。
好日子來了,擋也擋不住。
記得很清楚,那是2008年。
高速公路拓寬,佔用了路邊的一大部分果園,賠付了9萬元。
我對父母說,這不是我不讓你們種果園了,是老天爺都覺得你們該享福了!
65歲的父母親,從此告別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
我用小車大車把父母接到了城裡。走那天,父母對來送行的人直抹眼淚,是喜極而泣?還是故土難離?
我想第一種的成分多一些。
父母時常在我耳邊唸叨,說你大姐如何遭罪,你二姐如何困難,你妹和妹夫兩人如何為錢打架。
我聽著,能幫就幫。我借給姐妹的錢,都經過我老婆的手,老婆在送錢去時,總跟一句:“啥時候有,啥時候還。”
老婆從不說給,姐妹太多,給這個多給那個少,怕出矛盾。
姐妹的錢是借十萬還三萬,還一部分後再借。
有時候我的錢,裝進父母的左口袋,隔天以我姐妹的名義,把錢又還進我的右口袋。
這麼多嘴都來咬我啃我,有時也有怨言,可想到她們當初出嫁時的寒酸,我又釋懷了。
十年前,我把父母住的沒有電梯的三樓賣了,給他們買了帶院的一樓。他們閒不住,在院子裡種花種菜,他們過著許多城裡人也羨慕的日子:“晨起侍花,閒來拉呱。太陽底下打盹,小雨唰唰時洗花…窗外花開花落,院內菜蔬果瓜…”
當初沒嫌我窮的老婆是我的福星,我待她永遠如初戀。
如今我已年過半百,作為農村出來的人,我想說兩句:咱們都是吃地瓜餅子長大的,沒有生在帝王將相家,沒有顯赫的門第,就不要對親戚鄉親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
我也從不相信兒孫自有兒孫福這句話,我覺得三代人中至少要有一代人要努力。要麼你吃苦,要麼你的孩子吃苦,要麼你的老人繼續為你吃苦。
其實我們奮鬥的理由很簡單:年輕時不拖累生我們的人;年老時不拖累我們生的人。
老婆是一體的,她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她的。
趁年輕,擼起袖子加油幹!為父母,為老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