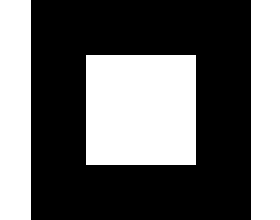那時,父親已中風五年了,生活處於半自理狀態,行動受限於家院子裡外,每日拄著柺杖挪來挪去,多虧母親和大姐二姐就近照顧,也是身居遠方的我長久的牽掛。
那天,外甥女從家鄉來了,想在這裡打工。
聊起家庭瑣事,她笑嘻嘻地說外姥爺嘴巴饞了,想吃個杏,問多少價錢,鄰居告訴他三塊錢一斤,他覺得貴,咂咂嘴,嘆口氣不吃了,鄰居說“老爺子太摳門了,退休工資還攢著呢?”
說者無心,我聽了之後很不是滋味,想象中他拄著柺杖,坐在門樓底下寂寞茫然的眼神,每天望著日頭升起又落下,瞅著雞鳴狗叫小豬兒呼嚕嚕,身軀已是風燭殘年,想吃點東西,又怕花錢,平日裡是能省則省,與往日康健時大不相同。
想起那時返鄉時,騎著三輪車帶他充血管時,發現暴凸的血管青筋畢現,手腕乾瘦,打點滴時那個醫生竟幾次跑針,氣得直朝那人吼,父親的眼神中有了些暖意,他已視我為依靠了吧?帶他去老澡堂洗澡時,扶著他下了池子,蒸汽繚繞中幫他搓了又搓,服侍他穿好衣褲,沒有半點矯情,這些都是應該的,可惜平日裡做得太少、太少。
在上海,多貴的東西,都會買來給孩子吃;孩子還不吃,大多浪費了;多少次對比家鄉的窮苦,想起二老的簡陋生活,都為此想訓斥孩子。
後來,給二姐打電話說起此事,二姐也說,父親的眼神精力明顯不如以往了,眼見著就老下去了,腸胃也不好,瓜果青菜吃多點,就會拉肚子,不敢讓他多吃。
又說起鄰居的四個老人,比父母的年齡還小,都一前一後地去世了。
跟著父親聽揚琴和柳琴的人又少了許多,每逢下午聽唱了,父親就拄著柺杖挨家挨戶地叫,有一天沒一天的,好像每天都是最後的聚會。
聽得喉嚨憋得發酸,眼淚差點落了下來。既是自責,又是心酸。
捫心自問:多年來,又盡了多少義務呢?廿年寒窗讀書盡,贏得親鄰薄倖名而已。
淚眼朦朧中,怔怔地想:一向喜歡趕集的他,再難以上街溜達了,即便是吃個杏,也要思量半天。
父親和我相差四十一歲。
印象中,只要是街上逢集,父親不管身上有錢沒錢,家裡需不需要買東西,他每天鐵定都要挎著破籃子到街上“巡視”兩三圈,一次性可以買齊的物件,非要三番五次樂顛顛的跑,好似八集街沒有他的“看顧”和“加塞”就不成“集”一般。按說這樣的殷勤,應該是貨比三家,買回來的東西是物超所值了。可他不,別人買一塊錢五斤的土豆,要比他一塊錢三斤的土豆質量還好,而且從來都是短斤少兩,小販們最喜歡這樣“窮闊窮闊”的買主了。
尤其是遇到街裡來了新鮮玩意,他是非湊上熱鬧不可,愣愣的能站在那裡半天,傻呵呵地經常被一些江湖騙子忽悠,買一些“萬能切菜刀、包百病虎皮膏藥、拉肚一日停、超級老鼠藥”等大而無當的東西來,發現被騙後,還每每自嘲為騙子開脫,“毒毒的日頭,人家在那裡吆喝得嘴巴都起泡了,你不買,我不買,人家賣給誰去?”
每逢母親數落他不會過日子,他則躲在牆角吧嗒吧嗒抽起煙來,毫不生氣。他只負責把錢花出去,別的一概不問。
沒錢時,父親也會垮著籃子、頂著破席夾子、披著衣服甩甩答答的上街,帶回來一點新上市的桃李杏瓜或是一小包狗肉雜碎,就著散酒咪上幾口,然後醉醺醺的睡個午覺,醒來之後,通常是日頭偏西,巧妙錯過了下湖幹活的“好時光”。他從來不喜歡下地幹活,有一次田地裡喂化肥,耽誤他喝酒睡午覺了,他一生氣,挖個坑,把半袋子化肥都填了進去。氣得母親大罵,他自知理虧,也不吭聲。
他愛抽菸,愛溜達,愛聽人嘮嗑,在眾人的目光下撒魚是他的高光時刻,在楝豆樹下邊修補漁網邊唱戲是他最難得的休閒,如是一天天的日子滑過,他老了,我們也長大了。
姐弟五個,好像他都沒怎麼問過事,或許這正是這種“無為而治”,讓我們無拘無束地生長,除了一點貧窮,兒時的我們,感受更多的是自由自在的狀態。
那年,他垂垂老矣,想吃個杏,無法親自上街了,竟也成了奢求。
轉眼,老人家離去,已經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