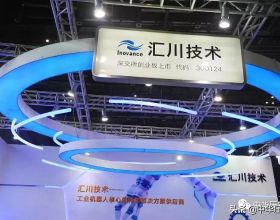週六早上九點半,鼓樓西大街79號。
坐滿了人的小平房裡,開始播放電影《風聲》。
不對勁,正常放電影,不應該關燈嗎?
然而,屋內不但開滿了燈,還有人拿著麥克風,在旁邊嘰裡呱啦,現場口述劇情…
但是,每個畫面,又講得極其生動:
把一根粗壯的麻繩吊在空中,拉得繃直,然後用鋼絲的刷子把麻繩刀麻,讓那些麻,全部齜出來…
兩個大漢抓著她的身體,從那頭推到這頭…麻繩上,掛著鮮紅的血滴…
現場鴉雀無聲,觀眾身臨其境…
電影放映結束,一位老太太走過來,對主講人王偉力說:
下次注意點,我們聽你講得都難受了!
王偉力笑了笑,心想:入戲就對了,下次還得這麼講…
是的,這裡的觀眾,只能聽電影。
因為,他們是盲人。
契機
王偉力,心目影院的主講人,大家都親切稱呼他:大偉。
2004年的一個週末,在家休息的大偉,打開了電影《終結者》,打算和老伴消磨時光。
不湊巧,一位盲人朋友閒著沒事,來串門兒了。
感到打擾了主人,朋友打算離開。
大偉有點不好意思,突然靈機一動:要不,我給你講電影吧?
這是科幻動作片,又是外語,一邊要忙著翻譯臺詞,一邊要講述電影裡精彩刺激的場面:飛天遁地、子彈亂舞、炮火亂飛、 槍戰、追車…
大偉的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也強,但給別人“講電影”,還是頭一回,過程手忙腳亂,但總算把片子的驚險炫酷,講了出來。
講述全程,朋友全神貫注,一聲不吭…
講完後,大偉轉頭看朋友的臉,卻看到對方腦門和鼻尖、臉頰上,掛著豆大的汗珠;
眼淚和汗珠,隨著影片完結的字幕,一同滾落…
朋友很早失明,別說看電影,就算是家人聚一起看電視,因為看不見,也插不上話,通常是搬張椅子到院子裡,獨自發呆。
聽大偉講電影,他第一次明白,那片從未接觸過的世界,那片浮華的光影,原來可以藉助聲音,刻進腦海…
朋友聲音顫抖,手上緊張得全是汗水,握住大偉的手:
謝謝你,這是我30多年來,最幸福的一天。
偶然的嘗試,不僅為朋友打開了新世界大門,連帶著大偉,也深受觸動…
在這之前,他從未想過,電影和盲人之間,會發生什麼關係…
他開始思考:我們看電影依靠眼睛,那盲人眼睛用不了,我們是不是可以幫一把?
帶他們,去看見
如果讓健全的人去描繪身邊的世界,不是什麼難事:
草地是綠的,晴朗的天是藍的,快要下雨時天是灰的,船駛過湖面會起皺紋,秋季葉子會變黃,奔跑的人腳下會泛起微塵,鞋子走過田野會沾滿泥土,學生的領口浸著汗水…
這些平常的視覺實踐,對於盲人來說,一生都難以體驗。
大偉明白,要想吸引盲人,給他們以和健全人觀影相近的觀影體驗,就要設身處地,走向那個,他從未經歷的世界。
比如,講直升機,他形容:一個扣著的湯勺,加幾片旋轉的扇葉;
比如,講摩天大樓,他比喻:是反扣的巨大玻璃杯。
為了把電影講得聲情並茂,王偉力經常讓妻子背對電視閉上眼睛,檢測他的講解是否能讓盲人們理解、是否有感染力;
他還時常會緊閉雙眼,由妻子攙扶著走上大街,切身體味盲人的感受…
大偉說話字正腔圓,每一次講電影,不僅飽含情感,更善於抓住細節,傳遞影片的精彩與微妙之處…
紀錄片《微觀世界》裡,他講兩隻蝸牛的纏綿:
在它們吻的過程之中,身體慢慢貼合在一起,從嘴部一直到腹部甚至於到尾部,它們一點點地粘合,身體逐漸蠕動…
他講《泰坦尼克號》裡,沉船後的悲壯:
男女主握住的手,一點點放開,女主看著男主,沉下大海…無數在冰水裡逝去的生命,都曾經試圖發出聲音,卻只能沉默地匯聚於冰海之下;
他講《唐山大地震》裡,突然的失去:
樓層被撕裂,人們在哀嚎…一個活生生的人,瞬間被倒塌的瓦磚掩埋…一個母親,兒子和閨女只能選一個,她淚流滿面、顫抖地說出:救兒子…
他講《少年的你》中,陳念和小北的對視:
看守所探視間,陳念和小北隔窗對坐,陳念安慰地看著小北,小北微皺眉頭,輕輕搖了搖頭,意思不要自首…
每一次講述,都是一次再創作。
音響要選好的,不然會影響盲人“觀影”的效果;
主講人要注意站位,不然坐在後排和側邊的觀眾,沒法得到最好的體驗;
音量要適當,給人一種在耳邊低語的感覺…(資料來源:@情智有氧)
每次放映前,大偉都會反覆觀影,打磨稿件,字斟句酌,寫出最通俗也最有穿透力的文字,宛如烏鴉寫稿般認真…
電影的影象,在大偉的話語裡,以另一種方式,被重新拼湊、構建、輸出…
他講平凡普通的人,如何在多舛的命運裡輾轉悲喜,如何在時代的風雨中,離散又團聚;
他講微小又鮮活的花草、昆蟲、牲畜,如何突破土壤,扛住風霜,從大自然裡找尋到活著的機會,在叢林、湖泊、沙漠、山間頑強生存;
他告訴觀眾,電影把思想的觸角延伸至未來,回程到過去,講人類在電影的世界裡,如何穿梭於不同的時空,每部科幻電影裡,時空隧道的盡頭,是凝望時間和文明的眼睛…
30平米的心目影院裡,盲人們被大偉的講述觸動,情緒隨著電影的劇情興奮、緊張、沉思、驚呼、驚喜、大笑、嘆息、流淚…
盲人影迷,奔赴的不僅是一場電影
剛開始,盲人到心目影院的情況,很是熱鬧:
觀眾衣冠不整、大聲喧譁、胡亂走動…
大偉知道,這是因為,盲人常常呆在家,少有社交,比較缺乏公眾場合的交際經歷…
所以,每當放映前,他都會給出時間,讓大家聊聊電影、聊聊天…
每週一次的放映時間,不只是盲人和電影的相會,更是他們和周圍環境,難能可貴的交匯和嘗試。
慢慢地,觀眾接觸到寬廣的現實世界,開始注意起一些小事:
比如,儀容穿戴開始整齊、端莊;
比如,影院裡只要開始放映,就會安靜下來,不再大聲喧譁…
電影所帶給他們的,不僅是藝術的享受,還有本該屬於他們的尊嚴。
盲人肖煥義,從2006年開始看電影,是心目影院的老影迷了。
他的片單,估計比一些影評人的長:《平原游擊隊》《地道戰》《盜夢空間》《八佰》《一代宗師》《寒戰》…
每個週末,風雨不改、雷打不動。
每次開場前的互動環節,他總是積極又熱情。
作為盲人,他深知:像他這樣的殘疾人,吃飽穿暖就行了,至於精神需求,是奢侈的,能免則免吧…
去了心目影院後,他才發現:在這個角落,盲人沒有被遺忘。
他說:我雖然看不到,但是我出門,能聞見化妝品的味道,能聞見別人身上的煙味…作為人類社會的一份子,能夠出門和同類說說話,待在一起,那也是非常幸福和愜意的事情啊。
那天,剛播放完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大偉接到了一個電話。
那一個70多歲的盲人影迷打來的,電話裡,他聲音顫抖:
我老伴兒去世,已經十幾年了,我連做夢,都沒有畫面…
今天看完你們電影,我一下子就想起,年輕時候和老伴在紫竹院公園,水裡那些白色的小木船,在我耳邊劃啦啦的響…
生活對我來說,就是個無望的黑洞…但是今天,你們讓陽光,照進了這個黑洞,謝謝你。
電影,於盲人來說,是生活之外的生活,真實之外的真實,那是想象力背後的烏托邦自留地,本是一片荒蕪;
現如今,在那片土地上,花草栽種,河流湍急,平地正待高樓起,現實的稜角輪廓,不再只是手中觸控到的單調,而是心靈上,無限的遼闊…
堅持
陸陸續續的,心目影院從只有大偉兩口子,到有其他志願者加入。
不變的是,這家電影院,沒有收過一分錢,從頭到尾,都是公益性質。
為了讓影院維持下去,他賣了車,用光了存款,甚至還向父母借錢…
儘管如此,他也沒有想過,要結束心目影院。
他說:觀眾們大多都六七十歲了,有沒有電影,他們都已經過了大半輩子了…他們來看電影,其實,是在實現作為一個人,生活的儀式感。
中國大約有1700萬視障人士,在前陣子烏鴉寫過的“殘疾設施測評”一文中也能得知,僅僅是基礎設施的缺乏,就讓他們對於外面的世界,望而卻步;
對於這個群體來說,看電影,更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幸運的是,殘酷的現實中,仍然有這麼一片小小的天地,能讓他們偶爾忘卻現實的艱難與不幸,在他們遍佈傷痕的心上,用聲音描摹出斑駁美妙的光影圖景。
2020年的初雪,心目影院在一個小影廳裡,放起了電影。
大偉的解說,伴隨著電影配樂,熟悉地響起:
音樂輕輕地迴盪,歌詞也很是應景:你鼓舞了我,讓我得以站於高峰;
你鼓舞了我,使我能橫渡,暴風雨中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