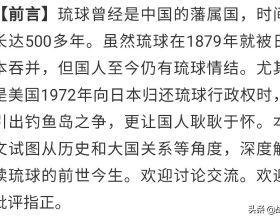1969年冬,炮212團組建時,楊副政委只是後勤處協理員。沒過多久,蔡政委調離,曹副政委擔任了政委,楊協理員就一躍成了副政委,可謂進步很快。
楊副政委是解放兵,原後勤處長也是解放兵,他一喝多了酒,就吵吵,“我就是機關槍‘嘟嘟’過來的唄!”楊副政委從來沒有過,他也沒有那麼多嗜好,除愛吸菸外,喝酒、打牌從來沒有見過,說話也總是一笑一笑地特別和人。
我真正接觸楊副政委是1973年在靈石張家莊軍工生產時期,他帶著高參謀是團裡住我們一營的工作組,當時就與營首長一起住在張家莊煤礦招待所。那時我是營部書記,與通訊班也住在那裡,為他們服務,自然就接觸多了。
施工起初,楊副政委帶著高參謀穿工作服、戴安全帽,時常到大山山洞裡施工現場檢查。一次高參謀與連隊上山,突然山洞裡停電,高參謀把手電筒裝在工作服內的軍褲裡,越急越掏不出來,裡面黑咕隆咚,不好往外撤,回來還與楊副政委當笑話學說。楊副政委說:“你就是缺根弦,安全第一,你怎麼把手電筒裝在裡面的軍褲裡,等一出事著急了吧!這就是麻痺思想,‘大意失荊州’,要不得。通知連隊,凡進入洞內施工現場的,一律將手電筒都要裝在外面兜內,以防突然停電後撤,確保安全。”
慢慢地施工進入正軌,晚飯後,楊副政委也開始了散步。營首長給我的任務就是陪同,主要還是為了安全。這裡四周是山,是煤礦、石膏礦,出門對面就是汾河。汾河也是季節河,平時也很溫順,上面一下雨,就波浪翻滾,水流頓時大了起來,巨石滾動,木材夾雜,成了洶湧澎拜的野獸。記得,我們在時就發生了上面下雨,沖走了一女青年,直到過了兩天,才在夏門村發現,人已經死了。
楊副政委沿著汾河走著,一般不說話,我也不會瞎開口,只是隨著走,像是護衛!一次,楊副政委突然開了口,“你會唱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的歌嗎?‘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嘩啦啦地流過我的小村旁’。”我說“會”。楊副政委說,“你看,像不像咱們這個地方。”我說“像”。這好像是我們多次散步,唯一說過的話,平時楊副政委話也不多,只是看書寫東西。
在汾河邊
那時非常重視階級教育,借五一勞動節,楊副政委特意聯絡組織部隊到富家灘煤礦——“汾西礦務局階級教育館”進行階級教育。富家灘煤礦緊挨汾河、南同蒲鐵路,是日本侵略軍掠奪資源的地方。富家灘煤礦萬人坑同撫順煤礦、鶴崗煤礦、大同煤礦等萬人坑都是聞名全國的。日本侵略軍要煤不要人,瘋狂地掠奪我國的煤炭資源,僅1942年冬一個出煤日,日本鬼子就趕53人到剛塌頂危險的新四坑出煤,這53人都慘死在煤礦裡。當時流傳著好多歌謠:“日本把頭是財狼,工人血汗被吞光”、“進了富家灘,兩頭不見天,乾的牛馬活,吃的豬狗飯。頭枕半頭磚,身披麻袋片,受盡閻王罪,仇恨記心間。”“進了富家灘,十有九不還。要想回家走,除非背骨頭。”
這都是當年參觀富家灘煤礦——“汾西礦務局階級教育館”進行階級教育時記錄下來的,日本侵略軍掠奪了我國多少資源。“富家不富汾河灘,國人難國萬人坑。掠奪資源人換煤,請君不忘亡國情。”這對我們年輕軍人來說,確確實實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無國那有家,保衛祖國,是我們每個軍人的神聖職責,國強民安,國強民富。
到了9月份,營長叫我幫著三連總結整理份經驗材料,我繕寫好讓營長去看。營長說,“我就不看了,楊副政委不是在這兒嗎!你讓他看去!”我給楊副政委送去,楊副政委說,“放這兒吧!”我便退了出來。一晚上也沒動靜,第二天早晨也沒話,吃完早飯,我沉不住氣了,就去楊副政委屋,想聽聽他的意見,看看到底行不行,或者說,哪兒還需要改。楊副政委依舊什麼也沒說,只道:“這字,是你寫的?”我說:“哦!”見楊副政委忙著,就出來了。沒想到這天上午,楊副政委就回團裡了,還把材料帶走了,弄得我七上八下,左顧右盼團裡來電話,好去團裡改稿,但一直也沒有音信。
後排左1:楊副政委,右1:政治處主任
師裡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連隊大會竟然召開了。三連連長回來就找我,高興地說,“書記,咱們的材料成功了,我們在師會議上進行了介紹,受到好評,我們連還被評為全師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連隊。”我也非常高興,功夫終於沒有白費,不過,團裡怎麼沒有說一聲。營長也回來了,也挺高興,給了我三天假回老家看看,叫我過了十一,到團組織股報到。這樣,我就被調到了團組織股。
看來這都是楊副政委運作的,他見三連的材料寫得不錯,回到團裡就交給組織股按師裡統一的格式、字號列印上報了。師裡介紹後反映也挺好,楊副政委就建議把我調到組織股去,同時,讓組織股下去一個年輕幹事,到我們一營二連任副指導員。我就想,何必調個個兒呢?還不如讓我到二連去當副指導員呢,那可是副連吶,而我這組織股幹事才是個見習的排職。沒想到我卻站住了腳,在組織股一干就是四五年,人盡其才吧!
楊副政委不顯山不漏水,一直對我還是比較關心。1976年3月,楊副政委與老劉副團長負責老兵退伍工作,在研究送豐南退伍老兵時,他想到了我。楊副政委就對我說:“曹幹事,你回老家送豐南退伍老兵吧!藉此,買些蝦皮託運回來。”我們部隊多是由炮五師組建的,炮五師在昌黎駐防,各個團也多在沿海地域,吃慣了海味,就饞海味。我說:“行!到家聯絡好後,我再給你發電報。”
送戰友
其實,送退伍老兵的活兒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一般不讓連隊幹部去送,恐怕有矛盾發生意外,多是由機關參謀、幹事、助理員去送。我也明白楊副政委的用意,因我1975年10月1日剛剛結婚不久,也是為了照顧我年輕夫妻團聚,那時的老首長辦事考慮的多比較周全。
我一路帶著豐南退伍老兵格外用心,因為我們是一個車皮來的老鄉,我提了幹,他們今天揹著大包小包離開了部隊回家,人生是個重大的轉折,我能不盡心盡力嗎?從太原站轉車,我就找軍代表,要求安排有座位的車廂。到了北京站,不管人多麼多,我仍是去找軍代表,儘量要求有座位的車廂。快到唐山站,我就與他們商量,是先到縣城胥各莊報到,還是先各自回家,然後借趕集再到縣城胥各莊報到,多數人同意先回家,一到唐山站,我就撒了手各自回家。最讓人不滿意的是檔案,有的人想自己帶著,自己去聯絡工作。團裡出來特意明確規定,檔案一定要集中交到縣武裝部,要不然不給你開回執,不開回回執去就算你沒有完成送退伍老兵的任務。
這對我來說沒有問題。到了家的第二天,岳父就帶著我到縣武裝部去交退伍老兵的檔案,動員科的一見老政委來了,忙說:“老政委有事嗎?”岳父說:“這不是二姑爺回來了,他送退伍老兵來了,你們把檔案給他收下。”動員科的就說,“這點事,還用你老來,說一聲不就行了嗎?”岳父說:“我也沒事,順便看看你們。”說話間,點點一個個檔案,就開了回執。
岳父趁熱打鐵,騎著腳踏車,又帶著我去了水產局。水產局局長是我家屬同學的父親,兩家更加熟悉。水產局局長說:“那陣風兒,把老政委吹來了”。“這是二姑爺,這是陸叔”,岳父忙介紹。我也上前搭話,“陸叔好?我與你女兒也都是同學”。水產局局長說:“好好好!老政委,無事不登三寶殿吶!”岳父說:“二姑爺他們部隊想買點蝦皮,你看那些好,給他們答對答對。”水產局局長說:“二姑爺,你自己挑吧,看上那個,咱們就答對那個。”
買蝦皮的事情也辦妥了,我便給楊副政委發了電報。可是,錢卻遲遲匯不過來。我左等右等,還是年輕上進心強,恐怕待時間長了受埋怨,就與我妹妹說,“等錢到了以後,你幫著你嫂子僱車將蝦皮拉到火車站託運”,接著我就返回了部隊。
誰也沒有想到,我這一走卻出了事。妹妹幫著她嫂子僱了小排子車把蝦皮拉到了火車站貨運室。貨運室的人員說:“這葦蓆包不行,你們得再包加一層麻袋。”我家屬特別能幹,在內蒙建設兵團就是女排排長,認為這是個小意思,就不顧自己懷著身子與我妹妹兩個人自己動手用彎針縫包起來。一個葦蓆包蝦皮多是一百多斤,一包包再用麻袋片包裝,掫來掫去,我家屬不由動了胎位,幾次打保胎針都沒能保住,小產了。心痛的我母親,“哎呦!把我大孫子沒了”。看來,我就是沒有兒子的命。
等家中來信寄到部隊,訊息不知怎麼也傳到楊副政委耳中。楊副政委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平時不大說話的他見了我說:“本來是想給你辦件好事,沒想到惹出這麼大麻煩,錢沒匯到,你著什麼急回來呀!”
沒過幾個月,唐山豐南發生了大地震,岳母、小妹、外甥女都在大地震中罹難,岳父也轉到安徽當塗86醫院治療。母親說,“也許就是那次小產救了你媳婦,要不然七八月間正是預產期,要是在你丈人家也夠嗆。”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倚,看來有一弊必有一利。
轉眼到了第二批轉業幹部,楊副政委因為我寫仿宋字比較正規,全團轉業幹部的登記表就讓我填寫。那時還在團指揮連平房裡,我便插上門,一個人在屋裡填寫。一天,聽有人推門,接著又敲門,“大白天,插什麼門,給我開開。”我一聽是副主任的聲音,忙把正抄寫的登記表放進抽屜裡,這才去開門。
門開了,副主任進來,很不高興,“你幹什麼呢?這麼神神秘秘”。看來他知道我在幹啥,徑直走到三屜桌面前,拉開南面的抽屜翻看,南面的抽屜都是連排幹部登記表,他又拉開了中間的抽屜翻看,中間的抽屜都是營級幹部登記表,他終於看到了自己的登記表,再也沒有說什麼走了。
回去就與楊副政委大鬧了一頓,嗔究沒有提前跟他打招呼。那時軍隊幹部都不願意轉業,副主任也不想走,本來兩家關係特別好,一下子掰了。楊副政委一聲不吭,就那麼聽著他鬧,因為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性格,不該說的從來不說。
事情到此並沒有完,一宣佈轉業楊副政委也走,副主任吃不住勁兒了,又去找我,“小曹,我那天翻看登記表,怎麼沒有見楊副政委的?”我說:“楊副政委的登記表在北面那個抽屜裡。”副主任說:“那你怎麼沒跟我說一聲?”我說:“你也沒問那!團級幹部都在北面的抽屜裡。”楊副政委就在那年轉業了,不過,他是我在炮212團相處時間最長的副政委。
九口202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