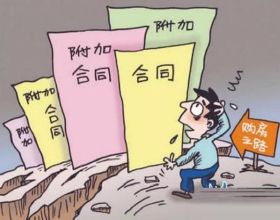內容簡介:
莊士敦在中國生活了三十餘年,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1919年-1924年,他身為溥儀的英文老師,見證和參與了溥儀所經歷的一系列浮沉奇遇。在這部“目擊聖經”的實錄裡,莊士敦不僅書寫了末代皇帝從少年到青年時代的身世,也藉此勾連起從義和團運動到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馮玉祥兵變等諸多重大事件的中國近代史。
作者簡介: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 出生於英國蘇格蘭。1898年被派往中國,1919年被聘為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英文教師;這位“帝師”早年在愛丁堡大學唸書,後來入牛津大學,得有文學碩士學位。他到東方來任職、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首先在港英當局服務,歷任香港總督府秘書、輔政司助理等職。在1904-1917年期間,他被英政府派駐租借地威海衛,直至任行政長官。莊士敦在遠東和中國人來往二十多年,會講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話,並且會讀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據他自己說,還於中國的佛教、孔子都有甚深的研究。
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後,不再擔任該職。著有《儒學與近代中國》《佛教中國》《紫禁城的黃昏》等書。
大清皇帝與“洪憲皇帝”
民國二年癸丑(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於是年10月6日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他的心願已經實現了,他略施手法,宣佈自己的總統為終身制,並且有權推薦繼位人。這時候,袁世凱的勢力大增,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解散。這一年的12月,副總統黎元洪應召入京,袁世凱表面上說是請他在北京輔佐行政,其實是生怕反袁分子利用他為工具。一切佈置妥當後,袁世凱即於民國三年頒佈修改過的新約法,任用前清的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國務卿,前清的山東巡撫孫寶琦為外交總長。
至於袁世凱個人對清室及宣統皇帝,則採取的是“恭敬”而不熱誠的態度。民國二年,袁世凱要實行“優待條件”的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的條文,請隆裕太后及清室離開紫禁城,遷往頤和園居住。此舉使清室人員極為狼狽。內務府的大臣聽到這個訊息,尤其嚇得魂不附體,他們深知宮禁已經移往頤和園,無異取消承認清室的初步表示,於是竭力向個愚昧的隆裕太后進言,請她提出強硬的反對。但“第三款”載在盟府,理應雙方遵守,提出反對,理由很是脆弱,虧他們想出一個辦法,向袁世凱指出,頤和園周圍的圍牆很矮,如果清室遷往居住,恐怕有壞人一跳就跳進園裡,對於皇室大有不利。
袁世凱為了應付清室這個反對移宮的理由,只好下令把頤和園周圍三英里長的圍牆加高几尺來堵住清室之口。加建的費用,當然不是出自民國的國庫,要清室掏腰包了。
一牆之隔的兩個世界
我是1919年3月3日第一次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的,這使我見到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上有距離的新世界。那是說,穿過這座神武門,我便從一個共和國走進一個“君主國”,也就是說從一個二十世紀的新的中國走進一個世界“最古的中國”,這個國家遠在羅馬還未建立之前已經屹立在東方了。在紫禁城外是一個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人民充滿著新希望和新的觀念,他們努力要使北京市成為一個新的民主國的首都,不讓它徒有虛名。這個城市有一所大學(譯註:指北京大學),萬千熱心愛國的學生孜孜不倦地在研究科學和哲學,他們研究世界語和馬克思學說
清朝官服的“官員”,他們仍然花翎頂戴,坐著轎子;年輕的貴族們多數騎馬;太監和蘇拉按著品級穿起制服,分立兩旁伺候那班大人下馬下轎,引他們到朝房等候傳見。內務府大臣細看這班大人的名單,哪一個準他見皇上,哪一個不準。最後,我們可以看見在宮裡的養心殿的一個暖閣裡,有個身材瘦長、穿得很樸實的十三歲孩子-這個孩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國的末代皇帝,被人稱為“天子”,又被稱為“萬歲”的人。這兩個世界相差得多遠啊!一個是進步的,要向著新的道路邁進,要把中國變成二十世紀一個新的國家;而另一個是反動的、開倒車的,“皇上”“大人”“謝恩”“奴才”等叫不絕口。
醇親王享有不跪拜特權
為什麼醇親王載灃見了遜帝不必行跪拜禮呢?因為他是遜帝的生父,做父親的怎麼可以向兒子行禮?中國禮法是不允許兒子比父親還尊貴的。同時,遜帝叫醇親王也不叫父親,只尊稱為“王爺”。原因是遜帝過繼給他的伯伯光緒皇帝為子,承繼大統,這樣便與本生父斷絕了父子關係。這樣一來,醇親王的繼承人不是遜帝溥儀,而是次子溥傑,將來襲爵的就是溥傑了。不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醇親王仍然是遜帝的“父親”,在整個宮廷中,只有他一個男人享有不必向遜帝行跪拜禮的特權。此外,也有幾個女人享有此特權,那就是在宮裡的四位太妃,還有遜帝的生母醇親王福晉。
師傅學生之間的禮節
我在紫禁城服務的年月,大抵可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19年3月起,到1922年11月遜帝結婚時止。第二個時期是1922年11月以後,到1924年遜帝被驅逐出宮止。這樣的劃分法不過是為了便利起見,因為這樣可以清楚地標出他的生活方式的變遷。遜帝在大婚以前,還未能完全自主,他所能決定的,只是一些細小的事情,但大婚之後可不同了,他已經成年,可以自由自主、為所欲為了,只要他的目光不望得太遠-望到紫禁城以外憧憬著外邊的一切,大概沒有人敢於干涉他的行動。
在第一個時期中,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書房上課。毓慶宮久為皇帝讀書之所,在此以前,曾一度為嘉慶皇帝做太子時的寢宮。它有一道小門通到一個小院子,這兒有一列配房,專為師傅們使用,有好幾個蘇拉伺候師傅們,招呼茶水。每一位師傅都是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但如果他要方便,也可以從東華門或西華門進入。到達之後,下了馬車或汽車(只有我一人坐車),坐上內廷特備的轎子,由轎伕抬著穿門過戶而進,每過一門,有武裝的警衛軍向他行禮。我有時也使用我個人所獨有的“異數”,一直騎馬入紫禁城。到了內部的景運門,下轎的下轎,下馬的下馬,步行經過祥旭門、惇本殿,再進而到毓慶宮。
遜帝“御筆”
我和遜帝的師生關係,一開始就很融洽,後來發展到越來越好的程度,我覺得他很聰明,性情坦率,他不只很熱心地去了解中國的一切事情,就是對世界大事也很留心。他待人以寬恕,不念舊惡,對貧苦的人很有同情心,又樂於為善,並且也有幽默感。近日讀他的自傳,他對自己的壞處也很坦白。在我未入紫禁城以前,他對英文是完全不懂的,也不想用功於此,希望精通這種文字。他對於學習語言並不十分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國際發生的事情(包括歐戰前後以至凡爾賽和會時的歐洲事情)、地理和旅行、自然科學(包括天文學)、政治學、英國的憲政史,以及中國日常發生的各項政治問題。我們見面時,常常用中國話隨便討論以上各種事情,當然,我們是在授課的時候談論這些問題的,把授課的時間佔去了。遜帝精通書法,因此他對寫字極有興趣,他學習英文不久後,已寫得一手很好的英文書法,有很多和他同年歲的英國學童見到了也應為之佩服。
溥儀最崇拜墨索里尼
我和遜帝的師生感情一向是很融洽的,在我的服務期中,我們相處得很好,就是現在回憶起來,也很令人愉快。當我在紫禁城裡的時候,對於義大利那個政治家非常崇拜,認為那個人能使義大利人走向新的生活,是了不起的。因此他收到黑衣宰相墨索里尼託義大利公使轉贈親筆簽名的一張照片,感覺很是榮幸。不過,照我看來,遜帝是知道他不會是一個墨索里尼的塑形的。
五四運動與反日狂潮
我在前文曾說過,遜帝對於中國政治舞臺上所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十分感興趣,所以他訂閱了很多報紙,自由閱讀,埋頭埋腦去研究、探討報紙上登載的訊息。我常常發現他在坐著,面前堆著一大堆高如山的報紙,其中有北京出版的,也有天津、上海、廣東出版的。我見到這個情狀,曾勸諫他,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光陰可惜,犯不著花這麼多的寶貴時間來讀這些無用的東西。
他往往答我,他讀了這些報紙,發覺它們所記載的新聞雖同是一事,而甲報所記,與乙報不同,丙報所記,又與丁報不同,黨同伐異,歪曲事實,到底這件事的真實情形如何,無從判斷。有這種情形,遜帝就要憑自己的聰明,用腦力去辨其真假了。幸喜他獲知有關中國的事情,不完全靠報紙供給,他常常收到他的舊臣及宮廷人員的有關中國政治的情報,這些情報或是書面報告,或是口頭報告,類皆公正可靠,不像報紙所載的那樣有偏見。我也時時向他講說歐洲發生的事情,他聽了也同樣有興趣,並且很表關切。
我們同在一個動盪的時代生活。當我在1919年擔任遜帝的英文師傅的時候,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五強”在巴黎喜氣揚揚,繪製一幅新的世界地圖,並草擬一個可悲的條約加諸戰敗國,保證世界從此永遠和平,不見兵戈。在中國,一般有政治思想的人皆把目光集中在青島問題。青島這個地方,本是德國人藉口教士被殺,強迫清政府將膠州灣租給他們的,租借到手後,德國人又修築膠濟鐵路,大傷中國主權。
到1914年歐戰發生,日本帝國參加英法集團,從德國人手上將青島搶去。當凡爾賽和會開會時,中國人要求在和約中規定青島及德國人所築的鐵路以及其他利益應無條件全部交還中國。日本在和會中提出有關青島及舊時德國利益等問題,應由日本直接與中國談判,不必載入和約,在談判期間,青島仍由日本管轄。中國人對日本這一提議,竭力反對。但日本這一提議,似乎在凡爾賽甚得“五強”的贊成,因此更引起中國人的憤怒,於是發生了五四運動,由一班愛國學生領導,打倒賣國賊等。愛國學生振臂一呼,全國學生響應,繼而全國商人罷市,抵制日貨,盡力支援學生。北京政府被這個情形嚇慌了,終於訓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不得在和約中籤字。
遜帝對於這些事情都予以密切注意,同時,對於中國地方上的軍閥橫行、政客的興風作浪,以及國會議員(這時候,中國有三個議院,各自稱為“正統”)的活動等,也同樣關注。我常在書房或乾清宮他起居的地方,和他很隨便地討論這些問題。
張勳復辟失敗的主因
當我在1919年2月要到紫禁城服務的時候,距離張勳搞的復辟把戲不過十九個月。我在上文曾經提及,張勳的復辟失敗,其主要原因不在那些有軍事、政治力量的掌權者不同情他,拒絕和他合作。其失敗的大部分原因是張勳個人的愚妄,自以為他一個人就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把那個兒皇帝扶上寶座,對於復辟派人物不加信任,甚至到了時機成熟時,這個辮帥還剛愎自用,不肯和這班同事坦白商量,又對他們的官癮不能予以充分滿足-他們所希望的是一旦天子重坐龍廷,他們個個都是開國元勳,可以得到攝政、總督、巡撫這些職位。但事情竟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他們就存有不合作的心理,到了大勢將去的時候,張勳也不和這班人商量,一直把他們當作圈外人,這樣張勳就註定失敗了。譯註:莊士敦對復辟一事所下的斷語,不能說是觀察正確,其中有許多複雜的因素與內幕為莊士敦所不知道的。
在這短短的十九個月中,中國人並不會忘記張勳復辟的把戲。後來徐世昌被選舉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清室那班人皆大歡喜,以為大有希望了,因為徐世昌這個人是舊日清朝的大官僚,他一上臺,還不替他的舊君打算來光復故物嗎?甚至徐世昌就職後第一個行動不是赦免張勳,取消他的通緝令,這班人也沒有覺得失望。至於中國人的人心趨向,也是值得一說的,有好些地區的中國人對於中華民國失望已極,人民認為民國政府所答應的事情沒有一件做到,反而使人民生活窮苦,日在兵戈之中。
當時歐洲人的報紙就廣泛地反映這種情形,它們的內地通訊對這些情形有詳細描述。寫這類通訊的人大部分是教士,他們眼見辛亥革命把那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推翻,他們也很熱心地擁護新政府,希望新政府成立後,中國會日漸富強興盛,中國人民和西方國家的友誼更為增進,以前很多不讓教士前往傳道的地方,現在門戶開放了。怎知事情並不是這樣,這班教士也失望了。現在我摘錄1919年6月23日上海《字林西報》一段甘肅通訊,便可
見其一斑。它說:苛捐雜稅以及官吏的貪汙枉法,使人民懷念清朝,渴望清朝能夠有朝一日恢復它的政權。人們認為清政府雖然很壞,然而中華民國比清朝更壞十倍。我們不只在這個偏遠的地方聽到這種慨嘆之聲,希望清朝捲土重來,就是在其他地方,也聽到人們期待著復辟。
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當遜帝還未滿十六歲之前(這個時候是1920年的末季),他對於宮裡的種種制度、習慣,都覺得不耐煩了。他要自由發展,什麼時候做什麼事,他要自己決定,什麼時候玩要,也自作主張,不肯受到那些繁文縟節的制度的束縛。他往往在宮裡走來走去,從這個門走到那個門的盡頭,不愛坐在那頂黃轎子裡讓人抬著他走路了。他的年紀漸大,已經有點懂事了,他看出自己是個有名無實的皇帝,但他左右的人仍然拿他當作真皇帝看待,他看了真覺得不舒服。
遜帝熱切地渴望走出紫禁城看看這個現實的社會,但他卻不能如願以償,有時他在御花園假山最高之處,或靠近神武門左近的亭閣向外邊窺望,更使他野心勃勃,要出去玩玩才覺得安樂。每逢他請求到紫禁城外玩玩的時候,內廷的人就會阻止他,對他說,外面是個危險的地方,南邊孫逸仙的革命分子時時刻刻在等候機會侮辱他、毆打他,甚至將他置諸死地。所以最好就是不要離開紫禁城一步。將來總有一日他可以自由行動的,但在這個時候,他仍須忍耐,自由的日子還未來臨。譯註:這些人所說的一番話,豈知四十年後,溥儀以平民身份在北京街道上自由行走了。
結果遜帝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機會來了,但這是一個悲慘的機會。他的生母醇親王福晉於1921年9月30日逝世了。她是死在北府-在北京城北的醇親王府,遜帝出生的地方。在10月初,遜帝到北府行禮他曾在北府停留了半日。這一天他離開紫禁城之前,打從神武門起,以至景山之北的街道,通至鼓樓這一帶,沿途佈滿民國的軍警,加以保護。
遜帝想避居東交民巷
1922年春的軍事政治危機,又引起紫禁城那班人的恐慌了,他們認為在此種局勢之下,只會使遜帝的危險增加,於是又舊事重提,利用我去英國公使館找英國公使,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給遜帝安排一個避難所。這時候,繼朱爾典為駐華公使的是貝爾貝·阿爾斯頓爵士(Sir BeilbyAlston),我把來意向他說明後,阿斯頓爵士很表同情,但他不想由英國公使館公開這樣做,恐怕蒙上不潔之名,為中外人士指責英國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他向我建議,在英公使館裡撥出一個房間給我居住,我以遜帝師傅的名義住在這個房間,而邀請我的學生去同住,當作我的客人。同時,我又和葡萄牙公使、外交團首席代表弗列達先生及荷蘭公使歐登科先生商洽,一遇事態緊急時,皇室人員可以到他們的公使館暫時託庇,這樣便可以萬無一失了。
受人豢養溥儀感恥辱
儘管外界這樣亂糟糟,軍閥們通電相罵,然後兵戎相見,但在紫禁城裡的那個“宣統皇帝”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廝殺之事。這時候他已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了。他不僅覺得他在紫禁城裡過著的生活令人討厭,同時也漸漸知道那個腐化的機構-內務府的種種壞處。他看出內務府的人什麼都不理,只要維持現狀他們就滿足。現狀能夠維持,那不是等於說他們的飯碗不會摔掉嗎?此外,遜帝也知道自己擁有一個“皇帝”的虛名,而實際上沒有皇帝的權力。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愛國者,對於一度曾是他的子民的中國人連年受戰爭之苦,很是關懷,他渴望著中國能有進步繁榮的一日,所以他時常覺得像他這樣的一個拿公家錢而不做事的人,實在是恥辱。事實上,民國的優待費雖然日見減少,在不久的將來,只是變成徒有其名的一張空頭支票,但遜帝絕不會因此情形而減少他內心的不安,而滿意於現狀。即使就是他在名義上是一個民國政府豢養的人,他也認為恥辱,他和我談話時就屢次這樣表示過。
馮玉祥逼宮前夕的紫禁城
1924年中國發生了一次很大的內戰,引致北京政變。首先是浙江的盧永祥和江蘇的齊燮元打起來,繼而是東三省的軍閥張作霖為了援助他的盟友盧永祥而派兵入關,攻打直係軍閥曹錕(時為總統)和吳佩孚。吳佩孚帶著他的“討伐”軍到了北方,他在北京的“四照堂”排兵點將,由曹錕下令討伐奉系軍閥。吳大帥準備一切後,將往山海關督戰,並誇說他此行必獲大勝,一個月內便可以打到瀋陽。
1924年9、10月之間,南北雖有戰爭,但紫禁城裡並沒有受影響,一切安靜如常。“基督將軍”馮玉祥是吳佩孚在北方的一位重要將領,雖然有人認為他對吳有不軌之心,但他卻沒有什麼異動,仍然忠於吳大帥,也許他在吳的監視之下,不敢有什麼行動。吳佩孚的大軍在10月初和奉軍惡戰,據前線的情報,直軍穩操勝券,不久便可有機會攻入瀋陽了。吳佩孚派馮玉祥的軍隊把守古北口,鎮守北方最重要的關隘,以防奉軍從側面進攻。吳大帥此舉並沒有失算,只是他委託非人而誤了大事。也許他是不想使馮玉祥分去他的嫡系軍隊攻入瀋陽之功,同時,又怕馮的軍隊駐在北京區域不大妥當之故。他顯然沒有想到馮玉祥對他懷有怨恨之心的。
10月17日,我見遜帝很是憂鬱,沒精打采的,那並非與中國的政局有關,而是光緒帝的瑾妃病重,已經到了群醫束手無策的時候了。我就在10月17這天往西山的櫻桃溝別墅小住一時,21日我在山中步行,又騎馬經過了山岡到達頤和園,即在頤和園住了一夜,就聽到瑾太妃逝世的噩耗。第二天我駕車回北京,奇奇怪怪的謠言滿天飛,但北京城的外表上還很平靜。這一天我沒有進入紫禁城。
景山之上堆滿著大兵
10月23日清早,我的一個僕人大驚小怪很緊張地走來對我說,內城的北面有兵變發生,後門(這是一條有城門的大街,距離我住宅北部約數碼之遙)已經關閉了,有軍隊把守,電話不通。路上的行人大驚失色,有錢人家紛紛搬入東交民巷,住到六國飯店。(北京的有錢人,一遇政局變動,往往避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所謂兵變之說,後來證實不過是謠言,並無其事。但真正發生的事情,卻是馮玉祥主持而得到十分意外成功的政變。原來馮玉祥的軍隊沒有遵命開赴古北口,而是半路折回北京。和他合作的兩位將軍,一個是孫嶽,一個是胡景翼。吳佩孚留下他們駐守北京附近一帶,但他們暗中和馮玉祥將軍約好了,10月23日天色未明之前,駐軍開了城門讓馮玉祥的軍隊長驅直入。軍隊入城後,分別控制了火車站、電報、電話的交通中心,並派兵包圍曹錕總統的住宅,把那個倒黴的曹三爺從好夢中驚醒過來,想逃入東交民巷託庇外人,但路不通行,被軍隊活捉了。
我還不知道這次的具體情形,以為不過是兵變罷了(中華民國兵變的事,常常發生,我們見慣了),我驅車往紫禁城,到了景山與紫禁城之間的一條大路中,見到情形不妙。景山是北京城裡最高的一個地方,俯瞰全城,形勢險要,我見景山上面的建築物和山坡上滿是軍隊。正對神武門的景山門,也站著軍隊多人,他們穿的卻不是紫禁城護軍的制服。神武門一切如常,很是平靜,我的轎子照常停放在門外等候我。守門兵士照常向我行敬禮。
我到了遜帝居住的地方,人們對我說他在御花園我的養性齋裡等著我,並盼望我立即和他相見。我到了養性齋,見遜帝坐在我的書房裡,有幾個僕人隨侍左右。他見到我,就叫他們走開。
御花園漫步遜帝憂心
遜帝對於今晨發生的事情比我知道得更少。我初見他時,並不提到這件事,只說到端康太妃之死,慰唁他一番。他問我知否有軍隊把景山佔據在這個時期,紫禁城裡的氣氛日漸恐怖了。瑾太妃死後,宮裡在辦的喪事,如果在平時,喪禮必定大事鋪張,但現在卻無形中受到了限制駐紮在景山孫嶽的軍隊,漸漸撒野了,他們故意留難出入紫禁城的人,人告知我,孫嶽的軍隊每日都滋事,意在找尋藉口,以便引起紛爭。
11月2日星期日,黎明後不久,遜帝就召我入宮開會,我到了養殿,見到榮源(遜帝的岳父)和鄭孝胥已先在座了。他們一致相信馮玉正在動念頭,來另一次突然的行動,其目的就是針對遜帝。我們討論用麼最好的法子把皇上立即撤出紫禁城,走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但通往禁城的每一道門都有軍隊嚴密地把守著。據我個人觀察所得,把守著神門的皇室衛兵已撤入神武門內,而孫嶽的軍隊則已在神門外守衛著了。遜帝交給我一捆很重要的檔案和一包貴重的物品,讓我找個安全的方存放。後來我把這些東西放在匯豐銀行。
不久後我又回到紫禁城裡,因為我要親往端康太妃的靈前致祭。祭後,我到遜帝的住所,向他報告那些貴重的東西已經存放在很妥當的地方了。他開啟櫃門,拿出一個小匣子,揭開匣蓋,裡面滿是珍珠寶石的形指。他笑著說:“這些東西都是端康太妃的,如果仍然留存在她的寢宮裡一定會全部被人偷光。你就挑選一個留為遺念吧。”於是我便選擇了一隻綠玉戒指。
慌慌張張直闖紫禁城
11月5日,星期三。我正在吃早餐的時候,有電話找我,這次的電話通了,我聽到對方的聲音很是慌張,但立刻認出他是載濤貝勒。他給我訊息雖然是在我的意料中,我不覺得奇怪,但也使我極度不安。他說,馮玉祥的軍隊已開入紫禁城,佔據神武門了。他們不讓任何人出入。皇上的電話線已被割斷。沒有人知道皇上的情形如何。他問我可否陪他同往神武門,設法進入宮裡。譯註:利用外國人勢力保駕,這倒是個好方法,載濤以為外國人是天之驕子,什麼都辦得到,中國人遇事都給他們面子也。
不到十分鐘,載濤自己開著汽車到我家中,他一直把汽車開入院子,下了車,就把車子停在那裡。他願意坐在我的車子裡同往紫禁城。我連忙開了汽車和他同往,不消幾分鐘便到了神武門,但三道大門都關閉著,並且有軍士嚴密把守。我的汽車在景山前就被攔下了,一個軍士上前查問。我拿出我的中文印成的名片給他看,並對他說我是有權進入紫禁城的。他拿了我的名片去請示他的上司。在他離開我們這兩分鐘裡,和我同車的那位濤貝勒很激動地對我說:“如果他們讓您進去,您就對他們說我是您的僕人。”
他說的這句話留給我的印象畢生不能忘記。他的內心依違於兩種感情之間-他生怕一進目前這個危險的紫禁城生命便有危險,但他又想到如果能他希望可以假稱是我的跟班隨同入紫禁城,而不會被守軍看出他的真面目。
滿族的天潢貴胄一向是自尊自大的,而這句話竟出諸一個貴族之口,可見其內心之痛苦。如果那個不可一世的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眼見他們的子孫-這個子孫,他的哥哥是皇帝,侄兒也是皇帝-為了要偷入他的祖先征服了的紫禁城而不惜冒充洋鬼子的僕從,不知作何感想。慈禧太后在庚子之役也是要把洋鬼子盡行逐出中國之外的,她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她的子孫中有一個人說過這樣的話,她又不知作何感想了。
溥儀出宮的詳細情形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深夜,攝政內閣舉行攝政會議,決議清廢帝宣統,即日遷出皇宮,這實在是代表大多數國民意願的措施。負責執行這項任務的是警備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並請李煜瀛做國民代表,會同辦理。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時,警衛司令部先派出軍隊,到神武門一帶,把駐守該地的警察改編資遣。這裡的警察,共有四隊,每隊約一百二十多人,駐守在神武門護城河的營房裡。
這次的編遣工作,到十二時就全部完畢。神武門一帶的警衛責任,正由警衛司令部接收的時候,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及李煜瀛諸人,也就會同清室內務府大臣紹英,在上午十時去見溥儀,要求他即日廢去尊號,交出宮廷印璽,並遷出皇官。到下午三時,溥儀和他的夫人、親屬等,乘汽車出宮,遷到什剎海的醇親王府裡去。溥儀出宮之前,交涉情形,當然是費了若干周折的。不過,情勢所迫,他自然是非遷不可了。出宮之後,還留下不少的問題,在清室方面的,主要是瑜、瑨兩太妃的拒絕遷出;在社會上的,是一般前清遺老與復辟黨人的抗議。清室方面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出版的《社會日報》,對此有綜合性的報道說:“關於清室之善後事宜,中外人士,非常注意。茲將昨日所得訊息,報告於下:一、清室所有之警衛隊,業於昨晨解散完畢,現由鹿司令派所部步兵代任警衛之責。二、溥儀夫婦及瑜、瑨兩妃之應用器具物品及衣服等,已次第由清室運送出宮。三、藏於庫內之元寶銀,昨日下午一時,由雙方委員共同監視,先將藏於裡庫者過秤,計秤得該庫銀兩共六千三百三十三斤,合十萬一千三百二十八兩。秤畢,僉以該元寶均鐫有福祿壽喜字樣,每顆均重達十餘斤,確係當時清帝用以為犒賞之用者,遂議留數顆,為將來陳列之用,其餘悉數發還。當即由鹿司令飭兵當眾代為裝包,每包裝訖,即書明數量於其上。俟全部裝訖,即由鹿司令派兵百餘人,並由雙方派員監押送往清室所指定之監業銀行。
事畢,清室代表因士兵勞苦,請以一千兩為犒賞搬運銀兩兵士之用,但鹿司令則璧還之,謂此事乃吾人應為之事,無犒賞之必要。清室代表因強之至再,終不允受,乃致感謝之意而退。至於外庫之銀兩,其數稍少,截至下午五時,尚未秤畢,此則須容明日再行報告矣。四、瑜、瑨兩妃前此之所以頗躊躇於出宮,蓋恐物品錢銀,不易攜出,現因政府方面,對於非古物之物品及金錢,無絲毫留難之意,遂決計擇於陰曆十月二十五日出宮,現已以此意令清室代表轉告鹿司令矣。······到十一月二十一日,瑜、瑨兩老妃出宮之後,遷到北京寬街大公主府裡。溥儀出宮問題,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遜帝對我談出宮經過
遜帝帶我到他的私室裡,我們安詳地坐下來談話。他的態度顯得還是那麼高貴而又泰然自若,他對於在外面大廳上那班人驚惶失措的舉止,大為鄙視。關於遜帝離開紫禁城的經過,後來內務府的官員詳詳細細對我說了據說,那天早上大約九點鐘左右,馮玉祥手下的鹿鍾麟到了神武門前,命令軍隊將紫禁城的警衛解除武裝,然後留下一隊軍士在神武門外收集槍支,並禁止未經准許的人出入,鹿鍾麟和北京文化界名人李石曾進入紫禁城,叫幾個已解除武裝的警衛帶他們到內務府。他們到了內務府,就要求見“溥儀先生”。有一個侍從對他們說,皇上在皇后宮裡。他們就大聲大氣用挑釁的語氣說,他們來叫“溥儀先生”和他的妻子、兩個太妃在三小時內離開紫禁城。“如果他們再事耽擱,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就不能負責了。”
於是他們拿出一件公文交給內務府大臣紹英,叫他立刻交給“溥儀先生”,要他接受修正的優待條件。這些條件是沒有商量餘地的。修正優待條件的條文開頭的一段,用遜帝的語氣說他自願修正的,現在將其譯為英文如下:譯註:我現在省去譯文,將原文錄此,以符真相,因為從英文再譯成中文,必定走樣的。
修正的清室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 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 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款,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居住,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 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第五條 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這件公文是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由攝政內閣所發的。上面也有鹿鍾麟和京兆尹王芝祥、警察總監張璧的名字。內務府大臣接到這個公文嚇到作聲不得,連忙送給他的主人,但他的主人比他較為鎮定,一點兒都沒有恐懼。現在最麻煩的問題就是那兩位年老的太妃了。據遜帝對我說,兩位太妃拒絕出宮,她們說如果國民軍用強把她們趕出紫禁城,她們只好自殺。
最後一次經過神武門
遜帝和皇后只拿一些個人的物品-鹿鍾麟等人不許他們多拿東西-步入御花園,在花園之北,他們的汽車停放著。他們上了汽車,沒有權利選擇他們所要去的地方,恰恰和攝政內閣的指令裡的修正優待條件中所說的,他是民國的一個自由的公民“以後得自由選擇居住”相反。
他們分別上了汽車,每一車子只限一個隨從陪著,一個兵士坐在司機旁邊,另外兩個武裝兵士站在車門外的踏板上,以資保護。車子一開出神武門也許就是他們最後一次了-隨後就有裝滿軍士的車子跟著,加人隊伍而去。汽車很快開過了景山,經過我的住宅,出後門,
本來出皇城這一道門平時是關閉著的,只有在遜帝經過時,仍援舊日之例,開放給他行走。現在使遜帝第一次感覺到無此尊榮了。他們顯然是要教訓這個“溥儀先生”,提醒他。你也不過是個平民而已,與中國其他平民並無任何分別。
北府是遜帝父親的私邸,在此種情形之下,以北府為遜帝居停,實非遜帝本人所願。因為這個地方在城北,距離北京城中區約三英里之遙。他所要住的應是使館區,但這是鹿鍾麟等人不肯讓他去的。他到了北府之後,僅僅在一小時內,遜帝就覺得自己變成一個被軟禁的人了。他要試驗一下是否有自由,就吩咐備車,他要出門兜兜圈子。在這個時候,醇親王府原有的警衛已被撤換,改以國民軍守衛了,他們聽說遜帝要出門遊玩,便說他們奉令保護,“溥儀先生”最好留在家裡,不要出門。
末代皇帝的悲劇之路
我來不及向醇親王辭行,即走向大院子裡,上了我的汽車。外面的門已經關閉了,我叫門,他們才把門開啟,但在我出門之前,有個警官走上前把汽車裡從頭到尾搜查一遍。此舉顯然是以為遜帝會躲在我的毛毯下面,由我偷運出去。
我在使館區差不多逗留了兩個鐘頭才回家裡去,一方面,我深為清王朝慶幸,蠶食它的那個內務府已垮臺了。我一向都希望遜帝能擺脫內務府那班人的包圍,自由做人,現在可實現了。不過,這次的事變,純出於被動,而非遜帝本人的請求,實在不能不令人有遺憾。我孤零零地獨自一人坐在書房裡胡思亂想,想到我在頤和園那些快樂的日子,想到幾小時之前和我道別的那個皇帝也走上了歷朝末代帝王所走的悲劇之路,又想到我一向所希望的好像馮玉祥已做了的事情,竟然在今日發生。
這就是11月5日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一天,在紫禁城上徘徊了十三年的黃昏,終於轉入黑沉沉的夜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