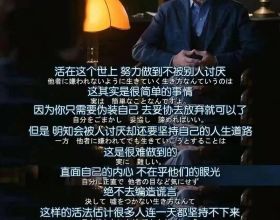豬獾子在農村很招人憎惡,外表憨厚,糟蹋莊稼讓人咬牙切齒,拱紅薯土豆不說,吃玉米最讓人討厭,玉米剛長出一穗嫩嫩的小米粒,獾子就開始每晚來糟蹋,偏偏吃相又很難看,先是將玉米稈撲倒,再將玉米棒外殼三兩下撕開,再急匆匆的啃幾口玉米,一根玉米棒子還沒吃到三分之一就又去糟蹋另一棵,一隻獾子一晚能毀掉十幾棵玉米,被撲倒撕開的玉米棒子又會招來老鼠和鳥類繼續搞破壞。
打獾子不需要獵槍,兩條狗,一把鐮刀,最多再加上一把錨鉤即可,夏秋的獾子不好吃,羶騷氣味很重,要等到農曆白露之後,獾子已吃出一身肥膘,滿身長出灰白色冬毛,邁著肥短的四條腿準備冬眠時才是逮獾子的好季節,臭味小,肉也變得肥瘦相間,加上辣椒桂皮先燉再炒,味道相當霸道。
那年我養了一條好狗,名叫烏嘴,夏天烏嘴才六七個月的時候我就天天帶著它巡視家裡的玉米地,教它辨別獾子的氣味,鍛鍊它的循跡和追蹤能力。到秋末時,烏嘴已長成大狗了,雖然還沒正式逮住過獵物(開嘴),它倒也喜歡整天漫山遍野的追野雞兔子。有一天我爸說狗也要有“狗師傅”,有經驗的老狗帶它打幾次獵了這狗應該還不錯。
我爸說這狗有潛質是有道理的,這烏嘴,個子不大還偏瘦,鼻豁大,溼鼻子,尾巴是典型的蛇尾。肥狗或掃帚尾的狗要麼懶要麼耐力差,枯鼻子小鼻豁的“撿氣”不行。
從那天之後,我就開始找上三爺爺了,三爺爺愛打獵,家裡養了兩條狗,每年冬天都會打上幾隻麂子掙點過年錢。
秋天在農村還很忙,收秋,砍柴預備過冬,地也要翻一遍等冬天上凍凍透,凍透了的地來年開春之後特別鬆軟,好耕種。所以雖然我找了好多次,也一直沒能成行。
直到一個下雨的清晨,我還沒起床就聽見了狗的銅鈴響聲,接著就聽見三爺爺叫我起床,我急匆匆爬起來開啟門,三爺爺說:“餘老三家天坑坪的晚玉米地裡說來豬獾子了,你一隻說要我帶帶你,趕緊收拾收拾走吧。”
我二話不說,拿上鐮刀,給烏嘴套上銅鈴就跟著出發了。天坑坪在河谷陰坡邊,往下幾百米就到三叉溝,四周都是懸崖深山,每年都會被野牲口糟蹋不少。等我們趕到,雨已漸漸停了,濃厚的白霧遮天蓋日,樹林子裡露水早已將人狗淋溼的不像樣。到了玉米地邊,三爺爺對著狗群一聲吆喝“尋起”,兩條大狗馬上緊張的沿著莊稼地的邊緣開始搜尋,烏嘴也急匆匆的跟著忙的不亦樂乎。
十幾分鍾之後,領頭的大狗幾聲急促的叫聲傳來,三爺爺大喊:“開叫了,往下山去了,你從山腰下溝,我去溝底慫狗”,接著他就飛快的跑了下去。我一時慌不擇路,一步跨進了灌木林子,全是藤蔓刺條困的我舉步維艱,等我跑了一半,就聽見狗叫聲已經過了溝正在往對面山坡追趕,三爺爺也到了溝底在喊我:“畜生上坡了,沒掉騷,你趕緊下溝到白崖下邊坐起哦”。可憐我一臉懵逼的擦著滿頭的露水,白崖在哪我也不知道啊,不管了,先下溝再說。揮著鐮刀邊砍邊往下溜,終於到了溝底,可狗叫聲已經聽不清了,只感覺頭頂上方很遠處狗叫聲汪汪一片,夾著山谷的迴音,完全辨不清方向,偏偏大霧罩的我找不到白崖在哪,著急忙慌的順著河谷往上游尋找,本來鞋底已沾滿了林間的粘土,河谷的石頭淋雨之後滑的像抹了油,頓時一個屁蹲摔得我眼冒金星。
正懊惱時,隱約聽見狗叫聲漸漸又近了,我趕緊跑了起來,終於看到不遠處一堵石牆般的懸崖白花花的,二三十米高四五十米寬的樣子。我跑到崖下使勁伸著脖子聽動靜,三爺爺又喊了:“五爪要上徑噠哦,崖下要坐好”。我一聽就興奮了起來,五爪說明今天追的果然是獾子,而且正在朝我逃來。我手裡除了一把鐮刀啥武器也沒有,手裡攥的汗都出來了。
正當我焦灼等待的時候,林子裡傳來幾聲我沒聽見過的叫聲,很像小豬娃打針時的慘叫,接著是狗打架時的嗚嗚咆哮,接著又是狗捱打時的一聲尖叫,我在崖下手足無措,三爺爺應該還沒追上狗群,只聽他在大聲的吆喝:“咬到!咬到哦,嘚兒咬死它"!接著又是幾聲豬叫,頭頂還是往下掉落石子樹葉子,我在崖下伸著脖子什麼也看不到,只聽見聲音越來越近,我半蹲著做好預備起跑,緊張的盯著白崖側面的豁口。
突然,崖邊的樹苗急促的晃動,還伴隨著不知是獾還是狗蹬起來的枯枝落葉“滾滾而來”,我使勁瞪著眼睛透著大霧看去,一隻獾子和一條大白狗交纏在一起從崖邊的陡坡翻滾而下,另外兩條狗緊追在後邊。那獾子一身灰毛圓滾滾的,一邊揮舞著四肢想攀爬住逃跑,一邊又呲牙咧嘴的攻擊群狗,領頭的大白狗咬住獾子的後背一直沒鬆口,鼻子裡嗚嗚的咆哮,還時不時的猛擺幾下頭,可惜獾子太肥大,狗沒辦法將它甩動,所以狗一直沒機會換口咬住脖子,一沒注意臉上已被獾子刨了一爪,稍一鬆口獾子已一個翻滾逃了下來。
眼看獾子離我已經只有十來米遠了,我趕緊迎了上去,一聲大喊慫狗:咬到!獾子一驚一扭頭,我的烏嘴一躍就騎到了獾子身上咬住了後脖子,緊接著大白也一口咬住了獾子的屁股。那獾子拖著兩條狗速度猛地慢了下來,我跑過去舉著鐮刀躍躍欲試,又怕傷了狗,只能一直堵住獾子的去路,另一條落後的獵狗也終於趕了上來加入了撕咬。我見狀料定今天這獾子已經在劫難逃了,對著崖上喊三爺爺:“咬到噠,跑不脫噠哦”!
三爺爺很快就傳來了迴音:“叫狗子咬,告(教)哈狗子蠻好”。
十來分鐘後,三爺爺也趕到了,狗群還在撕咬,獾子已經漸漸沒有了還手之力,嘴還在呲著牙嚎叫。三爺爺見狀開始轟狗,拎著大白的項圈使勁拽開,一邊拽跟我講:“狗要牲口時要連著後頸皮一直拽,這時候狗紅了眼,你要一邊吼一邊拽,要不它會咬人護食”!
一番忙碌之後,獾子已被三爺爺塞進了蛇皮袋子紮上了口,群狗吐著舌頭流著口水趴在石頭上休息。三爺爺捲了一支旱菸點上後說:“你這烏嘴真不孬,撿氣起騷都蠻快,就是個子小咬口差,你看我那大白,花舌頭,咬住就不鬆口”。
我還替烏嘴不服氣,“剛才大白是咬屁股,還是烏嘴咬上脖子了呢”。
“今天是咬獾子,以後要趕豬子“野豬”你就曉得了。今天還可以,一個歇茶(倆鐘頭左右)就把牲口趕到噠,不耽誤回去吃早飯,哈哈哈哈”。
我和三爺爺砍一根樹棍抬著獾子一邊走一邊聊著,走到我家烤著火,全身的溼衣裳烤的冒白氣,又教了我很多打獵的技巧以及獾子要是進洞了的辦法。我爸拎著獾子在秤上稱了稱,三十來斤呢,對三爺爺說:“三叔你拿回去吧,他小孩子就是跟著好玩的”。
三爺爺說:“我不要,這季節的獾子還不好吃,小伢子喜歡玩這也沒啥,今天算是運氣不錯。這個狗子也還可以,多告(教,馴的意思)哈。我剛才趕獾子的時候查到幾個黃麂子的跡,等過幾天忙完了喊幾個人一起去玩幾天”。
那條烏嘴我養了三年,特別擅長趕豬獾子果子狸,慢慢在圈子裡竟混出了名氣。後來我應徵入伍,有人上門找我爸商量五百塊錢買烏嘴,我爸很乾脆的拒絕了那人。那之後一個多月時,烏嘴失蹤了,再也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