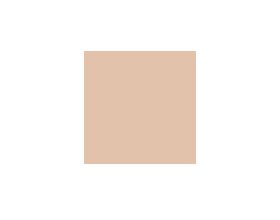文:戴二彪
許多國家都有正規教育體系之外的教培機構。若論數量和影響,有考試選拔傳統的中日韓三國無疑最為突出。在日本,按業務內容,教培機構可分為兩大類:學習塾和其它。其中,學習塾“主要以中小學生為物件,提供與學校課程相關的課外教育服務”,影響到千萬家庭,廣受關注。
2020年,日本有近5萬家學習塾,從業人員約32萬人。縱觀學習塾的發展史,從其迅速擴張的1970年代至今,日本文部省的學習塾管理政策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的變化。
上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後期:批判和抑制階段
伴隨戰後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人口城市化,1970年代日本進入所謂“1億總中流”時代,家長對子女教育愈加重視,大眾化的學習塾也迅速增長。1970年代後期,全日本的學習塾已超1.5萬家,但業務不歸文部省管轄,媒體稱之為“亂塾時代”。
隨著媒體對學習塾負面報道的增加,1976年文部省首次在全國實施了“學生校外學習活動的實態調查”,次年釋出了《關於規範學生校外學習活動的通知》,並提出“以充實學校教育和改革入學考試製度為中心”的對策。1985年,文部省第二次實施了同名調查,發現中小學生課後通塾比例進一步上升。1987年文部省在《加強學校學習指導的通知》中,首次公開批評了學習塾,強調“課後通塾是關係到學生健康和學校教育信賴的重要問題”。為了抑制課後通塾,文部省要求全國繼續充實學校教育和改革入學考試製度。此外,不少地方還直接要求家長和學習塾共同自律,限制孩子通塾次數和聽課時間。
但是,由於日本政府部門和大企業普遍重視名校畢業生,應試教育的社會需求根深蒂固。上述對策不僅效果有限,有些反而事與願違。比如東京等地改革公立學校入學考試製度後,公立名校的入學難度確實大為減低,但導致公立學校學力的普遍下跌和私立學校的崛起,直接拉昇了公立學校學生的課後補習需求和應試私立名校的輔導需求。1980年代後期,學習塾衝上了3萬家大臺。
上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批判性的認可階段
1990年前後,日本經歷了資產市場的空前繁榮以及其後的泡沫破裂,而美國透過IT革命等科技創新,重現經濟活力。這一時期,科技創新必需的好奇心、想象力等素質的重要性以及應試教育的弊端,被反思中的日本社會廣泛討論和接受。文部省也在中小學加速推進了前階段已嘗試的“寬鬆教育”,進一步削減授課時間、減輕授課難度。
在寬鬆教育政策指導下,中小學校增強了學生的文體活動和社會體驗,對學科教育明顯放鬆。結果,學習塾在維持中小學生基礎學力中的存在感愈加突出。至1990年代末,日本學習塾猛升到近5萬家!
面對學習塾作用日益鞏固的現實,1999年,日本文部省在“生涯學習審議會”的答辯中,首次承認學習塾是日本社會教育“不可忽視的存在”。但是文部省繼續保持批判的姿態,提出:在重視學生生存能力的教育理念下,應該促進學習塾轉變功能。
本世紀初至今:與學習塾開展合作階段
進入本世紀後,日本各界對過度的寬鬆教育帶來中小學生基礎學力下降表達了嚴重擔憂。2002年,文部省宣佈:將“紮實的學力”和“生存能力”並列為教育政策理念的兩大重點,這一教育新政與學習塾相當親和。此後,文部省不但不再批判學習塾,而且鼓勵體制內中小學甚至大學和學習塾開展合作。不少地方已出現政府支援的“公費支援型學習塾”。
在文部省政策出現戲劇性變化的同時,受價值觀多元化的影響,日本家長的育娃行為也日趨理性。據文部省調查,2017年小學生各•學年的平均通塾率為46%,初中生61%,高中生27%。大多人的頻度是每週1-2次、每次1-2小時。同時,在充分的市場競爭下,學習塾的收費合理,人均通塾費用為每月2萬日元左右(約1200人民幣),大多家庭能夠承受。
受人口減少的影響,本階段日本的學習塾停止了增長步伐,數量穩定在5萬家上下。但是,其在日本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社會形象有顯著改善。
從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過去半個世紀中,日本的教培行業經歷了輿論的批判、政府的抑制等考驗。能有今天,市場需求的支撐、政府政策的調整、行業和家長的自律缺一不可,其發展過程值得中國深入研究。
(作者系日本亞洲成長研究所副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