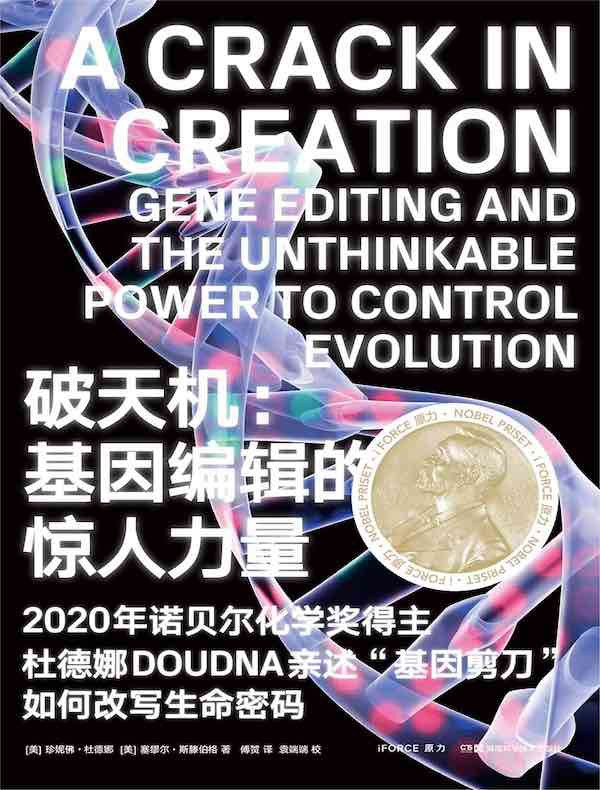蘇婉/文
在中國,基因檢測技術的商品化已經極大地拉近了人們對基因科學的認知。這種認知不再只是停留在《生物》課本中的克隆羊多莉和雜交水稻,如今,普通人只需要向基因技術公司寄去一份口水樣本,就能夠解鎖一項新的自體認知許可權,在極微觀的基因層面上重新認識自己。
想象一下,如果檢測報告顯示,某個位點的基因與長期折磨你的慢性失眠極度相關,此時你可以獲得一個替換掉這個基因的機會,無需開刀手術,可能只需一劑注射,你會選擇從根本上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嗎?
基因自由的開端
從基因科學的角度上說,生命是一套資訊。在現代人類出現的10多萬年來,這套資訊的組成和表達一直被兩種不可左右的強大力量所塑造:隨機突變和自然選擇。自從2001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以來,科學家已經精確鑑定出4000多個會導致遺傳病的突變位點。今天,科學家已經完全有能力與這兩種自然之力對抗,透過強大的生物技術工具來修飾活細胞裡的DNA,不僅能夠改造地球上所有物種的遺傳密碼,還能改造人類自己及其後代的基因,從而實現某種意義上的逆“天”改“命”。
《破天機:基因編輯的驚人力量》(A Crack in Creation :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介紹的正是這些工具中最尖端的成果,CRISPR技術(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palindromicrepeats,“規律間隔成簇短迴文重複序列”,簡稱為“CRISPR”)。2020年,兩名傑出的生物化學家,珍妮佛·杜德娜與埃瑪紐埃勒·沙爾龐捷,憑藉CRISPR-Cas9基因剪刀為基因組編輯領域做出的變革性貢獻,共獲諾貝爾化學獎。 她們也是首次同時獲得諾獎的女性科學家。《破天機》正是由珍妮佛·杜德娜和她的學生塞繆爾·斯滕伯格在2016年共同完成的科普讀物,他們面向大眾,將CRISPR複雜的技術原理、發展歷程、倫理難題,以故事的方式展現給讀者,他們的初衷是為了促進科學界與公眾領域的溝通。《眾病之王》的作者、普利策獎得住悉達多·穆克吉曾評價,“如果你想理解生命的未來,請閱讀本書。”
CRISPR-Cas9改編自細菌中天然存在的基因組編輯系統。細菌能夠從入侵的病毒中捕獲DNA片段,並利用它們來建立被稱為CRISPR陣列的DNA片段,使細菌能夠“記住”這些病毒的特徵。如果病毒再次發動攻擊,CRISPR陣列就會產生RNA片段,同時,Cas9或類似的酶能切割病毒DNA,使其“毒性”失效。這項發現啟發了生物化學家利用類似的原理,從細菌中分離出的Cas9蛋白質,並構建出特定RNA幫助Cas9精確鎖定DNA序列,切開雙鏈。其中,RNA的功能就像GPS,精確制導,Cas9是火力系統,實施最後打擊,從而實現對基因的增加、替換或敲除。
CRISPR之所以意義非凡,是因為它能夠更快、更經濟、更有效地實現基因組編輯,這種堪稱飛躍性的進步,不僅能夠普惠科學界的各項相關研究,同時更為基因遺傳病、癌症、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癒帶來希望。CRISPR技術可以用於治療的疾病清淡越來越長:軟骨發育不全症、阿茲海默症、肌萎縮側索硬化、糖尿病等,理論上所有跟突變或者DNA缺陷有關的病理現象,CRISPR技術都可以對任何相關的DNA序列進行精確定位並修復,把缺陷基因替換成健康版本。
不過,CRISPR也並不是萬能且完美的。對心臟病等受到環境因素等外部作用較大的疾病,基因編輯的作用可能不大。並且,如同所有藥物一樣,CRISPR也會有脫靶效應,就像化療在殺死癌細胞時也會殺死健康細胞。脫靶效應如果未能及時發現將會非常危險,因為細胞會不斷增殖複製,不可逆轉地導致整個生物體的災難。
CRISPR技術的諾貝爾獎雖然只頒發給了兩名主要的科學家,但這項成就的取得則是透過跨學科間切實的交流和合作完成的。就像眾人一起拼拼圖,每個人的工作都要依賴前人的工作,並貢獻自己找到的那塊拼圖。CRISPR技術的關鍵進展得益於不同學科間的知識流動與成果共享。杜德娜並不是CRISPR的首位發現者,事實上,她第一次聽說CRISPR是在2006年,一位地質微生物學家跟她共享了這個資訊。
十多年間,CRISPR研究報告之所以能從寥寥無幾的幾篇迅速進入井噴期,也是得益於成果的共享。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可以透過非營利組織愛得基因(Addgene)獲取含有CRISPR的質粒,而每個科學家也都貢獻出自己構建出的CRISPR質粒,每份質粒不到100美元,2015年時就有80多個國家的科研人員從那裡獲得了60000份質粒。這不僅對於科學界來說是一個普惠規則,甚至也將CRISPR帶向民間對此感興趣的獨立研究人士,“CRISPR把基因編輯帶進千家萬戶,這注定會使這項曾經鮮為人知的技術變成很多人的嗜好或者技藝,就像自家釀製啤酒。”
從某種意義上,人類將憑藉CRISPR技術開啟基因自由之門。
作者: (美) 詹尼佛·A.杜德娜 /
(美) 塞繆爾·H·斯坦伯格
出版社: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譯者: 傅賀 / 袁端端(校)
出版年: 2020-12
成為造物主
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不斷地改造自然,但從未達到今天如此劇烈的程度,地質學家將這個時代命名為“人類世”。杜德娜在書中暢想,地球史的新紀元將被CRISPR開啟,更高產的糧食、更健康的牲畜、更有營養的食物,“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會實現人類自史前時代就有的夢想:讓大自然屈服於人類的意志。”
有了CRISPR技術,人類可以強烈地干預自然秩序。
杜德娜本人完全沒有料到在,從2012年她發表論文之後的短短几年內,這種暢想就幾乎接近了科幻小說中的圖景。基因工程師已經透過改變參與控制肌肉形成的基因,製造出了施瓦辛格版小獵犬,透過抑制豬身體內對生長激素起反應的基因製造出迷你豬,或者更好吃的山羊和更像猛獁的亞洲象。我們可以復甦滅絕動物,也可以滅絕現有的物種,比如在非洲傳染瘧疾的蚊子。
某位昆蟲學家曾說,“如果我們明天就徹底清除了蚊子,生態系統不過會打個嗝兒,然後生活還會繼續。”然而即使生態系統有著自動適應的能力。我們就能對自然生命體基因進行任意改造嗎?出於何種原因進行改造?誰擁有改造的權利?在美國,這是一個包括科學家、立法者、醫藥企業、政府監管機構、NGO組織、基因致病患者及其家屬進行多方博弈的過程。
對於科學技術的應用,最棘手的衝突總是發生在價值觀層面。在這個博弈過程中,支持者認為人類因為懼怕風險,已經太久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進步。美國民間的“生物駭客”(biohacker)認為科技應該是能由普通人共享的,他們甚至認為改造自己的基因應該如換髮型、下載app一樣便利和自由。反對者則擔心基因工程應用結果的不確定性將導致不可預測的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社會治理等層面的問題。更有人擔心這將是生物武器的開端。
紀錄片《物競人擇》(Unnatural Selection)中記錄了一個價值觀碰撞的典型案例。一名美國科學家計劃協助紐西蘭政府,用以CRISPR為中心的基因驅動(gene drive),在紐西蘭的某個毛利人社群消滅導致多種鳥類瀕臨滅絕的老鼠等入侵性捕食者。鳥類的滅絕將對社群的生態產生毀滅性影響,但這是一種更加激進的基因工程,因為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驅動新基因在大自然中散播並引起環環相扣的鏈式反應,它的實施必須徵得社群居民的同意。
執行這項任務的生態學家認為,人類早就為生態環境帶來了不可逆的負面影響,以人為的方式對人為的影響進行消除,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時,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同樣要與其他物種進行競爭。但是在一神教教義中,生命存在皆有神意。上帝不會憑空創造兩個物種,人也沒有權利帶走一個。在毛利人的萬物有靈信仰中也有相似的邏輯,每個物種都有靈魂,靈魂與其他居民平等,沿襲祖先與自然相處的智慧,自然之力神聖不可侵犯。以自然的勉干擾性為終極目的,還是以人類的健康福祉為目的,在有神論的國度並不會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最終,這項計劃沒有被執行。
食品方面,CRISPR也不得不面對類似於轉基因作物所遇到的爭議。與傳統的育種方法(自然突變、誘發突變和雜交)相比,CRISPR技術使得科學家可以更加精確、快捷地操作基因組,培育出抗細菌感染的大米,天然抗蟲的玉米、大豆、土豆,不會褐變或過早腐敗的蘑菇。杜德娜本人擔心這些作物會遭遇轉基因食物一樣的抵制。美國農業部對轉基因技術的定義是,“為了特殊用途而對動植物進行可遺傳的改良,無論是透過基因工程還是其他傳統方法。”杜德娜認為,按照這個定義,不僅CRISPR技術編輯過的農產品在其範圍,而且我們吃的幾乎所有食物,除了野生動植物,都屬於轉基因生物。
對此,她提出辯護,“人們好像總覺得轉基因生物不自然,甚至邪惡。事實上,我們吃的每一種食物幾乎都被人為改造過,比如選育種子時用過隨機誘變。因此‘自然’與‘不自然’並沒有截然清楚的區分。中子輻射創造出紅葡萄柚,秋水仙素誘發了無籽西瓜,蘋果園里長滿了基因型完全一致的蘋果——現代農業的這些現象都不是自然出現的,但我們大多數人都在毫無怨言地攝入這些食物。”
胚胎編輯中的難題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科學家提醒我們,對於一項即將應用在人身上的技術,需要擔憂的永遠是最壞情況,而不是最好的情況。截止到2021年,在鐮狀細胞病、先天性黑蒙及癌症等涉及體細胞的臨床實驗中,CRISPR技術都表現出巨大潛力,人們會自然聯想到,治療絕症可以,最佳化基因可以嗎?讓基因缺陷者成為健康的普通人可以,讓普通人成為擁有完美外表、最強大腦的超人,可以嗎?
這個界限劃在了編輯生殖細胞系,也就是能夠成長為人的胚胎的倫理爭議上。首先,最低限度也是最緊迫的,對於不幸攜帶特定遺傳突變的人來說,不能生育下一代,或檢測出後代具有患病的極大可能,那麼可以透過體外編輯受精卵中的基因,從而讓這些人實現生育健康後代的權利嗎?但是,如果將胚胎視為初始形態的人,他們是否被剝奪了知情權和選擇權?
對此,杜德娜本人的想法也經歷了一個轉變。她在2015年第一次聽說已經有科學家把CRISPR技術用於編輯人類胚胎(雖然是不能成活的“三體胚胎”)時感到“反胃”,後續短短一年中,經過與法學、哲學、公共政策制定者等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的專家進行交流後,她的看法改變了。
杜德娜說,“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我認為並不存在禁止生殖細胞系編輯的理由;我還認為,父母有權利使用CRISPR來生出更健康的孩子,只要這個過程是安全的,而且不偏袒少數群體。”同時從安全性的角度講,如果在胚胎植入前剔除脫靶突變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那麼就沒有理由對CRISPR技術提出明顯高於其他醫學或生物手段更苛刻的要求。
大自然不是一個工程師,而更像一個水平不穩定的修補匠,它的粗心大意對於那些因為基因突變而患病的人來說顯得無比殘忍。大自然沒有能夠跟上環境變化來最佳化我們的基因組成,相反,處處都有不適應演化的突變,無數的生物體因此受損。人類違背自然的意願左右演化程序,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於一個真正患有遺傳病的人來說,剝奪他爭取不再痛苦的權利才是有違倫理的。
杜德娜呼籲社會尊重每個人決定自己基因的命運的權利。基因編輯胚胎本質上是一種優生學的實踐。不必惶恐,產前進行超聲檢查,孕中進補充維生素、戒菸戒酒,一切旨在生出健康寶寶的措施其實都符合這個定義。
但是,人們也擔心這將為基因最佳化開了口子。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政治想象就是一個基因不平等的反烏托邦社會。如果走向一種商業化的基因自由,那麼越富有和掌握越多權力的人是否會擁有特權,將後代改造為明顯比普通人具有基因優勢的人?這種自由是否會鞏固不平等,或者製造出新的不平等?
書中說道,中國會是基因編輯研究的沃土。我們已經率先開展諸多國外無法開展的實驗。的確,我們幾乎沒有太多宗教上的門檻。然而,道德和法律起到了相似的作用。人們或許已經淡忘了2019年初賀建奎事件。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團隊正是使用CRISPR技術修改了雙胞胎的胚胎基因來獲得對HIV病毒的免疫力。他們最終被判處非法行醫罪。杜德娜曾在紀錄片中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賀建奎團隊的斥責,她認為這種改造沒有進行過臨床試驗,甚至都沒有在動物身上實驗過,不應該如此草率地應用在人體,而且還是胚胎。
所有革命性的科學技術都同時具有兩個方向上的巨大潛能。倫理規範與進步主義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張力。進入現代以來,人們對科技進步的神話開始充滿懷疑。
基因編輯技術似乎預示著另一種賽博格的未來形態。相較於人工智慧技術,它可能會更加激進地改造人類的自然屬性。人工智慧改造的是外部世界的形態,但這種改造要依託於肉身之外的VR眼鏡,它仍舊是一個可以取戴的工具。但基因技術不僅將深嵌於人類的細胞中不可逆轉,而且將世代相傳。
然而就像杜德娜所呼籲的,科學界與公共輿論界應該建立更有建設性的、更加開放的對話,讓人們真正關心這些重大的科學進展,並在理性理解的基礎上,參與到討論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