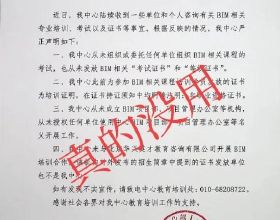趙豐(左一)、周暘(右一)等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法門寺出土絲綢。受訪者供圖
這是河南省滎陽市汪溝遺址出土的炭化絲織品。新華社資料片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區域性上檢測到的紡織物痕跡。新華社資料片
20世紀50年代錢山漾遺址出土的家蠶絲綢片。新華社資料片
2014年“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但在一錘定音之前,有國家提出異議。中國國家文物局就此要求考古界拿出“絲綢起源於中國”的實物證據
其實,百年來的田野考古已獲得多次實證,但方法主要是觀察。如何在炭化、灰化、泥化、礦化的遺蹟遺物中,找到絲綢的痕跡?這便需要科技的力量。“尋絲之旅”就是要於無形處覓絲蹤,這也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
大約5500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稱作中原的地方,一個村落裡,一個孩子夭折了。按照慣例,人們在小身體外包上一層絲羅,放進一隻尖底陶瓶,再在上面倒扣上一隻陶罐,形成一具小小的甕棺,然後讓他入土為安。
——這個村落和墓地後來成了遺址,於2013年出土,人們稱它為“汪溝遺址”。
又到了大約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稱作成都平原的地方,一座城市裡,人們在西南角挖了大坑,放進金器、青銅器、陶器、玉器和絲綢,可能還放了一把火,然後填平。
——這個城市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遺址,有的祭祀坑裡有厚厚的灰燼。
再到8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被後人稱作南宋的皇朝治下,一艘木質商船從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港口泉州揚帆啟航。它是福建制造的“福船”,尖底、窄頭、寬尾,其船體是多重板結構,分有多個水密隔艙,抗風強,吃水深,據說能裝七八十萬斤的貨物。它滿載著瓷器、鐵器和絲綢,寄託著船東貨主的財富夢想,不料沉沒在珠江口與雷州半島之間的南海海域。
——這艘沉船後來入評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編為“南海一號”。
古棺、古城、古船,三個故事中都出現了同樣的元素:絲綢。但是,在古蹟重見天日的時候,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土蝕、火焚或水浸,早已使絲綢化為烏有,讓人無法想象曾經的光澤、柔順和絲滑。而多年來,一批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尋絲之旅”,就是要於無形處覓絲蹤。
絲之證
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的100年間,田野考古已經獲得“絲綢起源於中國”的多次實證
2014年6月,第38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行,這個會議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遺產大會”。在這屆大會上,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但是在一錘定音之前,有國家的代表提出了異議。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趙豐回憶說:“他們說本國的絲綢比中國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蠶(柞蠶、蓖麻蠶等)吐的絲,而不是家蠶(桑蠶)。全球公認的蠶桑絲綢業的起源就是中國,像‘養蠶業’在英語裡就稱作‘sericulture’。其中,‘seri’就源於古希臘古羅馬對中國的稱呼‘Seres(絲之國)’。而‘culture’一詞是要有人的作用,才能稱為‘culture’,野生的、採集的,都不能算作‘culture’。”
本來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還是要重視。凱旋後,國家文物局就要求考古界拿出絲綢起源於中國的確實證據。而在2010年,國家文物局就依託中國絲綢博物館,成立了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這個任務自然也落到了基地身上。
事實上,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的100年間,田野考古已經獲得“絲綢起源於中國”的多次實證:
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帶隊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考古學人首次獨立帶隊在中國進行的考古發掘。他們意外地發現了一枚形如花生殼的黑褐色物體。後經辨認,它居然是被割掉一半後剩下的“半個蠶繭”。“半個蠶繭”現藏於臺北故宮,它所屬年代學界仍有爭議,一般認為已有6000—5500年的歷史,是人類利用蠶繭的實證。
1934年,學者慎微之在家鄉浙江湖州的錢山漾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原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錢山漾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綢片、絲帶、絲線,其中的綢片和絲帶被確認為人工飼養的家蠶絲織物,距今有4400—4200年的歷史。這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
1981—1988年,鄭州市文物部門對滎陽青臺遺址進行了6次發掘,在數個甕棺中發現了灰白色的炭化絲織物,距今已經有5500年的歷史。這與“半個蠶繭”一樣,也是黃河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
而就在去年,同樣在山西夏縣,考古工作者對師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又找到了距今6000年的石雕蠶蛹。
“田野考古找到了眾多絲綢起源的實證,鑑定的方法主要是觀察。”趙豐說,棉、毛、麻、絲是人類使用最久的四種天然纖維。在史前時期,棉不太可能傳到中國,毛主要在邊疆使用而不在內地,而區別麻和絲就要看它們留下的印痕:用顯微鏡放大來看,從縱向看,麻留下的印痕粗糙,絲留下的印痕光滑;從截面看,麻的截面是散亂的,絲的截面則是一個三角形,而且,“家蠶絲的截面是鈍角三角形,野蠶絲的則是銳角三角形”。
但是,尋絲的時間追溯越久,遺蹟遺物完整儲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那些炭化、灰化、泥化、礦化的遺蹟遺物中,還能不能找到絲綢的痕跡?這就更需要科技的力量。
絲之痕
2017年,在汪溝遺址的兩具甕棺中,從土樣裡檢測出了絲蛋白的訊號,由此一錘定音——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絲綢實物
氫、碳、氮、氧,四種元素的原子,按照不同的分子結構,結合成18種氨基酸。18種氨基酸再按照一定的序列,連線成肽鏈。肽鏈再經過β摺疊、α螺旋……形成了絲蛋白,絲蛋白外再裹上一層絲膠——蠶絲的本質就是一種天然高分子蛋白類化合物,而蠶就像是一座有生命的小小的生物反應器。
桑蠶——春的蘊藉,終究難以抵擋世間千年的風霜。古往今來,無數的絲綢經歷了從絲蛋白、肽鏈、氨基酸再到更簡單的元素的降解過程。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絲蛋白的降解產物中找到它曾經的痕跡。
“其實這項工作我們在2009年就開始了,當時是為了尋膠。”趙豐的同事、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暘娓娓道來。
當時,南京長幹寺地宮出土了一批北宋紡織品,有的運用了印金工藝,即將金泥與明膠調和,在絲綢上描畫。但是過了1000年,這批紡織品都吸飽了水分,膠質已經流失,如何證明絲織品在描金過程中用過膠?
中國絲綢博物館等機構的科研人員想到過多種方法。做元素分析,膠質已經流失;做質譜分析,文物上汙染物太多,分析出的噪音太多。後來,他們想到了免疫法。這個方法曾被美國蓋蒂研究所用於古埃及壁畫上,找到了古埃及人在顏料中使用蛋清的痕跡。
免疫學的原理每天都在人類和動物身上發生,並被人們有效運用。細菌、病毒等有機物質進入血液中,導致血清產生抗體。這些導致抗體產生的有機物質則被稱作抗原。從血液中檢測出傳染病的抗體,是醫生的重要技術,而我們注射疫苗後,體內也會產生相應抗體。
透過免疫法,研究人員在這批宋代紡織物上找到了膠的痕跡。能找到“膠之痕”,同樣的辦法也能找到“絲之痕”。隨後,中國絲綢博物館等機構開始了名為“基於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的研發。研究人員找到絲蛋白中的特徵片段,以這種分子標誌物在兔子身上製備抗體。抗體和抗原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這種抗體的任務就是去史前遺址尋找抗原,也就是絲綢的分子標誌物。
2016年,免疫法技術在“南海一號”的一個船艙裡找到了絲蛋白的訊號。船艙原被淤泥塞滿,大家以為是個空艙,但是就是這個空艙裡的發現消除了“海絲無絲”的困惑——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千帆百舸,當然裝載著絲綢。
2017年,這項技術又在汪溝遺址的兩具甕棺中,從土樣裡檢測出了絲蛋白的訊號。研究人員先用顯微鏡觀察土樣,看到了紡織品痕跡,再用土樣做免疫學檢測,由此一錘定音——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絲綢實物。
2021年3月,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要專案工作進展會議在成都召開,現場揭曉三星堆遺址重大考古發現。其中一點,就是多個祭祀坑裡都找著了絲綢痕跡。在一件青銅器的表面,免疫法找到了曾經附著的絲綢,顯微鏡也看出了絲綢的結構——這是有抑菌效果的銅離子立功了。而在四號坑的灰燼中,免疫法同樣找到了強烈的絲蛋白訊號。
幾經改進,這一技術的核心部件,是一支形如驗孕棒的試紙。周暘說,如果絲蛋白的訊號過於微弱,她們還可以採用電化學的方法,即用電能將訊號予以放大,敏感程度達到皮克級。皮克,也就是1萬億分之一克。
“抗體陽性”,在醫院的報告單上,這樣的結果或好或壞。而在絲綢考古現場,它只代表著一個令人興奮的結果:無論年代如何久遠,遺物如何衰朽,其間一定有過絲綢。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用今天的蠶絲蛋白製成的抗體,能夠高度靈敏地檢測出5000年前相對應的抗原,也就是說,5000年前的蠶絲蛋白和現在的並無二致,先民在5000年前飼養的桑蠶,繁衍至今。周暘說,這與西南大學等單位之前對桑蠶基因組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絲之魅
“尋絲”,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絲綢不但是商品,也是硬通貨,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
2015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絲綢博物館聯合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尋找中國絲綢之源”專案,分別在滎陽青臺、汪溝和鞏義雙槐樹等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展開工作。目前,相關研究還在繼續。周暘說,他們希望找到最早的繅絲作坊,還會在長江流域“尋絲”。
今年8月底,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在杭州舉行了一次成果鑑定會。專家認為,中國絲綢博物館等單位完成的“考古現場紡織品(絲、毛)文物免疫檢測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專案成果,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最近,周暘等人的團隊又在美國化學會(ACS)主辦的全球分析化學頂尖期刊《分析化學(Analytical Chemistry)》發表了相關論文。
“研究的競爭有三個層面,第一層是比拼誰的資料庫更完備,第二層是比拼誰的裝置更先進,第三層是比拼誰的理念更出色。”回顧免疫法技術的研發,周暘表示,“尋絲”是她所喜歡的第三層比拼。
但是,這還不是驅動他們“尋絲”的全部動力。最為本真的動力,或許可以從她的另一個問題看出端倪:“我們有沒有想過,在史前時間,蠶可能是一種害蟲?”
確實,在遠古時代,野蠶食用桑葉,可能會導致桑葚減產,而桑葚至今仍是人們喜食的一種水果,在過去的荒年還可充飢。
“野蠶是非常‘高冷’的動物,喜歡獨處,但是家蠶可以扎堆。野蠶碰到雨天,會躲到樹葉下面,家蠶毫無自我防護能力,要靠人類保護。野蠶蛾可以飛到很遠去找配偶,家蠶蛾飛行能力很差。”周暘告訴記者,對桑蠶基因組的研究發現,與野蠶相比,家蠶有354個基因位點發生了變化。“人們為什麼要馴化蠶?只是希望它的繭能從花生米般大小,變成現在這麼大這麼厚嗎?”
對此,趙豐認為,先民關注蠶,馴化蠶,生產絲綢,很可能是出於原始崇拜。“蠶作繭自縛,又破繭成蛾,讓他們感到很神奇,希望透過馴養蠶,找到生命復活或者靈魂昇天的力量。所以一些新石器文化遺址裡會有蠶形器、蛾(蝶)形器。他們用絲綢包裹屍體或重器,也是希望逝者在安葬後能像蠶破繭而出一樣,死而復生,或者靈魂昇天。”
“這種原始崇拜的思想在上古時期保持了很久,但是在戰國以後,中國生產力大大發展,人們更趨理性,絲綢的實用性更受到認可,並且成為區別階層的服飾符號,最終形成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文化。”趙豐說。
“絲”,在甲骨文裡是兩束蠶絲的象形。翻開《現代漢語詞典》,“糹”部首收入的漢字數量大概在200個左右,很多字在造字之初的古義,我們已經淡忘了,比如“純”就是蠶絲,“緒”是繅絲時繭子的頭,“組”是用絲繩系起的祖先牌位……
而這些漢字如今的含義,除卻實用價值,又多有一種宏大氣象。我們稱讚傑出人物可以經天緯地,描述國家昌盛是一統江山,把禮義廉恥稱作國之四維,認為社會執行需要有綱紀準繩……可以說,蠶、絲乃至於紡織,已經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烙印。
“從絲綢的起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古老理想,也可以看出古老的農耕文明對於團結協作的需求。”周暘說,“尋絲”,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
在“尋絲”歷程中,他們曾在漢武帝茂陵陪葬墓出土的兵器上找到了絲綢,周暘為此很激動。我們知道,漢武帝依靠霍去病這枚“少年戰神”,打通河西走廊,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絲綢是中國外交的原動力。”趙豐說,西方人對絲綢的渴求,知道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生產絲綢的國家,才有了絲綢從東往西傳播的動力,最終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而古代歐洲、西亞、中亞的文化元素,也會沿著絲路向東傳播。在絲綢之路上,絲綢不但是商品,也是硬通貨,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
“我們今天如何弘揚絲路文化?談絲路就不能離開絲綢,因為絲綢是絲綢之路的原動力。”這是趙豐多年以來一直持有的觀點。
“尋絲”的意義,也同樣在此。(記者 馮源)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