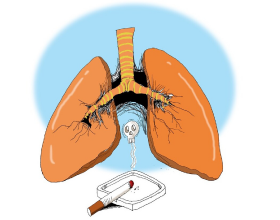下午,我坐著皮划艇,悄無聲息地潛入湖心島蘆葦叢,近距離觀察一群疣鼻天鵝。
青寶和豆蔻已在清晨被一對紅狐夫妻獵殺,用金黃草絲編織的窩巢裡,靜靜躺臥著四枚擺成“口”字形的天鵝蛋。
成年天鵝們從青寶和豆蔻的窩巢前經過時,沒有任何一隻停下來看看這四枚可憐的天鵝蛋。疣鼻天鵝社會沒有撫養遺孤的習俗。成年天鵝一旦發生意外,留下的雛天鵝,別的天鵝家庭是不會接納的。雛天鵝無人照料,只能自生自滅。許多鳥都是這樣,親鳥遇難,鳥卵隨之滅亡。
我正準備將望遠鏡從這四枚天鵝蛋上移開,突然,我看見雌天鵝紅珊瑚從漾濞湖登上島,搖搖擺擺地朝蘆葦叢走去。途經青寶和豆蔻的窩巢時,我感覺到紅珊瑚的神情有點異樣。它搖搖擺擺地走到青寶和豆蔻的窩巢前,細長的脖子彎成S狀,溫柔地端詳躺在草絲間的四枚天鵝蛋,神情異常專注,似乎在諦聽著什麼。我相信,它一定是聽到了蛋殼裡雛天鵝在蠕動和踢蹬。它扁扁的喙輕輕翕動,噝呀噝呀發出輕柔的呢喃聲。
我心裡一陣激動,莫不是它想扮演親鳥角色,替代青寶和豆蔻孵化這四枚天鵝蛋?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紅珊瑚剛剛經歷喪子之痛,無處安放的母愛需要有一個出口。果然,紅珊瑚在青寶和豆蔻的窩巢前徘徊,欲進未進,一會兒側轉臉做沉思狀,一會兒頸窩貼在蛋殼上摩挲著,顯得遲疑不決的樣子。
別猶豫,勇敢跨進窩巢去,你就成了這四枚天鵝蛋的媽媽,你的喪子之痛就能得到慰藉,它們也將獲得新生,何樂而不為?我在心裡唸叨,期待著事情真能朝我想象的方向發展。如果紅珊瑚真的跨進窩巢孵化青寶和豆蔻遺留的蛋,應該說不只是雙贏了,還多了一贏,我的野外考察贏得了重大突破。迄今為止,所有文獻均無疣鼻天鵝抱養孤兒蛋的記載,鳥類專家普遍認為,雌疣鼻天鵝不具備母愛延伸和擴充套件的能力,不會為不幸的同類撫養遺孤,更不可能去為非親生卵抱窩。看來紅珊瑚要幫我修改這條結論了。
我正在暗自高興,事情突然有了變化,紅珊瑚停止了把頸窩貼在蛋殼上摩挲的動作,若有所思地搖搖腦袋,然後搖搖擺擺離開青寶和豆蔻的窩巢,跑出一百多米遠,蹲坐在蘆葦葉上,專心致志地悶頭啄理胸脯上的羽毛。我觀察了十來分鐘,紅珊瑚再沒朝青寶和豆蔻的窩巢張望一眼,它似乎已忘了那四枚正焦急等待母愛的天鵝蛋。
我有點失望。看來,“雌疣鼻天鵝不具備母愛延伸和擴充套件的能力”這條結論不是那麼容易推翻的。
兩隻大嘴烏鴉像兩片黑色的樹葉,在蘆葦叢上空盤旋了幾圈,呱呱叫著降落到青寶和豆蔻的窩巢裡。失去成年天鵝看護的天鵝蛋,就是空巢天鵝蛋。
我注意到,擔任哨兵的兩隻雌天鵝,明明看見兩隻大嘴烏鴉闖入棲息地並降落到天鵝窩巢裡,卻並沒飛到空中發出報警的訊號,似乎是默認了這種入侵。
在常規放射治療中,脊髓、腦幹、腮腺、顳頜關節、面板等組織器官,都會在高劑量射線下暴露,受到影響後,發生面板損傷、口乾症等副反應,對患者的治療安全造成影響。相關研究表明,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療的過程中,如果常規分割DT在10 Gy以上,在照射野當中的唾液腺,將會降低50%左右的分泌;如果分割DT在45 Gy以上,唾液腺將會受到不可逆的損傷。而採用調強放射治療技術,利用了多野共面照射的方式,同時與動態多葉光柵相配合,能夠最佳化調節正常組織受到的照射劑量,進而使放射治療產生的毒副反應發生率最大限度的降低。
夕陽懸掛在半空,疣鼻天鵝們正陸續歸巢。雖已是黃昏,但天色依然亮堂,疣鼻天鵝們不可能沒發現正要糟蹋四枚天鵝蛋的兩隻大嘴烏鴉。大嘴烏鴉雖然屬於食腐兇禽,但與成年疣鼻天鵝相比,個頭小,力氣也小,只要有一隻成年疣鼻天鵝跳出來干預,就一定能將兩隻大嘴烏鴉從青寶和豆蔻的窩巢裡趕走。可即使左鄰右舍有許多成年天鵝,它們明明都看見這兩隻討厭的大嘴烏鴉了,卻裝作沒看見似的。
大嘴烏鴉不愧是竊蛋高手,尖利的喙猛力一戳,就在一枚天鵝蛋上啄出一個洞來,土黃色彎鉤狀的喙伸進洞去,啄出一條黏稠的蛋清,吱溜吸進肚去。
在疣鼻天鵝的棲息地,大嘴烏鴉展開了一場肆無忌憚的虐殺。
左鄰右舍的天鵝們的反應各不相同。有一家鄰居,天鵝夫妻均把頭扭到一邊去,不看這血腥場面;另有一家鄰居,雄天鵝守護在窩巢前,脖子伸得筆直,警覺地望著,擺出一副格鬥狀,卻遲遲不見它衝過去制止這場殘暴的虐殺。許多天鵝目睹了大嘴烏鴉正在殘害雛天鵝,卻沒有一隻站出來干涉。
我知道,左鄰右舍的天鵝之所以聽憑兩隻大嘴烏鴉啄食天鵝蛋,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青寶和豆蔻留下的四枚天鵝蛋,雖然還有兩三天就要出殼了,但由於親鳥雙亡,終止了孵化,小生命就在蛋殼裡畫上了句號。
終於,兩隻大嘴烏鴉將兩枚天鵝蛋收拾乾淨了。窩巢裡還剩下兩枚天鵝蛋。一隻大嘴烏鴉的爪子撥弄著一枚天鵝蛋,另一隻大嘴烏鴉用喙摩挲著另一枚天鵝蛋殼,準備進行第二輪虐殺。
“噝噝,噝噝——”許多天鵝豎直脖子發出嘶啞的嗚叫聲,整個湖心島充滿悲鳴聲。
我很想拔出防身用的獵槍,射殺這兩隻渾蛋烏鴉。可我也只是想想而已。我是動物學家,不能將人類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硬套在野生動物身上,我更不能憑自己的好惡去幹涉和改變野生動物的命運軌跡。我是一個旁觀者,只能客觀地觀察野生動物。
剩下的兩枚天鵝蛋,靜靜地躺在用草絲編織的窩巢裡,它們沒有任何防衛能力,只能聽任命運的擺佈。
突然,一隻疣鼻天鵝貼著湖面快速飛行,須臾之間已飛臨青寶和豆蔻的窩巢上空,撲向正欲啄食天鵝蛋的兩隻大嘴烏鴉。兩隻大嘴烏鴉沒有思想準備,嚇了一大跳,立即蹬腿起飛。
大嘴烏鴉身體輕盈、起飛迅疾,但它們還是慢了半拍,其中一隻烏鴉被那隻飛撞過來的疣鼻天鵝啄中尾羽,好不容易從疣鼻天鵝扁扁的喙裡掙脫出來,天空中卻也飄舞著三兩根黑色的烏鴉羽毛。
兩隻大嘴烏鴉嚇破了膽,驚慌地叫著,向梅里雪山山麓飛去。那隻疣鼻天鵝不依不饒,奮起直追,直到把兩隻大嘴烏鴉趕出漾濞湖上空,這才飛回湖心島。
當那隻勇敢的疣鼻天鵝降落到青寶和豆蔻的窩巢旁,我調整焦距,仔細打量,驚訝地發現,這隻勇敢地向兩隻大嘴烏鴉飛撞過去的疣鼻天鵝,潔白的羽毛光鮮亮麗,那塊鮮紅的瘤狀突起十分耀眼,哦,那不就是我曾經關注的雌天鵝紅珊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