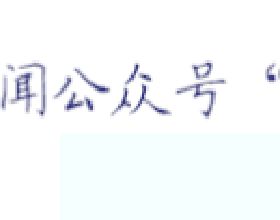前幾日去了一趟三溪水庫遊玩,聽說那裡的風景獨好,尤其兩岸的山石更是奇特。去過的人,對那裡的山石都讚不絕口,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就是山勢險峻,怪石嶙峋。
我去的那天天氣格外的寒冷,站在水庫大壩上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壩上的冷風比別的地方要來得凜冽許多。那是因為水庫兩岸山勢險峻,使得庫區成為一個巨大的風口,寒冷的氣流源源不斷地從上游峽谷推送過來。
我手足並用小心翼翼的從大壩上爬下河堤,沿著傾斜的河床往峽谷深處緩慢的走去。環目四顧時,發現兩岸不但山勢險峻,而且從山頂到山腳都散落著許多巨大的類似圓球形花崗岩。彷彿是有一個巨人正在山頂上將一塊塊巨石,順著陡峭的山勢往下推。
那些石塊有的已滾落到了庫區裡,有的一半倚靠在高高的峭壁上一半還懸空著,有的剛滾到半山腰……突然有人按了停止的按鈕,滾動的巨石隨即成為靜止的畫面。那些巨石就以各種不同的姿勢卡在山石上,好像隨時要繼續滾落下來,讓人看了不禁心生恐懼。
令人驚歎的是,那些欲滾落的巨石在那樣陡峭的山勢上,竟然還能維持千萬年而紋絲不動,不得不叫人讚歎大自然的神奇與奧妙。
由於冬季乾旱的緣故,使得河床大面積地露出灰白色的沙土。沙土上凌亂地散落著許多殘敗的乾枯樹枝,我踩著沙土和枯枝前行,每一步斷去的枯枝都用沙啞的聲音唱著一首低沉的輓歌,在寒風吹襲下的庫區上空飛舞飄蕩,如泣如訴。
遠遠地看見兩根看似門柱的石板,筆直地立在沙土上,走近才發現原來是一座墳墓的殘垣斷壁。在立著的石板的斜坡上方,還躺著一個缺了一半的墓碑。雖然不完整,但還是可以看出那墓碑上刻寫著十幾個人的名字,是祖孫三代的家族墓地。在右下角的地方還寫著立碑的時間:民國十六年。距今已將近一個世紀了。
長子,長媳,次子,次媳,長孫,長媳…這些名字使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一座巨大的三合院。推開三合院的大門,看到一位頭戴氈帽的老頭正拿著一個水壺,悠閒地吹著口哨給庭院中的花草澆水。穿過庭院的花草來到廳堂,一位頭髮發白的中年婦人,正抱著一個滿月不久的小孫子,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逗著孩子玩,時不時的傳來稚嫩的嘻嘻聲。左右兩側的東廂房和西廂房裡,分別是一對遲遲未起的夫妻。
這是一個多麼溫馨和諧的大家族日常畫面,然而時光流轉,住在那三合院裡的人,一個一個卻成為了刻寫在這個墓碑上的名字,直到有一天那最後來到世間的小孫子,也走進了這個墓碑。一個家族活生生的十幾口人,竟彷彿只是一剎那就從一座溫暖的三合院住進了這個冰冷的墳墓。這樣想時,不禁讓人心生感傷,哀嘆時空的冷漠無常。
我想住在這座墓地裡的先人,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在他們死後的31年,他們的墓地竟成為了水庫庫底的一角,使得他們常年處於水流之下。如果他們泉下有知,不知要哀嘆到何等程度。由於我不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因而不確定他們的遺骸是否已經搬離。
聽一位長輩說,在未建水庫前,水庫的河床上,甚至是庫區到處都是墳墓。後來因為要建水庫,大部分的墳墓都搬走了,但還有一些無人認領的就成了無主墓。我想這座還留著墓碑的是不是就是一座無主墓,因為在整個河床上,我就發現一個相對還算完整的墓地。可是那麼大的一個家族,真的就沒有一個後人嗎?這樣想時,又平添了幾分感傷。
那兩根依然堅強立在沙土上的石條,以及靜靜躺在枯枝上的墓碑,在寒風中向每一個遊客訴說著一個家族從興盛到滅亡的無常。在嚴寒的冬日清晨,看著這座殘缺的墓碑,特別能給人一種悲涼的感覺。那種悲涼,比從水庫峽谷深處吹過來的徹骨寒風還要令人顫抖。
從水庫歸來,使我心中沉悶,特別能感受到生命的短暫和時空的無常。即令一個人生前是多麼的富有,有多麼顯赫的身份,百年之後也是一樣毫無差別地成為這些荒冢裡的孤魂。
到水庫去遊玩本是為了散心,沒想到卻因為那些殘缺的墳墓令我心生感傷,想來真是一件掃興的事。因而建議還未去三溪水庫的人,不要下河床,沿著大壩往兩岸的高處行走即可。那樣更適合欣賞到兩岸的風景,也能免於因為那些荒冢而影響到遊玩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