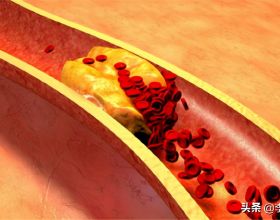那天參加完媒體見面會,我回家覺得格外困,有那種集中精力學習完的疲憊感。
因為陳曉楠老師和季業老師的聊天特別有意思,非常真誠而且準確。我節選了一些在這裡,希望你也會喜歡。
這就是一場殘酷的青春電影
問:本季節目中誰最讓您觸動?
陳曉楠:是《獄外來信》的陳泗翰。
我採了他兩次,我還記得我採訪到最後的時候,他不是學吉他嗎,我說那你唱一個吧,他還特別不好意思。他說,那我要唱《這世界那麼多人》,因為我覺得那首歌每一句都在說我。
就在我們播出之後,那首歌的詞作者也看到了,還發了一個朋友圈,他說,沒想到我當年寫的詞在某一時刻陪伴了這樣一位年輕人,就是那種很神奇的連線。
(採訪陳泗翰之前)我突然就看到了那些信,那是在一個文字的報道里面有一些照片,信中的字特別稚嫩,但特別整齊。就看到了好多時間線,比如他剛剛入獄的時候說,現在離你離開已經有幾天了;然後慢慢你就會看到說我們中考過後誰誰誰考得好;後面又看到我們現在上高中了,我告訴你個秘密,我現在體重都多少多少了……
這個時間線特別清晰,也特別殘酷。從信中你分明看到這些年輕人的命運被分成兩條軌道往前走。我當時一下就覺得這個角度特別打動我,就是那種頭皮發麻的直覺。
(陳泗翰把自己挖得那麼透)他的語言是詩意的和散文化的,以及精準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和這些孩子們之間情誼的破碎感,那種遺憾,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他都說出來了。
他回憶起他們一起出遊,夕陽灑在他們的身上,金邊灑在每一個人的肩膀上,那種文學性的畫面,會讓我有好像毛孔張開的感覺。他出來之後和同學有依稀的聯絡,他仍然有一種又想向前又退後的情緒。我覺得特別複雜,五味雜陳的這種東西,就是事實和命運的真相吧。
我還記得我採訪出來給季老師他們打電話,我很激動,我說這就是一場殘酷的青春電影。
這期節目最主要是感謝陳泗翰。我會有一種很珍貴的撿了一顆珍珠的感覺。在職業生涯當中,你覺得這樣的故事撿一顆是一顆,哪怕它就在今天截止,我都覺得是沒有什麼遺憾的。我覺得美好而純粹的東西里面,即便它有殘酷的一面,但是當它被這樣書寫出來,它一定是能觸動到別人的,我特別愛這期節目。
最大的挑戰在於選題
問:在最新一季中,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季業:我覺得是選題上的。
就是外界對這種選題的需求,我發現大環境在慢慢變化,觀眾在看節目的時候,他更需要尋求一種力量。
我們過去做節目,老說三維度:故事性、相關性、話題性,覺得符合三維度就可以。我們追求一種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表現風格,對人物不做任何道德評判。我們前幾季也會涉及到一些相對有點爭議和灰色(的話題),或者是沒有那麼好判斷他是好人或壞人的人物。就會有一些觀眾說,這個東西很高階,但是他的出路是什麼?
我後來就在想,在這樣一個艱難的時代,給大家提供一點內心的力量也是很好的。所以這一季我會給三個維度之上再加一個維度:有力量的人性。就是故事性、相關性、話題性再加上有力量的人性。我希望我們呈現的人物都能夠體現出人性的真善美,來讓大家看到一些看似無解的社會話題、人生話題當中的一些出路。
節目最終呈現是遺憾的藝術
問:我們知道曉楠姐一期的採訪時長有5、6小時,可節目最後呈現只有半個多小時,我們作為觀眾常常覺得不夠看。
陳曉楠:這個其實特別矛盾,因為我們已經是戰戰兢兢地來佔大家30分鐘到40分鐘的時間了。
我們作為創作者當然希望你能看到全本了,因為我們每次最大的糾結,最難的就是把它剪短。比如從5個小時到1個小時,難度是遠遠小於,幾倍地小於,從5個小時到半個小時的難度。就從割出來1小時到半個小時之間就得吵無數架。
因為你選哪不選哪,你可能就把他組建成了另外一個人了,就是後期二度創作的時候。這就是採訪普通人最難的地方。明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明星他已經有前提了,你是瞭解他的,他現在說的所有的話都是附加分,他不是從一開始讓你瞭解這個人。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塑造一個普通人,你有可能會把他塑造成另一個人。我們就會小心再小心,也會非常的痛苦和糾結。
但是我們現在就必須得接受遺憾。我剛入行的時候,經常夜裡給季老師打電話:“我說的那句話,他說的那句話很好,為什麼沒有用?”他那會就直接懟我:“用不了,就擱不進去了。”
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擱不進去了,那麼必須得有取捨。它是個遺憾的藝術。
(主持人陳曉楠)
採訪普通人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問:節目中有一些主題比較敏感,是如何說服被訪者的呢?
季業:我覺得跟嘉賓的聯絡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急功近利。
我們嘉賓要跟曉楠聊5、6個小時,還要深入地聊自己的人生和情感。他帶著利益訴求來的話,採訪一定會失敗的。我們就是耐心地跟他交朋友。
(節目總監製季業)
陳曉楠:季老師說得特別對,採訪普通人和採訪名人不一樣。採訪明星團隊是一種工作關係,但你無法拿自己的工作關係去跟普通人建立信任,你需要跟他建立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並不瞭解你的工作,接受採訪也不是他的任務。
展示悲慘不是我們的初衷
問:有幾期節目都很容易讓觀眾大哭,想請問一下,節目採訪過程中會不會也有進行不下去的時刻?
陳曉楠:我原來做《冷暖人生》的時候有個經驗,如果嘉賓始終在情緒極度悲傷的情況下,始終在哭的時候,是沒有辦法跟你好好講故事的。我知道螢幕上的人哭很容易帶動觀眾哭,但那是空的,哪怕你哭了,你並不會有所收穫、對他有更多的理解,你只是覺得很慘很可憐。
展示悲慘不是我們的初衷,雖然說展示悲慘會有無盡的選題去做。它一定要有背後的深度,背後站著一群人,和一群人共同的價值,也就是所謂的公共性,不是一個人的悲慘。
比如我們採訪喬任梁的父母就是因為看到這個話題的公共性,它是失獨的人及所有人都會面臨的問題:你如何面對分別和失去?活著的人怎樣有尊嚴地活下去?這是人類永恆的話題。
我們看到的是喬任梁父母的笑。他們在短影片裡最開始的正襟危坐,後來的那種活潑,還有迅速學到一些新鮮的語境,這種反差特別觸動人,你在裡面能找到力量。
(媒體見面會現場圖片來自主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