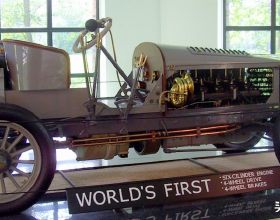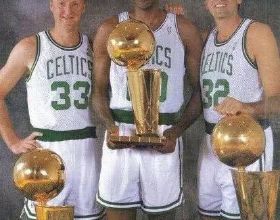我的老家位於翼城縣南關村,又名河底村,人民公社後合併為東關大隊,後改名為東關村。
村東有條河叫澮河,河水從東北順東關和南關村東奔流而下,途經曲沃侯馬,一路向西南併入黃河。河東是田地,河西是人們住的村子。村裡人藉助澮河水世世代代以種菜為生。南關村和東關村西面有道城牆,高約80米,城南有道坡,又名南門坡,坡頭有城門。城東亦如此。城牆之上是老城,又名城內村,城南是縣中學。
1938年,日本兵侵略翼城縣,一箇中隊的日本兵進駐縣中學。爺爺是南關村的村付長,馬芳庭是東關村的村付長(馬芳庭於1957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受到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接見)。爺爺講,當時老屋住著一個班12個日本兵,每天監視著爺爺和馬芳庭給住在縣中學的日本兵送菜。爺爺和馬芳庭二人每天一人一擔,一擔約180斤。爺爺和馬芳庭二人身高一米八幾,大塊頭,每人挑180斤在坡下歇一下,然後一口氣挑上南門坡。
送菜時間長了,爺爺和馬芳庭便起了“賊心”,在往廚房卸菜的時候,如果沒日本兵在,兩個筐裡剩點菜,把另兩個筐扣在上面,一人挑筐,一人去結算菜錢。
這樣時間長了,爺爺說,怕日本兵發現。後來,二人想了一個辦法,在每個筐的下面,各綁一條一拃長的麻繩。過秤時兩人一人抬一頭,用腳踩住繩子用勁往起抬,一次能多稱個十斤八斤的,過的斤數太多了也不敢,如果出了格,日本人會發現的。怕什麼來什麼,一次,在過秤的時候,日本兵司務長髮現了端倪,嘴裡咕嚕著:“你的,良心大大地壞了地幹活!”說著從廚房裡拎了一把菜刀出來。
爺爺和馬芳庭二人怔在原地。爺爺講,當時心想,命怕是難保了,不如跑吧。還沒等爺爺和馬芳庭抬腳,日本司務長拎著刀彎下腰把繩子割了,然後揮舞著菜刀在爺爺和馬芳庭面前晃了晃,厲害道:“你們今後地、小心地幹活!”
三伯是個瞎子,二伯是獨眼。爺爺講,三伯和二伯是1938年的時候,日本飛機轟炸從太行山下來的抗日軍隊,一個炸彈落在了河東的菜地裡。飛機過後,二伯、三伯還有父親(當時二伯16歲,三伯13歲,父親5歲)三人在菜地裡摳炮彈殼,三伯摳了個啞彈,用炮彈殼去摳。不成想,“轟!”的一聲,只見三伯滿臉和雙手流滿了血,蹬在地上哇哇大哭,原來三伯的兩個眼珠被炸出了眼外,雙手食指和中指也不知去向;二伯左眼珠也被炸了出來,雙手捂著左眼哭,父親嚇得直哆嗦……
自我記事起,二伯和三伯及大娘一家就住在河東的東崖上,又名十八彎。十八彎,自然是拐了18道彎,而路是在崖坡上開拓的二尺寬的羊腸小道。崖上無水,全憑人下到十八彎下的河裡挑,一來回六里多地。二伯瞎了一隻眼,可以下地幹活,為了生計,二伯學了板胡,隨戲班有婚喪嫁娶的掙個小錢貼補家用。而三伯是瞎子,手又是殘廢,自然是下不了地,幹不了活,唯一能做的就是拄著柺杖走路。
走路幹什麼呢?三伯只能下河挑水,自此,三伯就挑起了挑水的重任。平時一個人空手上十八彎都嚇得心驚肉跳,累得腿抽筋,別說一個瞎子挑水,可想難度要多大。而三伯下到河裡去挑水,走上二里地不歇一下,一口氣能挑回十八彎的家中。中途三伯不敢放下桶歇,生怕水桶落地,地面不平,水桶倒了就白忙活了!
後來三伯還有更驚奇的事。大娘走後,三伯為了生計,從沒見過縫紉機是啥樣的,竟能修理。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非常驚訝三怕的悟性和能耐。
後來才知道,三伯不知怎麼找到五交化一個修縫紉機的師傅去學習了,那個師傅可憐他,就手把手地教。其實很簡單,就是皮帶鬆了緊一下,齒輪沒油了加一下。但這些活,村裡的莊稼漢是幹不了的。
想不到三伯一個瞎子,也竟靠著這樣的能耐,自食其力地生存下來了。
郭學德(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