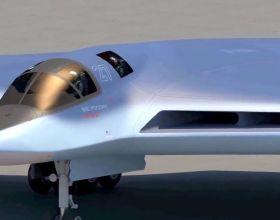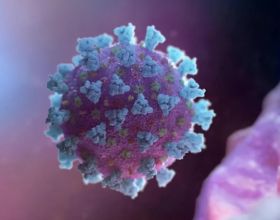起始,是柳煙夜色中的一座拱橋,橋是硃紅色的,被細微的波浪拍打;然後,是建築體內部的一個門洞,迷宮的分岔,出口或入口;再然後,是垂掛著的一簾黑色的幕布,天鵝絨質地,密實厚重,簾幕背後隱約已有人聲……
幾張畫,指引一般,帶領人款步進入一個視覺劇場,那裡有舞臺,有故事,有青春的肢體,沉默的聲響,片段的寓言——有景有情,活色生香。

夜宵 Nocturne,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80 x 190 cm

欲前行(二)Forward movingII ink and colors on paper 192-5 x98cm_2014
如臨 upcoming ink on paper 191x97 2015
12月20日,黃丹個展“入境”在三遠當代藝術開幕。這是黃丹在三遠當代藝術的第三次個展。在這個展覽中,黃丹持續嘗試在實踐中提取感覺與情緒的更多可能性。重疊的水墨,重拙的色與宣紙摩擦,產生喚起觸覺感知的視覺體驗。層層堆疊的墨暈底色既有水的親近,又有堅緻酸硬的石頭觸感,畫面被放置於曖昧的感知下,將觀者引入一個無論他們是否在觀賞都會自行發生的戲劇事件。
“‘入境’是一個比較寬泛,或者比較中性的詞。它並非具體內容,而像是一個邀請動作,一個趨向性的指引。它也是一個把個人私密的想法開啟的動詞。”黃丹告訴南都記者。
黃丹的前兩次個展,無論是2019年的“生”還是2020年的“觀其生”,其主題都與“生”有關。“生不是指活著,而是‘不熟’,一種還沒有開始衰亡,剛剛興起的狀態。我感興趣的實際上是跟生命有關係的東西。”黃丹說。
對人的關注,對人作為主體感知到的世界的關注,貫穿於她創作的始終。“入境”也不例外。黃丹把一切繪畫還原為人和人身邊的事物。她畫人,也畫花卉和動物,“在我來看它們就是跟我有關係的一切,跟生命有關係的一切,跟我們的選擇有關係的一切。”
展廳現場
展廳內闢出許多小的空間,每個空間有相對獨立的調性和主題,形成一種層次豐富的多聲部效果。
“比如有個隔間掛的是黑白的《弗裡達》;展廳的過道對面掛著兩張臀部,是比較私密的,卻正好放在一個通道里;最裡面那個有斑駁陽光的廳,掛的是虎,蘭花,梅花,還有鵝,實際上是我的一種堅定而私密的表達。慢慢地從外到內,給予人們一種途徑,進入到藝術家的思想空間裡。”黃丹說。
上臺 On Stage,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05 x 248 cm

漸深 Into the Deep,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47 x 276 cm

皎 Bright, 2021, 紙本水墨 Ink on paper, 64 x 96 cm
在一些作品中,黃丹對舞臺身體活動中所囊括的動態加以描繪,用有選擇的設色與物—景—事件之間的修辭流轉創造了一種極具力量的敘事。在畫作《上臺》、《漸深》和《遙》裡,芭蕾舞演員們被置於黑色背景中的聚光燈下,她們表情一致,動作誇張而簡勁,硃紅、白、黑、灰的對比極具視覺張力。在《皎》這樣的畫作裡,人物被定格在一個瞬間,某種情節在暗裡湧動,緊繃的情緒之弦已拉滿,但畫面卻是細緻而寧靜的。
不見身相 The Absence of Bodily Forms,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97 x 133

桃 Peachy,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53 x 77 cm
而在《不見身相》和《桃》這類作品中,黃丹專注於描繪身體的區域性,比如腿,或者臀。匍匐的軀體在休憩,或者幾雙跳芭蕾舞的腿在竊竊私語。由於聚焦片段和區域性,這樣的作品更有銳度,也更引人遐思。正如黃丹自言:“它的視覺衝擊力來源於它沒有說清楚一件事情,不清楚的時候反而你覺得內涵更廣。”
澤 Marsh, 2021, 紙本設色 Ink and color on paper, 75 x 145 cm
黃丹給人的印象是聰明、幹練、勤奮,總是在追求一種富有邏輯的、有力量的表達。多年以來,她一直孜孜矻矻地尋找自己的水墨語言,不管是具象的、複雜的、敘事性的,還是單純的、抽象的、區域性微觀的,這讓她的畫作呈現出靈活多樣的面貌。
她告訴南都記者:“很多人從傳統裡挖一塊東西變成自己的,這就夠用了。但我不要,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對於傳統來說,我想的是我能對它做什麼,而不是它能為我做什麼。這是藝術家本來應有的出發點。”
南都專訪藝術家黃丹
我選擇不同的方式,只是想找到更有力量的表達
南都:我以前在各種展覽裡經常看到的是你的人物作品,這次發現你除了畫人物,也畫花卉、動物等等。我知道你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能講講你的師承嗎?
黃丹:我讀的是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人物專業。我們分得特別細,比如我是在國畫系的人物工作室,還有山水工作室,花鳥工作室。我的研究生老師是韓國榛,比較傳統的畫家。
韓老師最好的一點是讓我自由,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因為他只畫傳統,但他看過很多現代的東西 ,他告訴我那些東西有多好,雖然我當時未必能理解。我是慢慢地吸收進去的。他把他身上的保守、墨守成規等問題,一覽無餘地告訴我。這作為教育者來說太難得了。所以我對他特別感激。他是在思想上,用他的經驗,用他的教學,去推動我的進步。
我的畫所有人都覺得特別像田黎明老師。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田老師都身體力行地給予了我們好多實際的指引。客觀地說,在造型上,在對水墨的不停的推動和探討上,我實際上是接田老師的衣缽接得最好的。我們一直想為水墨做點什麼,而不是把傳統擺在嘴上。實際上田老師在他的年代是很創新的。他是盧沉教授的研究生,並不算是很正統的美院人,他的那些東西剛開始也是被人詬病和質疑的。他所有的畫都是在探求造型,他自己有個定義叫“文化造型”,帶有文化意味的造型,這是田老師對我最大的啟發。
南都:你覺得你在田老師的基礎上又讓水墨往什麼方向拓進了一步?
黃丹:往內心表達上。是往內的,不是往外。田老師已經開始往內了。外界經常看到的是他的高士圖,或者陽光少女,但他真正好的東西是寫生。他的寫生在造型上的高度可以媲美弗洛伊德,嚴謹,而且有自己的處理。弗洛伊德的寫生很重,肥碩,大,力量,體塊感。田老師實際上也有,但是他用很淡的,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去體現那種重的造型。
展廳現場
我很懷念那時候。我們寫生不是課上的,都是他想畫,然後我們一起加課。下午這個光線下,在美院的工作室,對著模特畫人體。我們一起去畫,他說,你們不要看我,因為他的特點太強的,淡淡的粉色一鋪,很容易一學就學到皮毛。他的寫生不是陳丹青那種,很較勁,很寫實的,他是一種更有高度的寫生,他在寫生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實現了一種突破。我們真的很賺,有這樣一個人天天在你面前畫。
從技術上來說,美院所有老師的技術都臻於完美。但造型到底是什麼,是寫實,還是有自己的處理?田老師比盧沉老師更走向自己,我又比田老師更走向自己。因為我還是女性,我還佔了這個“便宜”,我可以更敏感,也可以更“自私”,我不用考慮別人,我也不用考慮學院教學。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我更具備這個優勢,在他的成果上再往前走。
我為什麼是得他衣缽最完整的?我想可能是因為追求一樣。比如說像馬,一般都會畫很飄逸的鬃毛,但我要的是整體,我要的是文化意味,它代表的是東方。我並不想侷限於傳統或者東方,可問題是它是我們天生具備的,是融入在血脈裡的。比如我畫石頭也是,這個石頭不是具體的,它也沒有任何肌理,你可能看不出它是石頭,但我畫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意味。
南都:我發現在你的畫裡線條被弱化掉了,這是刻意為之的嗎?
黃丹:你看田老師有一種圈墨法,他的光斑需要“圈墨”來實現。圈墨就是沒有勾線。
西方很多經典的東西都是講究線的,實際上油畫之下全是線條,只是作品是線上條之上去完成,加了肌理,加了明暗,線是一切的基礎。從吳道子以來,線條是國畫的一個很大的特徵,但線並不是國畫的全部。而且回到材料上來說,既然有水有墨,它的厚重感、它的滋潤程度,是它與西方繪畫最大的區別。
你看米芾的米氏雲山,那是好多點組成的。你看黑乎乎的宋畫,它真的只是線嗎?它整個畫面呈現出來是一個面。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黑漆漆的一大片,它是不是用好多點,好多短的線,好多染,最後形成整座山的感覺。幾根線是不足以表達的。為什麼有小溪流淌?小溪不是流出來的,是透過別的黑擠出來的白。
展廳現場
實際上,不管國畫還是油畫,它一定是符合藝術品的本質的要求的。第一是表達,第二才是你用的材料呈現出來的藝術家個人的特點。比如米芾跟四王是很不一樣的。藝術首先是表達,然後是每個人的特點,到最後才是材料、國籍、東方西方。
南都:你總是畫區域性的人體,但是很奇怪,它會產生一種視覺衝擊力,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黃丹:第一,是因為畫不完整的少。完整的話是敘事。比如我告訴你,我去了公園,這件事就完了。我沒有把情緒告訴你,比如我很開心,我很難過,我很難忘。敘事是具體的,但它也意味著限定。但是半截的東西,或者稱之為軀幹或者區域性,它反倒是更宏觀。它的視覺衝擊力來源於它沒有說清楚一件事情,不清楚的時候反而你覺得內涵更廣。這個時候每個人的理解就不一樣。我在路上,你可以理解為我去任何一個地方。但是我告訴你我去公園,那麼我只在公園。
展廳現場
片段性、不完整敘事,吸引觀眾自己去補充內容。你看到它的時候你會加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情感,因為它有空間。
當然畫區域性的人少,它帶有新鮮感。同時,畫微觀一點、區域性一點的東西,它更抽象。越抽象的東西包含越多。我還是想用最少的東西說最多的話。
南都:這是個好聰明的想法,其他藝術家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黃丹:其實還是因為他們不想做難的事情。我想做難的事情。所以我不停地嘗試。我也畫完整的,也畫有超強的敘事性的,但我不滿足於那個。我要找到更適合我表達,可能我甚至還來一段說唱,我選擇不同的方式,只是想達到更有力量的表達。
所以不管是具象的、複雜的、敘事性的,還是單純的、抽象的、東西少的、區域性微觀的,我只是在裡面選擇最能表達的。我比別人可能更勇敢一些,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我可以不停地換方式,我不用怕有的方式別人用過,還有一點,我比別人可能還要勤奮一些,所以不停地在嘗試。我沒有停在某個地方。
南都: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找到屬於自己的這種獨特風格的?
黃丹:一直在找。也沒有說現在就找到了。但是我確實一開始就不喜歡臨摹。我性格非常強,凡是臨摹課我都跳過不上。還好我們人物臨摹課很少。古時候人物畫很少的,《潑墨仙人》怎麼臨?沒法臨的。
我太想創造一種自己的方式了。我以前寫過一篇自己的文章《談何叛逆,我只是想建立》。我並沒有想叛什麼,我沒有反傳統,我是帶有水墨的情感的,帶有東方的人本質的東西的,我想用一種非常含蓄、隱性的方式來表現力量。只要是藝術品就是需要力量的,否則你溫和地告訴別人你要說什麼,你還不如不說。方式可以不同,但我一定要非常明確地把主張告訴他。我想建立自己的水墨語言,這種語言只要是建立在我對人的熱愛之上的,它就是符合所有規律的。
展廳現場
我覺得我可能有點像畢加索的性格。我們都有藍色時期,玫瑰色時期,都有技術性能夠達到,但是又放棄不走的一條路。他後來開始立體,開始慢慢地解構,慢慢地抽象,實際上也是我的一個方向。
南都:所以你現在也是從寫實在走向抽象的過程中?
黃丹:不存在純寫實。中國畫裡沒有寫實的概念。田老師的作品其實已經很抽象,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概括。它沒有完全變形。
比如蒙德里安畫的格子就是純抽象,但他中間有個階段,他畫灰色的樹,還有樹的形,但呈一些小格子狀,我覺得我正處於這個階段。比如羅斯科,最後就剩下三個色塊,我也很喜歡。但是我很難走到那一步。他的力量感太大了,那是跟生死有關的東西。但是如何從具象慢慢過渡到那一步?對我來講是個課題。我只能每一次稍微抽象一些。
展廳現場
實際上我前兩次的展覽是偏抽象的。今年的展覽反而更回到具象。為什麼?因為人物這一塊我的抽象程度還沒有達到物的那種自由度。人的束縛很多,它有主題性,還有敘事性,我好難把這些東西去掉。
還有就是我有一些想表達的東西,一定要在這個時候表達出來。我得去做。有時候我明知道不一定朝這條路走,但我不做會不甘心。而且我不怕辛苦,我做出來以後可以跳過它,我可以越過它。在我看來沒有彎路,永遠是一條直路,只是有時候我在某個點停滯的時間長一些。
南都:另一方面,市場是不是也更接受這種有敘事感的作品?你覺得藝術家要考慮市場嗎?
黃丹:肯定的。市場一定是比較接受明確的、敘事的東西。純抽象的新水墨會被歸到水墨實驗,但那又不是我喜歡的。
我會尊重市場,也會在意市場。但畫畫的時候,你不需要去考慮市場。不是藝術家自私,而是市場需要你去表達自己。市場給了你這樣一個權力。市場允許你,甚至要求你去做你自己。否則的話,你對藝術、對觀眾沒有貢獻。因為市場是對藝術整體的一個顯現,它在意的是藝術的多樣性,在意的是文化。
在我看來藝術是什麼?藝術需要我們每個人用自己的特點去推動一個大的規律,讓這個規律整個的面貌更豐富一些,更深一些。
為什麼我不想提傳統?因為很多人就是從傳統裡挖一塊東西變成自己的,這就夠用了。但我不要,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對於傳統來說,我想的是我能對它做什麼,而不是它能為我做什麼。這是藝術家本來應有的出發點。
展廳現場
南都:畫了這麼多年,怎麼保持對藝術這項事業熱情?
黃丹:還是因為我對其他東西不太感興趣。我會控制其他的愛好和慾望。實際上就是我沒有別的興趣。我覺得畫畫這件事情,我在付出的時候它也給我好多。經常有人問我,你怎麼堅持下來?為什麼要“堅持”呢?我得到了這麼多。
它不是名和利,我在畫畫的時候有一種滿足感,滿足於這個東西只有我能創造。我並不是一種創造者的姿態,而是我感嘆我創造了它,而這種東西只有我有。這種滿足感無與倫比。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