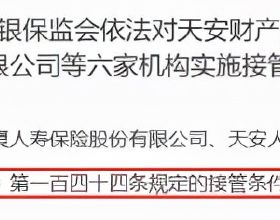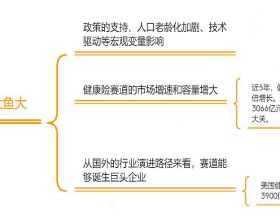德國新任外長貝爾伯克才剛上任三週,就因其外交理念而飽受批評。身為綠黨籍外長,貝爾伯克在多個場合強調“價值外交”的概念,還曾在向柏林左翼報刊《日報》表示,她將外交政策理解為“世界內政”,並且將中國稱作“制度性競爭對手”,引發對中德關係的擔憂。
對此,前德國國防部國務秘書弗裡德貝特·普呂格在德國保守政治文化雜誌《Cicero》上發表公開信,勸誡貝爾伯克應該吸取美國的教訓,不要進行道德十字軍討伐,應該意識到西方國家價值外交的侷限性。當然,作者對中國、烏克蘭等問題,依舊是基於西方價值觀做出的判斷。觀察者網翻譯此文,供讀者參考。
【翻譯/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親愛的部長貝爾伯克女士,
衷心祝賀您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您接手的是屬於最重要和最具成就感的一項任務,祝您諸事順利和持久成功。
請允許我就您宣揚的“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發表一些評論。自四十年前我在波恩大學完成博士論文以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我一直在思考和麵對“究竟何謂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這個問題。我的經驗歸納起來說就是:鑑於我們的歷史和根據我們的憲法,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是對的,但它不該成為道德上的自以為是和人權上的十字軍討伐。還有: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包括睿智的人權政策,但首先是確保和平。
懲罰奧地利
人權政治歷史始於1849年12月的美國參議院。為抗議奧地利軍隊鎮壓匈牙利革命,後來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劉易斯·卡斯(Lewis Cass)要求與奧地利斷交。對此,參議員約翰·帕克(John Parker)諷刺道:此事可得有始有終哦,“懲罰”奧地利之後,還得同樣鄙視(幫助奧地利的)俄羅斯或(並不善待愛爾蘭愛國者的)英國或(剝削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到頭來,你會與整個世界決裂。最後,參議員亨利·克萊(Henry Clay)就卡斯非要斷交這一問題指出,在某些情況下,派代表到維也納與奧地利人就匈牙利人的命運進行“閉門”談判其實更有幫助。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此後,人權政治貫穿了美國的外交。從伍德羅·威爾遜(“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約翰·肯尼迪(“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確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到人權號手吉米·卡特(“因為我們自己是自由的,因此我們永遠不能對自由在別處的命運無動於衷”),美國總統不斷要求推行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
民主輸出的失敗
然而,理想主義往往導致災難。隨著(1953)東柏林和(1956)匈牙利反共起義被鎮壓,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二戰後的政治解放言論歸於失敗。在美國“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無數次播報的影響下,最起碼當時匈牙利人是真的相信美國會來幫助他們的。越戰,作為美國在全球為“自由世界”掀起的反共高潮,展示了理想主義方式最終會導致什麼。1968年的美萊村大屠殺表明,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會以何種悲劇結果而告終。
40年之後,這一錯誤再次重演。美國智庫(譬如卡內基、蘭德公司等)和政客宣揚“大中東民主”(“Democracy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理念,以此來對可怕的“9.11”事件作出新保守主義式的反應。當時,我本人對此也很著迷。我至今還記得自己曾在2011年舉辦的一次哈佛會議上熱烈歡迎“阿拉伯之春”的到來。
我認為,阿拉伯世界的人們有權在伊斯蘭極端主義和集權體制之外走第三條路:自由民主。我至今都忘不了哈佛的卡爾·凱撒教授(Karl Kaiser)以及當時的德國社民黨外交政治家卡斯騰·福克特(Karsten Voigt)對此表現出來的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向傳統和價值觀完全不同的地區輸出民主會面臨失敗。
他們兩人是對的!無論在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還是阿富汗,除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等少數地區之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惡化了這些國家人民的處境。無數人傷亡、遭受酷刑和流離失所。2015年敘利亞人大規模逃亡歐洲或2021年西方士兵倉惶撤離喀布林,都再清楚不過地展示了善意和高尚的動機最終是如何適得其反的。
維護和平是最高目標
部長女士,請允許我基於歷史經驗以及我自身在過去的錯誤判斷,就價值觀外交、但並非自以為是的外交政策提出以下五個觀點:
1)維護和平是價值觀外交的當務之急
偉大的哈佛教授格雷厄·艾莉森將崛起的中國和“守成者”美國日趨嚴重的衝突與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不斷尖銳化的競爭進行了比較:當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堪比今日由臺灣空域引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從這個歷史比較中得出以下結論:中美之間必有一戰(destined for war)。基於這一危險,諸如不派官員到北京冬奧會等這類不斷火上澆油的做法是否明智?還是利用這場運動會展開廣泛的外交攻勢更迫切必要?
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首先應服務於維護和平。它不該一味用瀟灑和象徵性的言辭來橫加指責,而應該透過默默的外交來具體改善人們的處境。中國不久將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我們必須以理說服中國人,但我們不能“懲罰”,更不能“迫其就範”。重要的是利益平衡和外交解困。
那麼俄羅斯呢?我們有理由為俄羅斯挺進烏克蘭邊境感到擔憂,但是,我們難道除了威脅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嗎?難道我們不是更應該打破相互指責的惡性迴圈,並以新的建設性建議來取代有關新制裁的討論嗎?您提出的關於基輔和莫斯科應重新恢復直接會談的建議大方向是對的。
在這方面,是否應該考慮像延長烏克蘭天然氣過境協議那樣由歐盟出面調停?或者,是否可以考慮在氣候領域,如風能、太陽能、能源效率、造林、共同的氫能專案等,與俄羅斯進行廣泛的合作?在冷戰正酣的1970年,與蘇聯簽訂的天然氣管道交易至今都維護著歐洲的和平。氣候政策方面的廣泛和長期合作同樣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再說,這點也見諸於聯合執政協議中。誰閱讀過普京最近的一些講話,誰就很快能發現,俄方原則上也是有意合作的。
沒理由高高在上自以為是
親愛的貝爾伯克女士,您是否也認為我們對和平的認知太想當然了?或許因為我們中間只有少數人還記得那些轟炸之夜?而實際上,我們這裡以及世界上許多地區所擁有的和平正在受到嚴重威脅。核戰爭或許是最大的威脅,比氣候變化更具摧毀力!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區,核武裝到牙齒的國家相互對峙著。裁軍和軍備控制機制已經瓦解,新的更具殺傷力的武器正被髮明出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曾針對所有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說過一句名言:和平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和平則一切皆無可能。
2)不要進行道德十字軍討伐
我們可能經常認為別的文化傳統陌生、落後和值得批評。表達和推廣自己的信仰是允許的,有時甚至是必須的,但要警惕自己過度熱衷於道德優越感。其他的、有些甚至更古老的文明或有正統宗教信仰的國家不喜歡被管束或說教。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應維護歐洲文明的成就,但沒有理由表現出高人一等和自以為是。宗教異端裁判所、滅絕印第安人、販賣奴隸、殖民主義、迫害猶太人、在越南投放化學武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和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等,都還去之不遠,歷歷在目。我們自己經過數百年才實現人權,我們又有何權力要求其他文化立刻遵守西敏條例(Westminster Standards)?
3)認清我們自身的侷限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卡爾·馬克思)。德國伸出食指對世界上的新興國家進行說教究竟有多少收效?鑑於歐洲內部的爭論不休、經濟實力的下降趨勢和不斷顯現的軍事軟肋,人權指責在歐洲以外的世界裡除了被視為對內政的惡意干涉之外,並不能取得改變效應。
即使我們沒有次次都去幹涉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犯人權現象,也並不表示我們對其他人的命運無動於衷,而是出於對自己有限影響力的客觀認識。
4)價值觀之外還有合法的利益
德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有賴於成功的外貿。如果我們只向完美無瑕的西式民主國家出口,這將導致無數勞動崗位的丟失。機械,汽車和配件供應或化工,所有這些成就德國富裕和增長的關鍵領域,均嚴重依賴中國市場,譬如每兩輛大眾汽車中就有一輛是銷往中國的。我們必須在我們的人權信仰與生存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對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羅斯同樣如此。
譬如,2019年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在西門子和可耐福集團負責人的主持下在索契與普京交流,並非如一些德國批評者指稱的那樣是“恥辱會談”。雙方商談的更多是諸如急需能源和出口等符合雙方利益的共同經濟專案。即便“貿易促變”的希望經常落空,依然不能否認大型經濟專案有利於彼此合作和相互依賴的事實。它們起到建立信任和促進穩定的作用。

西門子和可耐福集團負責人的主持下在索契與普京交流。來源:urdu point
5)人權政治始於本國
我們在向其他國家因人權施壓之前,首先應該掃清歐洲門前的雪。譬如,匈牙利和波蘭的現政府正越來越遠離歐洲法制精神和條例。美國憲法之父們反對輸出人權,認為美國更應作為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屹立在那兒,成為別人的某種楷模。少一些佈道,更多透過榜樣的言行來成為世人矚目的人權燈塔。這才是維護和平之外另一個人權外交的基礎。
關於作者:

普呂格教授1955年生於德國漢諾威,1973年後在哥廷根大學和波恩大學攻讀政治學、法律和國民經濟專業,還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塞繆爾·亨廷頓。1982年在波恩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論文標題是《介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美國人權政治》(Amerikanische Menschenrechtspolitik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普呂格18歲加入基民盟,在黨內基層和下薩克森黨部均擔任過要職。1990年至2006年任德國聯邦議會議員,1999年至2005年任基民盟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2005年至2006年在第一屆默克爾政府中任聯邦國防部國務秘書(副部長),2006年至2011年任柏林市議會議員,並於2006年至2008年擔任柏林基民盟(CDU)議會黨團主席和反對黨領袖。
2010年10月退出政壇,從事教學工作,目前任教於波恩大學。曾在倫敦國王學院執掌能源和資源安全學院。2009年以來是賓克曼普呂格國際企業諮詢公司的合夥人。
此公開信2021年12月14日發表於德國保守政治文化雜誌《Cicero》。
來源|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科工頻道
講中國企業科技自強、科技向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