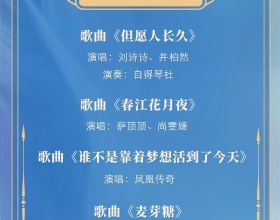老子有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意思是治理一個國家,必須像煎魚一樣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則一不留神就煎糊了。縱觀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的這一系列戶籍舉措,正好是老子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他的每一項政策都經過反覆推演,有設計,有試點,有鋪墊,有妥協,策略務實而有彈性,一步步走得十分紮實。從“戶貼”到“賦役黃冊”,從“一百一十戶裡甲”到“魚鱗圖冊”,從“糧長制”到“實習歷事”,層層推進,有條不紊。
朱元璋別的施政成敗姑且不說,至少在地方戶籍建設上,他表現出了一個成熟、理性、精明且極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
經常有人很奇怪,朱元璋在國初那麼折騰,為何國家沒怎麼亂?答案就在戶籍建設的細節中。
—————————————詳細解說的分割線—————————————————
自漢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戶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一個政權掌握的資料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治越穩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初始,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括閱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幹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則設計完備,資料儲存完整,能省不少事兒。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並;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運氣了。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做“諸色戶計”,以繁複而著稱。有按職業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採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戶、葡萄戶;還有按照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等等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但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明Excel和Access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複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十年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複的戶籍體系相對的,元代的戶籍管理卻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遊記第二章裡,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
雖然他是以讚賞的口氣來描述,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得多懶多糙,才會這麼幹啊!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多年。元末戰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吶,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複雜局面,只能摸著和尚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他在南直隸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做“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徵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閒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僱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衷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徵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 ——這是向民間徵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在第二年,朱元璋又宣佈:“須以原報抄籍為定,不得妄行變亂。”
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現在還是什麼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沒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儘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 “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貼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臺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訂了王府官制、五等勳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佈了一封聖旨,鄭重宣佈戶貼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它最早始見於南齊,從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裡時常可見,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封聖旨,在中國的皇家檔案裡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聖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驪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階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聖旨是這麼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徵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乃是脫胎於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釋出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後一道程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叫做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裡,大位次裡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臨戎錄》,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
說回正題。
朱元璋為啥要用這麼奇怪的白話文?不是因為朝中無人,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前後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人念,一直唸到六千多字,還沒進入正題。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這位皇帝態度倒真認真,罵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著念,唸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才聽見乾貨。
茹太素用最後五百字說了五件事,件件見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說:“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是忠臣,你的意見很重要,可你他媽的能不能說話簡潔點?” 後來朱元璋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大明律裡:“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
在國家級的政策檔案上使用大白話,也算是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
拋開文風不說,這份聖旨內容相當務實。裡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條分縷析,每一句都是乾貨,把戶貼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麼,戶貼制到底是幹什麼的?咱們不妨把整個執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當然是皇帝下發一道大白話聖旨到戶部,給政策定下基調。
第二步、戶部根據檔案精神,設計出一份標準戶籍格式尺寸,叫做戶貼式。
戶部規定:“戶貼”的用紙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邊緣還綴有一圈花卉裝飾。
這個尺寸,可不是隨便訂的。
早在晉代,朝廷製作戶籍時已有規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而是卷軸裝。每張紙之間左右粘連,形成一條長幅,因此寬度不限,只需要規定長度即可。
到了明代,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頁頁相疊,因此需要把長、寬都規定出來。將長度定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種從古吧。
看完尺寸,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塊。在最右邊,印製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聖旨,前面新增一句“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字樣。一來申明此乃皇命;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否則要充軍;三來提醒經手官員,如果他們違法徇私,也要處斬。
在中間部分,是戶帖主要內容,要寫明該戶的鄉貫、男子丁口、女子口、名歲、與戶主關係、戶種、事產、住址等資訊。
最左邊,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簽押,以便追溯責任。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籤起,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當然,這兩位的簽押都是提前印製好的,否則他們也甭幹別的事兒了——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會有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簽在後頭。
這是中央部門簽發部分。在戶貼背後沿邊還留有空白,以便地方執行官員簽下花押:從知縣、縣丞、司吏、典吏到書手、手辦、裡保一個都不能少。
調閱任何一份戶貼,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行小吏這一整條檔案流轉的路線。哪一環節出問題了,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
每一份戶貼,都要一式兩聯。首一聯叫做籍聯,次一聯叫做戶聯。前者交給官府留底,後者給百姓家裡留底。在籍、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要印有字號以作為堪合之用,還有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這樣一來,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偽造。
從一份戶貼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逐級簽字、騎縫用印、編號堪合、籍戶二聯,儘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僅此一點,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
第三步、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給官辦印坊,依照樣本批次印製,然後分發到各地州縣,並規定了繳還時間。
第四步、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後,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這個提調,是臨時差遣頭銜,和後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曉諭百姓,讓他們早做準備,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
接下來,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親自坐鎮監督,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分赴各地基層去執行落地。
第五步、衙門小吏和當地里正逐家去敲門送帖。百姓大多不識字,需要口頭申報,小吏當場填寫資料,並由熟悉內情的里正稽核、做保。三方確認無誤,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籍聯部分,帶回衙門,與其他籍聯彙總;剩下的戶聯部分,交還百姓自家留底,叫做戶帖。
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就是從戶聯這來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聯,在衙門彙總統計,要算明戶口、人口、丁口、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自己複製一份留底。這麼一層一層磨算,逐級彙總到戶部。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裡的,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總人口、總適齡壯丁總以及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
有了這份東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會變成透明起來。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的總數,如果願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
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麼?
老朱對於官僚一向不大放心,總怕有人居中舞弊徇私。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於白乾。
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的文書人員,分散到各地去稽核抽查,術語叫做“駁查”。用聖旨裡的話說:“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徵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
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相互包庇的機率不高。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那就發去充軍。
第八步、軍隊駁查完畢,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和戶部報告並讀。大功告成。
說了這麼多,那麼這個戶帖到底什麼樣子?
讓我們拿一份儲存至今的戶帖實物,看看都填寫了什麼吧。
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側,是朱元璋的大白話聖旨,佔了將近一半的紙幅。在聖旨結尾還有一行字:“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堪合戶貼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偽。
從中縫左側開始,進入正文:
一戶,林榮一。
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女子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事產:屋,一間一披。
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從這些資訊可以看出,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一家五口,一間房子幾畝田地,勉強餬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村裡。
再往左邊看,是兩行字:“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說明這份檔案是戶聯,給戶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邊,有一排殘字,只餘右半邊:“加字壹百玫拾號。” 這個是騎縫字號,另外一半字在籍聯上面,已被扯去交官。萬一起了糾紛,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騎縫字號能對齊,說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一共有六個。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還能看到一個“部”字。另外一個字是“戶”,留在了籍聯上。具體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聯捲起來,讓“戶”字和下一聯的“部”字恰好平齊,蓋上騎縫大印。如此操作,兩聯各留一半鈐記,功能和字號一樣,還兼具認證功能。
這樣一來,官府和民眾各執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來管理,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也可以憑此作為證據,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篡改的情況。
這份戶帖,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周詳了。
不過有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這個戶帖裡有兩個不太容易發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
大家不妨停在這裡,想上五分鐘,再繼續讀下去。
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麼?是徵收賦稅。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還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
稅賦依據,不止要看田地多寡,還取決於田地質量。
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鹼地,即使面積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產出大不相同;麥田和桑田,即使面積相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別。如果不加區別,只以面積來收稅,小則造成紛擾,大則激起民變。
早在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就注意到要考慮到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賦”。王安石變法時,有一項方田均稅法,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稅負各不相同。多佔良田者多繳,少佔貧田者少繳。
將田地分級,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減輕貧民負擔。
可在剛才那份戶帖裡我們可以看到,林榮一家裡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簡單地登記成:“自己民田地”。這塊土地種的什麼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戶帖裡一概沒寫,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
這讓朝廷以後怎麼收稅?
也許會有人指出: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你在戶貼裡當然看不到。
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裡面會將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標明,繪成圖形。因為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故而得名。它始見於宋代婺州,在元代開始流行於兩浙經濟發達地區,是國家釐定稅賦的重要參考。
但問題是,朝廷開始大規模修造魚鱗圖冊,是洪武十四年之後的事。在洪武三年、四年推廣戶貼的過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打算清查田地的意圖。
這太奇怪了,元末的狀況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賦無準”,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為什麼不摟草打兔子,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幹嘛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後才做?
其實,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重之處。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想!他做夢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賜,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泡爛賬,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像湯和、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飭,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
隱田藏匿得多,稅賦就交得少。稅賦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朱元璋當然希望儘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愁。
太缺人才了。
清點人口比較簡單,執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但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整的方形,經常會有圭、邪、箕、圓、宛、弧之類的田地形狀,執行人得精通方田之術,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
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互相包庇,執行人得足夠精明,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裡挖出隱田來。
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手裡暫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麼程度?那一次核田,只有事關稅賦命脈的浙西地區,朝廷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督查;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只能“分遣監生並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至於其他地區,中央連使者都派不出去,只能發一紙聖旨,讓各個地方自行“擇邑從事之賢者,新具圖籍”。
上頭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裡。好,你顧不過來,那我就慢慢拖唄。比如蘇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是在洪武二十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麼多田地,利益關係牽涉極深。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裡清丈土地,結果“緣以為厲民,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上下憂之, 遂不克竟”——楞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後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準不準另說,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各自賣個面子,相安無事。
這麼個複雜的地方,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連個水花都聽不見。
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說“父老鹹喜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賬不欺”,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
至於實際效果嘛,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名,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麼可能靠譜。
可見“竿尺有準”云云,也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你自己報上來,我給你寫下來,大家都別深究。
這還是在大明統治的核心地帶,至於外圍各地,更是鞭長莫及。
事實上,無論是技術上還是形勢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裡特意強調過:“國初定賦,止據一時一地之荒熱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
當然,朱元璋手裡還有軍隊,如果硬要強行清田,也未嘗不能。但一村一縣可以鎮壓,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天下初定,民心未附,這麼一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
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的彈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唄。
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貼大登記中,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這根高壓線。只讓百姓把手裡的田地面積寫清楚,官府做個賬面統計,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麼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也得有個參考吧?
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盛行,以產量來估田畝。割麥子的時候,三捻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則為一擔谷。拿著個經驗公式推算,肥田每畝收谷四擔,瘠田兩擔,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
這個經驗公式適用於江南地區,北方物候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叫折畝法: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叫做稅畝,好地一畝頂一稅畝,次一點的地,兩畝頂一稅畝,再次的地,三畝才折一畝。透過這種做法,儘量讓稅賦公平一點——後來到了明中後期,折畝法被髮揚光大,通行全國,不過那就是後話了。
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還是諸城的折畝法,都是折衷之舉。朝廷無法核田,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只好暫時採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
朱元璋退的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牴觸情緒會減輕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戶貼給推行下去。他甚至還主動下詔,鼓勵墾荒,說新開發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聽,好啊!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新田地還不用徵稅,那還不多幹點?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生產力迅速恢復。
至於戶貼,行吧,官府說什麼咱能填什麼,反正是免費的。
老百姓覺得自己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要更長遠。
他們不明白,戶貼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只要人鎖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未來朝廷可以徵稅的田地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旨宣佈“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 ——聽起來不錯,從十三年開始的墾荒土地可以不用交稅,但再仔細一想,洪武四年到十三年期間農民開墾的田地,可就得算進賦稅裡了。
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於此。
透過戶貼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朱元璋鍛煉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技術層面不存在問題。
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既緩解了基層情緒,又推行了政策,還鍛鍊了隊伍為以後埋下伏筆,可謂前後勾連,一舉數得。這般手段,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戶貼推行十週年——國家又一次捲土重來時,百姓們驚訝地發現,他們身負戶貼之枷,面對虎狼之吏,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
真應了那句話,稅收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裡的第二個問題。
林榮一的家庭地址,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注意這個“民”字,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型別,是“民戶”。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貼裡,我們還能看到“軍戶”、“匠戶”等分類。
等一等,匠戶、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職業戶制嗎?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原籍報抄”,但那不過是維穩的權益之計,怎麼洪武四年的新戶籍裡,還有這種鬼東西?
元代的這個職業戶制,是一種歷史大倒退。本來在宋代,因為經濟發展迅猛,戶口設計趨向於寬鬆流動。比如“客戶”是沒有常產的戶籍,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就可以“復造”戶籍,從“客戶”轉為有常產的“主戶”。
元代可不敢這麼幹,統治者最擔心的是統治被顛覆,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緊越好。職業戶制下的民眾,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不可變易。
放著宋的好東西不學,幹嘛學壞的?
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戶制,原因很複雜。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戶出身,牽涉複雜,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貿然廢除職業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明初百廢待興,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蒐集到的前朝舊檔,申明效力,讓職業戶各安其位——先穩住再說。
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性的,一來二去,職業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所制。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以衛所為單位,直接落地變成軍戶。閒時屯田自給,戰時赴戎。而軍人的子弟,世世代代也是軍人。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自誇說我朝不用徵兵,也不用徵餉,軍隊自給自足,不驚擾百姓分毫。
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軍戶”。
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塗。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歸戶部管,軍戶歸兵部,匠戶、灶戶歸工部。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但總算不像元代那麼奇葩。
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貼大登記中,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不分戶種,就地入籍。”
“不分戶種”是說無論民、軍還是匠戶,都要登記,沒有例外,這是全國一盤棋;“就地入籍”是說,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願意回去,也沒關係,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樣可以授田登記。
不過無論是權宜之計還是規劃衛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慾太強了。
這種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別適合維穩,而穩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在朱元璋心目裡,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呆在土地上,別到處溜達生事。
不光朱元璋這麼想,明清兩代對職業戶制,也頗多正面評價。比如萬曆年有一位戶部官員晏文輝讚譽說:“洪武舊本,如木之根,水之源,木有千條萬條,總出一根;水有千枝萬派,總出一源。任由千門萬戶,總處於軍匠民灶之一籍。” 清代的學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既有常業,有令世守之。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無非各事其事,童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
朱奇齡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來,職業就註定了,不會有別的想法,自然不會瞎折騰——此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官府也方便管理,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
換句話說,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朝廷並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
這個職業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產物,在穩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覺得太好使了,乾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一代代傳了下去。
不清田,職業戶,從上敘兩處細節可知,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貼裡埋藏的用意,實在深若淵海。
這一次戶貼大登記,從洪武三年底一直到持續到洪武四年底,前後整整一年。因為策略務實、設計周詳,加上最高領導人高度重視,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並沒留下來,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總註冊人口數至少在五千五百萬以上。
這五千五百萬人,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而且處於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願意,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掌控力遠邁從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瞭解天下人口多寡。
這對於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意義重大。
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覺得大功告成之時,大明朝廷又宣佈了:戶貼統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人口會增長,田地會變化,從此以後,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每十年要再重新造冊。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鋪墊罷了。
真正的大戲,要等到十年之後。
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沒閒著。
平定四邊、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復生產,天下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處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還得抽出空來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兩次大清洗,日子過得忙碌而充實。
一轉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了戶貼第一次更新的時候了。
朱元璋沒打算做簡單的資料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統的全面升級。
在朱元璋的規劃裡,戶帖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他不止希望天下變得透明,還希望天下任何一處地方都能觸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達成一種對社會細緻而全面的控制,讓統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貫徹到大明最基本的戶籍單位——每一戶。
在明初那會兒,這個理想可不好實現。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續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中央政令下發到地方,執行難度很高。朱元璋曾經發狠,強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戶遷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會。但這種手段只能偶一為之,不可能在每一個地方都這麼硬幹。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戶貼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於種種客觀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協和折衷,他覺得很不痛快。經過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實踐,朱元璋覺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來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戶部尚書範敏等人商議過之後,朱元璋決定對基層組織下了一次狠手。他給這一次改革設定了兩個目標:
第一、擊破橫亙在朝廷和基層之間的利益集團,提高對基層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這兩個目標看起來背道而馳,怎麼可能同時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對質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眼光投向江南一處叫湖州的地方。
原來早在戶貼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經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個平行的試點工程,叫做小黃冊。
這個小黃冊試點工程,和戶貼制的內容截然不同。
小黃冊的基本行政單位,叫做“圖”。一圖之內,一共有一百戶人家。每十戶人家編成一甲,從中選出一戶甲首來管理,一百戶人家正好十個甲首。再設定一位里長,為一圖最高長官,負責掌管這十個甲首,直接向縣級衙門彙報,不過不算政府編制。
接下來,就到了規則的關鍵部分了。
無論“甲首”還是“里長”,既不是由上級全權指派,也不是由基層民主選出。這兩個職位選拔的方式,居然是輪換制。
首先這一百戶人家按照丁糧多寡,排出一個次序。前十名的富戶,按照排位輪流擔任“里長”一職,每戶任期一年,十年為一輪。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戶,則擔任甲首,每戶分管九戶人家——這九戶人家裡,也包括不當值的里長候選戶——他們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後,由甲內人家進行輪換,也是十年一輪。
也就是說,以十年為週期,一圖之內的每一戶人家,一定會有一年擔任甲首,也有機會擔任一次里長。
這一百戶人家,統一編入一冊戶籍檔案,叫做“小黃本”……啊,不對,“小黃冊”。這個制度,就叫做“裡甲制”。
每一年催辦稅糧軍需時,縣裡把命令下發至當值里長,然後當值里長會召集十個當值甲首,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戶(包括自家)交稅——嚴格來說,十個甲首能管轄到的,只是九十九戶,因為始終有一戶在擔任里長。
你輪值到里長這個職位時,並不意味著可以免除賦稅,反而要承擔額外的管理責任,如果管戶交不起,你還得替他們把缺額補上。為什麼要按富裕程度來選派里長?在這等著呢。
除了這些,里長、甲首還得負責排解鄰里糾紛、文書做保、治安巡檢等瑣碎的庶務,其職能,相當於現在的街道辦、居委會、公證處加聯防隊。
這些庶務,原來都是由當地富戶、鄉紳憑藉威望來主持的,幾乎每一個村裡都有一位土皇帝、幾家大族掌握著權力。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如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機會當“甲首”,有實力競爭“里長”的人家也比從前多,小小一個鄉里諸侯蜂起,這土皇帝自然也就當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一戶為一甲的強行劃分,把一些體量龐大的家族給分割開來。每一個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長要競爭,再想讓他們抱團可就難了。
裡甲輪換制的毒辣,就體現在這裡。
朱元璋的算盤打得很巧妙,皇權暫時下不去,那我就把你們的權力進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給更多人。
一塊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權力最大,大家都捧著;現在朱元璋扔過來十把刀,每個人都可以輪流切一下,原來切蛋糕的人也就變得沒那麼牛逼。
它的精髓在於,把政府讓渡給紳權和族權的權力做了進一步細分,保證每一戶人家都有機會掌握基層權力。這一招看似讓基層更加分散,反而讓中央權威回來了。
更絕的是,無論里長還是甲首的來源,都是從一圖之民中遴選出來。他們沒有官身,更沒俸祿,該職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黃冊的製作費用——均由集體公攤。對官府來說,不需要承擔管理人員的成本。
如此一來,“提高基層掌控力”和“減少管理成本”兩個目標,不就都實現了嗎?
這個裡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來自戶部,而是來自隔壁單位的刑部尚書開濟。
開濟是洛陽人,曾經在元廷當過察罕貼木兒掌書記,是個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於紹興的甲首法拿來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裡甲制。
這個裡甲制度始創於湖州,然後在東南幾省試運轉了十年,效果相當不錯。朱元璋有了底氣,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開始推行全國。
全國版的“裡甲制”,是以湖州版為基礎的2.0升級,兩者的運轉邏輯基本一樣,但在細節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說,除了農村的“裡”之外,還設了兩個同級別的建制:在城市的戶口,叫做“坊”,城郊戶口,叫做“廂”;再比如說,除了民戶之外,軍戶和匠戶也各自造冊,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廟庵觀以及田產,也同樣得建黃冊,不得例外。
在所有的改動裡,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個變化是:一里所囊括的戶數,不再是一百戶,而是一百一十戶。
這個改動有點奇怪,好好的一百戶整數,幹嘛又新增十戶,這不是增加計算難度嗎?
其實,這增加的十戶,才是真正高明之處,代表大明馭民之術又上了一個臺階——甚至可以說,整個改革的目的,就在於此。
湖州“裡甲制”對里長、甲首的職責描述,是“催辦稅糧軍需”、追徵錢糧”。而在全國“裡甲制”的框架下,里長、甲首多了一個職責。
倆字:徭役。
中國老百姓歷來要承擔兩種義務,一是稅賦,要麼交錢要麼交實物;還有一種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興修水利,比如運送軍需糧食,再比如地方官府還有些迎來送往、日常修葺的瑣事,都要徵調人力來做。
這些活都是白乾的,沒有工錢,服役者往往還要自帶乾糧。
徭役對百姓的壓迫,比稅賦更可怕。稅賦雖重,只要你辛苦耕種,總能湊出來;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備乾糧是一重負擔,家裡損失一個勞動力,導致田地拋荒,又是二重負擔——而稅賦可不會因此而減少,最終成了三重負擔。對百姓來說,服一次徭役,等於是三倍付出,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視徭役。沒有這些免費勞動力支撐,古代政府根本無法主持大型公共工程,無法維持府衙日常運作,更沒辦法在戰時組織軍事行動。
朱元璋建起裡甲制,就是打算以其為經緯,把徭役分配給每一戶人家,叫做“配戶當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雜泛”兩種。正役是國家徵調的各項工作,除此以外都是雜泛,內容極為龐雜,如民夫、皂隸、庫匠、轎伕、傘夫、獄卒等……里長和甲首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帶領一臉不情願的老百姓去輪流服這些徭役。
具體規則是這樣的:
全國版的一里之內,分成十個里長和一百戶普通人家。這一百戶人家裡,每十戶立為一甲,甲裡選一戶為甲首。
這十個甲,要排定一個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戶——去應徭役,十年一輪換。不應役之年,叫做“排年”;應役之年,叫做“現年”;
到了應役之年,現年甲首帶著自己所轄十戶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壯丁,到現年裡長那報到,然後一起前往官府,在規定時間去規定地點幹活。完成徭役後,甲首再把壯丁們帶回來。
也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十一戶人家前往應役:現年裡長+現年甲(現年甲首+九戶普通人家)。十年一輪,正好一百一十戶都有份。
我們可以把這個全國版裡甲制理解成四個同心大轉盤:
最內一圈是十個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個里長,再外一圈是十個甲首,最外圈是十個甲。三個輪同時轉動,每一年,都能找到一個對應的里長、甲首以及甲。
這樣一來,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攤派在每一戶頭上。這個設計,可謂巧妙。
為了進一步公平,官府還要對人戶進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為上,寡者為下,每戶輪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規則裡還加了一個監控條款。如果其中一戶逃避徭役被發現,那麼整個一甲十戶都要連坐受罰。如果一個甲出了問題,整個一里一百一十戶都要株連。這樣一來,民眾為了避免自己倒黴,會彼此監視,無形中替官府做了監控工作。
可是,這樣一來會產生一個問題。
當時的國民識字率很低,綜合素質差。人人都有機會管事,可萬一他沒那個管理水平怎麼辦?萬一他有那個水平,卻用來給自己撈好處怎麼辦?就算不徇私枉法,他為了一里私利,去侵佔別家利益怎麼辦?
任何權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為了確保這個制度的平穩執行,又煞費苦心,特意安裝了幾個制約裝置。
第一個制約裝置叫做“老人制”,這是脫胎自漢代三老的一種規矩,在當地選拔年齡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為平息鄉里爭訟的裁決者。朱元璋認為老人“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
根據《教民榜》的記載,民間戶婚田圖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裡甲老人理斷。可見里老人這個角色,等於是在里長之外,安置了一個類似於御史或大法官的獨立角色,用以平衡監督。而且朱元璋還特別加了一條:“不經由里老理斷的,不問虛實,先將告狀人仗斷六十,仍然發回里老去評理。”
好傢伙,越級上告還不行,必須得先經里老這一關。
第二個制約,朝廷下發了一系列規則。它其實是一套裡甲工作手冊,裡面詳細解釋了裡甲工作職能以及各種規矩。比如有份檔案叫做《鄉飲酒禮圖式》,這個名字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鄉村古禮儀法。
這套朝廷出版的規則,再加上地方自行約定的鄉約,構成了基層的準法律條規。里長、甲首就算什麼都不懂,只要嚴格遵循鄉約行事,總錯不了。而且這些檔案是完全公開的,甲內每個人都知道規矩是怎麼回事,無形中也有了制衡。
還有第三個制約。
早在洪武四年,當時裡甲制還沒建起來,地方勢力還很猖獗,對徵糧工作影響嚴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臨時性設定一個叫“糧長”的職務。
糧長的人選,是由當地丁糧多的富戶充當,平均每一萬石(各地區的數字不固定)的稅賦區域,朝廷會設定一人。
糧長的工作,是在前往京師領取文書,返回自己轄區,督促里長、甲首把糧籌集好,再帶隊解運到指定倉口。按照朱元璋的設想,糧長一可以監控官吏貪腐,二來可以繞開豪右攬納,上便朝廷,下通民眾。
等到洪武十四年裡甲製出現之後,里長和糧長的職務範圍就顯得有點疊屋架床。可這個職務非但沒有撤銷,反而更有發揮。糧長開始擔負土地丈量、勸導生產以及和農事相關的檢具、呈遞、蠲免等庶務。
它的地位之高,幾乎等於是裡、甲之上的一個非正式主管,自然也起到了制約作用。
經過這麼一番設計,里長和甲首一來要每年輪換,二來要受老人掣肘,三來還有鄉約來約束,四來還得應付糧長。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確保基層幹部沒有徇私舞弊的機會,更不可能盤踞做大。
皇權到底下不下鄉,其實正是從這些小細節裡體現出來:里長、甲首出自本管,幫役助手皆由其遴選,費用由集體均攤;鄉約代行約束,民事爭端要先訴之於鄉老;錢糧賦稅由糧長與裡甲共催辦之。種種瑣碎事務,皆由地方自決自負,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裡甲制的現實操作中,還有一些務實的小設計。
比如說。雖然法律規定一甲一百一十戶人家,但實際上每一甲的戶數,不可能正好湊齊,總會有一些鰥寡孤獨的家庭。這些家庭已沒法承擔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設計者把這種情況也考慮進去了:每一個裡的一百一十戶人家,叫做“正管”。除此之外,同裡產生的鰥寡孤獨戶,掛靠於裡下,但不算正管之數,有一個單獨分類,叫做“畸零帶管。” 這些畸零戶不允許脫離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們甩開。一旦正管戶缺編,隨時會把他們補進去。
好了,現在規則設計完畢,推行裡甲制只剩下最後一步:登記造冊。
這事應該簡單,此前朝廷已經掌握了天下戶貼的資料,現在只消把分散的戶貼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戶編成一里,不就完了麼?
沒那麼簡單。
或者說,朱元璋沒打算這麼簡單地處理。
以裡甲製為基礎的戶籍冊簿,不再叫“戶貼”,改稱為“黃冊”。 一里造一冊,每一冊一百一十戶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帶畸零帶管,還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戶的等級。戶數滿額叫做全圖,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戶,則稱半圖。
黃冊同樣也是十年攢造更新一次,和裡甲制的三個輪盤同步旋轉。
為什麼叫黃冊?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編撰者張廷玉——認為是其封面為黃紙裝裱的緣故。其實這是因果顛倒了。
“黃冊”一詞,來源於“黃口”。這個詞本意是雛鳥的嘴,後來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戶籍登記中,三歲以下或剛出生的孩子,稱為“黃”——所謂“黃口始生,遂登其數”,是說孩子一生下來,立刻就要去官府報備登記,這是一個人在戶籍裡的起點。從此“黃”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個戶籍的代稱,也叫“黃籍”。
明代第一次攢造黃冊,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後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規定進呈中央的黃冊封面,須用黃紙裝裱。可見是先有黃冊之名,後才用黃色封面裝裱,而非相反。
咱們還是先看幾份實物。
安徽省博物館藏《萬曆四十年徽州府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籍》,裡面的戶口資訊是這麼寫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戶王敘 系直隸徽州府休寧縣裡仁鄉二十七都第五圖匠籍充當萬曆四十九年分里長
回想之前我們看到嘉興人林榮一的戶貼,上面寫的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林榮一的戶貼,寫的只是一個地址和戶籍分類,沒有其他任何資訊。而這個王敘,在地址和戶籍分類後面,還多加了一條“充當萬曆四十九年分里長”。
這個王敘大概比較富庶,屬於十戶里長輪值名單之內,萬曆四十九年,恰好輪到他當第五圖的里長。即是說,在每一次的黃冊攢造中,都得把每一戶的裡甲值年寫清楚。
只是多寫一句話,但意義卻變得完全不同。
戶貼的意義,僅僅在於登記人口數量,最多能為人頭稅提供參考。而黃冊寫明瞭里長、甲首的輪值年份,也就鎖死了他們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記錄一里狀況的黃冊之內,會附有一個很重要的欄目,叫做“編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圖”。這是一張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標戶名,一格一格寫明所有人家的應役次序,一目瞭然,相當於一張排班表。
不過百眼圖體現出的這個賦役,指的是正役,其他還有雜泛徭役和臨時性的徵派,都是當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內。
換言之,黃冊最重要的功能,不止於戶籍登記,就在於強化徭役管理。從此以後,官府可以拿著百眼圖做參考,去調動百姓去服各種徭役,誰也跑不了。
也正因為如此,黃冊在大明朝廷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賦役黃冊。
另外要說一句,黃冊所記錄的,是除現役軍人之外的所有民眾的戶口狀況,主要指民黃冊。還有記錄軍戶戶籍的軍黃冊,匠籍冊、灶籍冊等等,分屬不同部門掌管。
咱們再來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這份原件是嘉興縣的黃冊底稿,但它卻不是在檔案庫裡翻出來的,而是藏在一個誰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飛有個孫子叫岳珂,寫過一部書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間,出版商決定重印這本書。印坊為了節約成本,沒有購買新造紙張,而是從官府弄來一批淘汰下來的辦公舊紙,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處。
從讀者角度來看,這實在是粗製濫造,可對於研究者來說,卻是個大驚喜。因為這批舊紙,正是黃冊的清冊供單——這個接下來會細說——上面詳細記錄了嘉興一些人家的黃冊登記狀況:
一戶王阿壽今男阿昌 民籍
舊管
人丁計家男婦五口
男子三口
婦女二口
事產
官民田地七分二毫
夏稅
麥正耗一升五合五勺
絲二分六釐二毫
棉二分五釐
秋糧米正耗六升六合六勺
官田二分二毫
夏稅絲一釐二毫
秋糧米正耗六升六合六勺
民地五分
麥正耗一升五合五勺
絲二分五釐
棉二分五釐
房屋一間
船一隻
開除人口
正除婦女大一口祖母陳可員於成化十二年病故
事產轉除民一本土一則地三分於成化十六年賣與本都四冊徐順為業
(後略)
從這份黃冊底稿能看到,黃冊的主要內容和戶貼差不多,每戶人家有幾口人、籍貫、性別、年紀、與戶主關係、事產多少等等,但其中卻也有幾個奇怪的術語,比如“舊管”、“開除”什麼的。
這個地方,就是戶貼和黃冊的第二個決定性不同。
戶貼是靜態檔案,它體現的是洪武四年的戶籍狀況。但人口會增減,財產會變化,黃冊每十年一造,必須能體現出這種變化趨勢。
所以黃冊裡的戶籍,多了四柱分項,分別是: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舊管指的是上次造冊的人口和事產數字,新收指本次造冊新增數,開除指本次造冊減少數,實在是本次造冊時的現有數字。
舉個例子吧。比如前面那個王阿壽一家,在成化八年的黃冊登記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還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黃冊要重新登記了。官府戶房小吏跑來他家裡,先調閱成化八年的舊檔,寫下“舊管”數字:人口5口,田地7.2分。
小吏詢問了一下,得知王阿壽的媳婦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個大胖小子,便開列了“新收”一項的數字:人口+1。
然後他又得知,王阿壽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賣了三分地給鄰居。這些都屬於減少,於是小吏又開列了“開除”一項:人口-1口,田地-3分。
一番加減之後,小吏最終寫下了“實在”一項:人口5口,田地4.2分。
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壽家最終落實在檔案上的數字。等到下一個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這一屆的“實在”,就變成了下一屆的“舊管”,再進行新一輪的加減,如此迴圈往復。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這麼一個公式。
這個“四柱之法”,本來在湖州小黃冊裡是沒有的。在試執行的過程中,朝廷發現監控力度不夠,朱元璋就把裡甲制的創始人——試刑部尚書開濟叫過來,問他怎麼辦。開濟稍動腦筋,回答道:“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
一句話,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質。
你想作弊,想把這一期數字改了?可官府調出你從前的檔案,前後四柱一對,便能發現數字有問題。有了四柱之後,每一期數字,都和前後兩期像齒輪一樣緊密咬合,動一處,則牽連全體。這麼一來,朝廷不止掌握了你家的現狀,還控制住了過去和未來,控制力度空前強大。
這招太狠,一經推行,從此“人戶以籍為定”,老百姓再也翻騰不出什麼浪花。
順便說一句。開濟這個人,實在是個國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裡甲制和黃冊四柱之外,他還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員的KPI考核制度,給每個部委的文書處理都定下一個程限,根據完成情況來評判功罪。結果“數月間,滯牘一清”,大得朱元璋褒獎。
從此以後,凡是涉及到田賦、訴訟、河渠工程之類的大型專案,朱元璋都把開濟叫過來諮詢。而開濟也沒讓他失望,“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可謂是明初管理學第一人。不過開濟這個人,算是酷吏,曾擬定過一部反詐偽法,極其嚴苛細緻,連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說你這是張密網以羅民啊。
開濟本身的性格有問題,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從來都不受同事待見。其他官員逮到機會就拼命黑他。有一次,開濟牽涉到一件官司,御史趁機上書,說這傢伙每次都是帶兩份相反的奏章覲見,聽天子口氣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遞,以此邀寵。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聽你連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給棄市了。
帶兩份奏章上朝這種事,不是開濟這種腦子,還真想不出來。
咱們說回黃冊。
黃冊裡面,其實還隱藏著第三個細節。
黃冊裡會記錄一戶的土地狀況,比如王阿壽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這是從官府租的地,還有五分自家的民田——這和戶貼是一樣的,只記面積,不寫田地位置、形狀和肥瘠程度。
不過黃冊比戶貼多了一項稅賦記錄,田地下面,標明瞭夏稅多少,秋糧多少,寫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們說了,朱元璋怕步子邁的太大扯到蛋,所以推行戶貼時,並沒有順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黃冊裡多了土地稅賦一項,說明朝廷終於要開始啃最艱苦的一根骨頭了。
當年形勢不穩,土地清查必須緩行。此時的局勢,已經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裡甲制和黃冊保駕護航,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空前,可以開始搞魚鱗圖冊了。
《明史食貨志》裡記載:“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
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資訊。
第一是時間。洪武二十年開始造魚鱗圖冊,這距離黃冊正式編成已經過了六年,怎麼朝廷工作效率這麼慢?
其實這是《食貨志》說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項持續時間很長的工作,不可能一紙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結果,前期有大量準備工作。黃冊制度之所以推行那麼順暢,是因為戶貼制鋪墊了足足十年。同樣道理,洪武二十年開造魚鱗圖冊,也不是突然之舉。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積極籌備。
明代的魚鱗圖冊裡,是記錄一塊塊田地的檔案,檔案包括每一塊地的所屬、方位、面積、形狀等基本資訊,還要寫明地形、四至、肥瘠種類等等,如果土地涉及買賣分割,還要填寫分莊。如有佃戶耕種,亦要一一標明。旁邊附有檔案編號和地內橋樑、山川、河流等情況。
這還只是一戶的資訊。
十戶的魚鱗圖冊要合成一甲合圖,十一甲合圖再合成一里之總圖,一鄉的若干裡總圖匯聚在一起,交給縣裡。縣裡再一次合圖彙總,上交州、府乃至戶部。
可見打造魚鱗圖冊的繁劇程度,還在戶貼和黃冊之上,絕非一蹴而就。
《休寧縣誌》曾提及:“國朝高皇帝洪武十八年遣官量田,定經界”。足可以證明,魚鱗圖冊的準備工作,從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年之間,從未停歇過。二十年的修造魚鱗圖冊,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罷了。
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頭銜是國子生。
國子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國子學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學府,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通文藝者並充學生”、“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 洪武十四年,他在雞鳴山下設立國子學新址,並於次年改名叫國子監。
大家應該還記得。洪武初年,朱元璋無法推行魚鱗圖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專業人才匱乏。所以他非常重視國子學的培訓,當成了政務儲備人才的培訓基地。既然是政務儲備人才,那麼就不能只讀聖賢書。
朱元璋做人務實,給國子學加了一條規矩,叫做“實習歷事”。它還有一個更明白的名字,叫做“監外歷練政事”。
國子學或國子監的學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須要各個政府部門實習,熟悉政務。他們的身份,就叫做“吏事生”或“歷事監生”。朝廷視其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予以拔擢任用。這種歷練對培養人才的好處,自不待言。讓學生早早經歷政事磨鍊,可以迅速上崗,對於緩解明初人才匱乏的窘境幫助極大。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一口氣選派了一千多名國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縣;洪武二十四年,又選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國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牘;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在冊的國子監生,從原來的平均兩千人,躍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這三個時間節點很值得玩味。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案發,株連萬餘;二十三年,胡惟庸案發,波及數萬;二十六年,藍玉案發,波及萬餘。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讓官場為之一空,這些缺額只好讓國子監頂上去。
“實習歷事”的效果實在太好了,以至於朱元璋覺得有這個選拔制度就夠了,一度停辦了科舉。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開科,他還反覆叮囑“務求實效、毋事虛文”。
這位叫武淳的國子監生,竟然可以主持魚鱗圖冊這麼重大的工作,可見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實習了很久,對庶務得心應手,才會被委以重任。類似武淳那樣的人,還有很多。見諸史書的有呂震、古樸等人,都是國子生出身。可見朱元璋在主導土地政策的同時候,對於配套政策的建設也沒有放鬆。
第三個有趣的地方,是“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
前面咱們也提到過,糧長是朱元璋在“裡”和“縣”之間設定的一箇中間環節,主要職責是催收區域內的稅賦,職責和里長有所重疊。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裡甲制建成以後,這個臨時性職務就該取消。可朱元璋卻堅持保留下來。
保留糧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洪武十四年之後的土地大清丈做準備。
像武淳這樣的監生,縱然能力出眾,可畢竟是中央來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況的人來配合,才好開展清丈。
地方縣府離基層太遠,資源有限;里長、甲首級別又太低,都不適合配合工作。而糧長一來熟悉鄉情,二來糧長的管轄範圍是“隨糧定區”,一區四個糧長,一個糧長的管轄範圍涵蓋一萬石左右的地域。以“萬石”為單位逐一造魚鱗冊,既不至太過瑣碎,也不至太大難以兼顧。
可見朱元璋這個伏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一舉多得。
由於前期工作準備得透徹,魚鱗圖冊編造進展十分順利,趕在第二期黃冊再造之前,完成了兩浙與直隸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沒看錯,只是兩浙加直隸。其他地區的魚鱗圖冊和編甲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才陸陸續續完成,併成為一項長期工作,一直持續到了永樂年間。
從此以後,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偏遠地區和邊境之外,大明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隸地區被朝廷嚴密控制。
從此以後,老百姓和戶籍緊密地聯絡到一起,幾乎沒有出遠門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會隨時查驗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討,衙門也能查到你的黃冊底細,遣返原籍。
黃冊和裡甲鎖住了人口相關的稅費和徭役,而魚鱗圖冊和糧長則掌控了田地租賦。黃冊,魚鱗圖冊以及裡甲制三位一體,構成了一道又一道縱橫鐵索,牢牢地把百姓釘在了土地之上,動彈不得,化為穩固稅基,源源不斷地為朝廷輸血。
大明憑藉著這三樣工具,將控民之術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歷數前朝,還從未有一個政權對民眾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細緻。
賦役黃冊、魚鱗圖冊和裡甲制所構成的體系,對民眾的管束和禁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是不折不扣的“張密網以羅民”。明清兩代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巔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這套底層設計裡。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實現。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三位一體初建之後,全國戶數一千零六十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國耕地面積達到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共可收夏麥四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意味著一個新生政權已經度過了初期難關,徹底站穩腳跟,開始進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心情不錯的朱元璋,向天下頒佈了一道聖旨:“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覺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稅賦已足夠國家開銷,從此以後新開墾的土地永不必徵稅,老百姓隨便種吧。這個的政策開始只覆蓋兩省,很快又涵蓋到幾乎整個北方。
敢於宣佈新墾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這個底氣,正是從成功的戶籍推行中來的。
在很多歷史書裡,作者講到各朝開國君主,往往熱衷於描繪疆場上的血腥攻伐,沉醉於宮廷官場的勾心鬥角,對於民政建設往往一筆代過。讓讀者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只要君王們得了天下,稅賦錢糧、民眾徭役就會自動各歸其位,傾心輸誠。
事實上,這些瑣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難事。老子有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意思是治理一個國家,必須像煎魚一樣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則一不留神就煎糊了。
縱觀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的這一系列舉措,正好是老子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他的每一項政策都經過反覆推演,有設計,有試點,有鋪墊,有妥協,策略務實而有彈性,一步步走得十分紮實。從“戶貼”到“賦役黃冊”,從“一百一十戶裡甲”到“魚鱗圖冊”,從“糧長制”到“實習歷事”,層層推進,有條不紊。
朱元璋別的施政成敗姑且不說,至少在地方戶籍建設上,他表現出了一個成熟、理性、精明且極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
經常有人很奇怪,朱元璋在國初那麼折騰,為何國家沒怎麼亂?答案就在戶籍建設的細節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定戶籍政策時既不論證、也不調研,全憑決策者一拍腦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亂,一亂就鎮壓,鎮不住就遮掩,治大國如和麵,面不夠加水,水不夠加面,大明能不能進入盛世可真不好說。
不過這套戶籍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它太過理想化,從根子上想搞絕對平均主義,又把民眾束縛得極緊,指望他們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