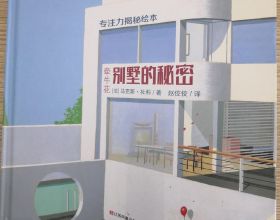陸英是在生第十四胎後因拔牙引起敗血症而死,她無力地躺在床上,任床前一大群孩子哭著喊著。雖萬般不捨,她也只能緩緩地閉上那雙出嫁時驚豔賓客的丹鳳眼,淚珠從眼角滾落,滾過蓬鬆的髮鬢、耳邊,浸潤在枕上成星點。
陸英21歲嫁入張家,短短16年,懷孕14次,為夫家生養了4個女兒5個兒子,基本上出了月子又坐月子。
除了傳宗接代,陸英更大的精力用於維持龐大家庭的運營,丈夫張武齡醉心於讀書、辦學,張家三房老小几十口再加上諸多傭人的家長裡短、人情世故、兒女教育以及大片土地、房產、商戶的賬目投資,都壓在她的肩膀上。
為了博一個“完美”的好名聲,她付出了整整16年的辛勞。
生命最後時刻,陸英明白,丈夫會有新的妻子、張家會有新的女主人,唯有自己的孩子,不會再有愛他們的母親。
臨終前,她對痛哭的大兒子張宗和說:“現在別哭,你哭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01 卿本佳人
韋均一嫁進張家是1923年8月,陸英過世兩年後。
一年前,她是張武齡創辦的樂益女中的一名老師。據說樂益是“陸英”的諧音,是張武齡低調紀念妻子的佐證。
因為擅長崑曲與國畫,再加上容貌不俗,韋均一在學校小有名氣。和那個時代的新女性一樣,韋均一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畢業於上海愛國女學,品學兼優,參加過五四運動,是家鄉有名的淑媛。
這樣的女性為什麼會嫁給比她大12歲且有9個孩子的張武齡呢?
韋布(著名導演,代表作《三毛流浪記》)在談及姐姐的婚事時,曾說這是“一場策劃的婚禮”,當事人(張武齡、韋均一)是無辜、受愚弄的,是女方家長先有此意,韋均一的叔祖父結識了張武齡,修建樂益女中的地也是他賣給張武齡的。
言語間,韋均一與張武齡婚姻的開始似乎並不那麼美好,也許男方豐厚的家底才是促成這段婚姻的關鍵。
哪個女孩不渴望情投意合,不傾心翩翩公子?誰願意在20來歲的時候,給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孩子當後媽呢?誰不知道在“完美主婦”後面接手家務事是費力不討好呢?
對於小嬌妻的委屈,張武齡心裡明白,他向來希望身邊人都好,因此不吝於讓她快樂。
他儘量抹掉前妻在家裡的痕跡,讓她感覺到自在一些。他讓孩子們稱她為媽媽(稱陸英為大大),很少在家裡再提起前妻,對孩子與她之間的衝突進行冷處理;
滿足韋均一的喜好,帶她去上海看美術展、看戲、聽講座,還讓她做了樂益女中的校長;
鼓勵她讀書求學,發展自己的興趣,韋均一婚後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研習國畫和古典文學,後來又考取無錫國學專修館本科;
對於她的親人愛屋及烏,韋均一嫁去張家時,帶著弟弟韋布,張武齡韋對他如同親兒子一樣,韋布曾說過自己的“思想史幾乎全部來源於”張武齡;
包容韋均一,張宗和的日記曾記道:
“......爸爸央著我們下去,請媽媽回來。媽媽不回來,一定坐在門口。爸爸去了,說了幾句好笑的話,把大家都引笑了,四姐更笑得厲害。我們把媽媽擁進爸爸的屋子坐著。”
對韋均一的甜膩寵愛,抹殺了陸英16年的存在,男人的深情真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真實得殘忍。
02 “白雪公主的後媽”
很多問題,並不是我們當他不存在,他就真的不存在。即使張武齡費盡心思,韋均一與這個家庭的矛盾還是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最激烈的是與那幾個大孩子的衝突。
在幾個孩子看來,她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女人侵襲,妄圖取代母親、奪走父親、還要控制她們;
在韋均一看來,她要孤身與9個孩子以及擁躉她們的下人作戰,要去與一個已經死去卻似乎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前女主人爭奪對這個家庭的影響力。
這種對抗在韋均一過門接連生兩胎都夭折後變得更加激烈。她覺得一定是張府有人想害她,可能是那些表面上對她恭恭敬敬的孩子,可能是那些對陸英忠心耿耿對自己抗拒和排斥的老傭人們,她越發暴躁。
據說有一次,韋均一過生日,張家姐妹跪下給她行禮,韋均一竟伸手打了一個女兒的耳光,還罵道:“你這是在拜死人嗎?”
再次懷孕後,韋均一躲回孃家待產,直到平安生下唯一的孩子張寧和。
這讓之前的懷疑變得更加詭異莫測,也讓他們的矛盾越發激烈。

1933年4月,張允和與周有光先的婚禮,張武齡(前排左四)、韋均一(前排左三)、張充和在最後一排(右六)
張家大女兒張元和在樂益讀書時,曾與教員凌海霞關係要好,認她做了乾姐姐。這種超乎尋常的好在眾人嘴裡變成了流言蜚語,籍著流言,韋均一以校長的身份停止續聘凌海霞。
不久後,張元和考上上海光華大學,凌海霞又趕去任教,大二時,韋均一便以家中開銷大、經濟困難為由,要求張元和退學回家。
張武齡對於二人的衝突不加理睬,間接也就幫助了韋均一,眼看姐姐就要失學,氣憤不過的張家二女兒張允和單槍匹馬地跑到樂益女校門口,鼓動學生們集體罷課。
張允和呼籲道:如果校長都不支援自己的女兒完成學業,那其他學生又何必來這裡上課求學?
張允和用破釜沉舟的勇氣,撕破了家庭的遮羞布,讓矛盾暴露在了陽光下,眾人議論紛紛,韋均一感到尷尬和難堪,只得不再提起此事。
但是,韋均一也有回擊的辦法。
她當著張允和的面,聽著她的痛哭、哀嚎聲,燒掉了關於陸英的所有相片,只有一張陸英在閨閣中照得幸存了下來。
所以有人說,張家姐妹愛得自由,對各自小家庭不離不棄,也許是因為她們已經沒有家,沒有了退路。
不過每一個犀利的女子,有幾個是天生的噁心腸呢?至少在張家四女兒張充和眼裡,韋均一算不上面目可憎。
與其他幾個姐弟不同,張充和出生8個月後,就被抱到合肥老家的叔祖母處撫養,與這邊往來很少,直至叔祖母去世,16歲的張充和才回到蘇州。
由於對對方沒有“歷史成見”,兩個人又都愛好書法、國畫、崑曲,韋均一與張充和相處非常融洽。
張充和曾說道:
“繼母只比我大十五歲,我們一起學戲。她愛畫畫,我愛寫字,她看我寫字可以一看看個大半天。家裡的人都不太喜歡她,但她喜歡我,跟我很親,我們像兩個很好的朋友那樣相處。”
韋均一曾畫過一幅《充和吹笛》仕女圖。畫上的充和麵貌清秀,十指輕巧,衣褶寬鬆,儀態嫻雅,唇上一抹紅,格外生動,充和十分喜愛。
1947年的中秋,在充和即將離開蘇州前往北大任教時,韋均一又為她作了一幅小畫,那是出自《牡丹亭》裡《驚夢》的《好姐姐》一曲:“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後來,隨著年歲漸長以及張武齡的去世,韋均一與張家姐弟的關係得到緩解。
其實雙方都並非惡人,如果不是過早樹起保護的刺,穿上厚厚的盔甲,也許她們會有更多的機會靠近對方,瞭解對方。那麼又該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03 孤獨老去
抗戰爆發後,張武齡關掉樂益女校,大家四散而去,偌大的張家四零八落。他們大多去了後方,張武齡則帶著韋均一和張寧回到合肥老家。
在這裡,韋均一過得並不愉快,她很快與張家人產生了矛盾,張武齡只得在其中轉圜。
1938年10月13日,張武齡病逝,年僅49歲。
縱然再吵吵鬧鬧,縱然再怨懟張武齡的“優柔”,韋均一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個很好的人,真誠、善良,是她的庇護者。
國難家仇,生離死別,此時韋均一不過40來歲,兒子張寧和才10多歲,感傷命運漂泊、幼子可憐,她寫下了十四首悼詩,讀來格外悲切。
“兒方束髮未成才,縗(cuī,粗麻布製成的喪服)絰(dié ,喪服上的麻帶子)稱孤已可衰。忍聽深宵人靜候,幾回夢醒喚爺來。”

一九四六年十月,張充和回到蘇州,抄寫了韋均一的十幾首悼念詩詞
好強的韋均一沒有留在老家,次年,她離開肥西回到蘇州,先後在私立英華女校和省立女師教書,後來又去上海租界代課。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進入租界,韋均一便靠待人批卷、謄寫文稿為生。1946年,在張家孩子的努力下,樂益女校復課,她回到蘇州,三年後,她“驟然血崩,乃離職養病。”
新中國成立後,韋均一曾任職於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韋均一的晚年很孤獨。
她唯一的親生兒子張寧和很早出國,再沒回來。
寧和是張家十個姐弟中最小的,特別聰明又懂事,他從小知道自己的母親與姐姐哥哥們有隔閡,就努力去彌補。
他與九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哥哥相處親密,甚至超過了他與母親的關係,他曾經說,我有九個極好的姐姐哥哥。
多年後,張家姐弟憶起往事,提及與繼母的矛盾也因為顧及寧和的面子,淺嘗輒止,一帶而過。
抗戰勝利後,寧和在姐姐哥哥們的資助下,去巴黎音樂學院求學,在那裡,他認識了比利時國家樂隊終身小提琴手吉蘭,兩個人相愛並結為夫妻。
中國解放後,寧和夫婦回國,成為中國交響樂團第一任指揮。他於60年代出國,定居比利時,再沒回來。
晚年的韋均孤身一人住在蘇州,沒有親人照顧,但她堅決不去養老院,靠外面請人一天三頓送飯。
但她一直努力保持著優雅。在侄女的印象中,清早她在肩上披一塊白布,用一把密齒的木梳子,沾著不知是清水還是護髮用品,一絲不苟地梳理她那頭短髮。
年紀再大時,她只能彎著腰做事,一間房便是她的全副家當。因為樓層高,她腿腳不便,所以常年都不下樓。
弟弟韋布想過去照顧她,但因為年事已高,被兒女阻止。侄女們看望她時,嘆“情景淒涼”,便送了個紅燈牌收音機給她做伴解悶。
而在不遠處,蘇州九如巷裡,繼子張寰和一家人十來口擠在五間房裡,顯然,這裡沒有韋均一的立足之處。

復興後的樂益女中郊遊(前排右四抱衣者即張充和,及張兆和、韋均一、五弟張寰和)
1999年8月22日,孤寂了半生的韋均一去世,張寧和並沒有回來,他委託五哥張寰和全權代理,並選擇了不設墓碑的水葬方式。
張寧和似乎更懷念的是在他十幾歲就已經離開的父親。
結語
蘭因且結出絮果,何況一場並不美好的開始呢?
韋均一的憤懣也許是因為初為人婦的不安,也許是出於對張家女兒們自由自在的羨慕,為她自己困在這樣一場痛苦的婚姻而不甘。
韋均一離世時,大概是孤苦的吧。她曾經擁有一大群兒女,但她又活生生地推開了他們。
如果她能開啟格局,理解孩子們失母后的惶恐與不安,多一些溫柔和包容,那麼,也許故事就會被改寫了。
而張武齡,作為孩子與妻子的連線人,他的責任無法逃脫。大概是陸英慣壞了他,才讓他對矛盾視若無睹,假裝“無為而治”。
其實,每個人都是好人,他們原應該可以更快樂。一切的錯誤大概是源於那場建立在利益而非愛情上的婚姻吧。
參考資料:
《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
《曲人鴻爪:張充和曲人本事》
《流動的斯文:合肥張家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