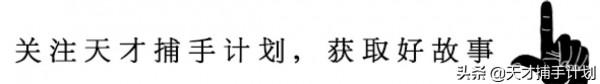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聽過一個笑話,人的疼痛分為1到10級,1級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10級就是生孩子時的感覺。
那你知道11級疼痛是什麼嗎——就是生孩子的時候被蚊子叮了一下。
事實上,真的會有遠比10級疼痛還疼的,醫學上把它稱之為“爆炸性頭痛”。
那是腦子出血導致的,就像掀起你的頭蓋骨,在腦子裡放一掛鞭炮,“砰”一聲炸開,有的人會當場疼暈過去。
神經外科醫生楊正經就曾接治過這樣一個病人。他本以為問題不大,做過手術後,病人就會順利康復。
沒想到,術後第二天,護士只是用棉籤往病人的嘴唇上擦了點水,病人就突然雙眼發直、四肢僵硬,眼看就要死了。
那段時間,接連幾天我總是做噩夢或失眠。
夢境多是混亂的手術現場。手術檯上的女病人睜著眼睛看我,衝我比大拇指,但臉上沒有一絲笑意。
失眠的時候,我就坐在電腦前查資料,不停地摘錄論文、課本上的內容,累的時候就想想手術過程,或者看著那個女人的CT片子發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在一天前的晚上,這個女病人突然抽搐,昏迷,氣管插著管,任我怎麼呼喊和刺激都沒有反應,心率極快,血壓也很高。
我剛接管她的時候,一切完全不是現在這樣。
這是我做醫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到救人失敗的滋味。
這個叫王淑紅的病人是夜裡送來的。
在急救室,我看到床上躺著一個50歲左右的長髮女人,面色蠟黃,體型微胖。她樣子挺和藹,只是會時不時嘆氣,還一直閉著眼睛。
她的CT檢查顯示,腦袋裡有個叫蛛網膜下腔的地方正在出血。
我給她做了檢查,除了脖子很硬之外,其他肢體都可以自如活動,只是雙手出汗很多。聽她不停嘆氣,我實在擔心她的精神狀態,就問有煩心事兒嗎?
“我頭疼,大夫,那會兒可疼了……”話還沒說完,淑紅又幹嘔起來。
我明白,這種因顱內出血引起的頭痛稱為“爆炸性頭痛”,也叫“一生當中從未經歷過的頭疼”。
就好像給你的天頂蓋鑽個窟窿,往裡面扔個鞭炮,“啪”地一聲爆炸,痛感比分娩還更強烈,很多人疼得當場就能昏迷。
而淑紅的乾嘔,則是因為顱內壓力升高,形成了顱內高壓,這種症狀的典型表現就是噁心、嘔吐。
尤其是病人在發病時已經吐空了胃裡的東西,但仍然還是會幹嘔時,簡直生不如死。
為了緩解她的痛感,我只好讓護士給她用了一支止疼藥。
在監護室外面等了很久,我才見到淑紅的丈夫,是個臉型圓胖的中年男人,穿著樸素,臉上鬍子拉碴,穿一身公交汽車司機的工服。
可能因為經常開公交車,肚子比較大,衣服像懷孕似得往前頂,跑快了或者著急了就能聽到“嚶嚶”的喘鳴聲。
他把手裡的押金條、發票、住院證這些東西,一股腦兒都遞給我,說:“大夫,哪個是要給您的?”
我看他滿頭大汗的樣子,把他帶到醫生辦公室,拿了凳子讓他坐下先歇會兒。
我告訴他,淑紅的症狀叫蛛網膜下腔出血,這種顱內出血,多半是腦袋裡血管上的動脈瘤破了,但具體的發病位置還需要做進一步檢查來確定。
他聽我說話,不停地咽口水,兩隻手握拳放在膝蓋上,身體漸漸繃直。
等到聊完,已經快凌晨12點了,他決定要做手術。
我囑咐他儲存好體力,如果很累就可以在一樓的家屬等候區的沙發上休息,有什麼問題我會隨時手機聯絡他。
第二天一早,我到病房門口才知道,這個男人因為妻子膽小而不敢離開她,在病房樓道外面湊合了一晚上。
我本想勸他到一樓休息,他搖搖頭,又朝監護室看了一眼,笑著說:“晚上看不見她,我也挺不放心的。睡在樓道里,我倆只隔了一堵牆,至少離她更近一些。”
淑紅在家發病,起初只是感覺頭痛,以為躺一會兒就能好,沒想到頭痛得越來越厲害,後來還吐了一地。
她平日裡一沒事就會去父母家走動走動,或者下樓跟周圍鄰居聊天,趕上鄰居需要幫忙,她也總愛衝在前面。
但發病時,她打的第一個電話,是給她丈夫,而不是她父母、鄰居,甚至不是120。
她總說,怕麻煩別人。
入院後,淑紅給所有醫生護士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剛入院那晚,我瞭解完淑紅的病情後,臨走時給她蓋了蓋被子,記得她當時輕聲對我說了句:“大夫,謝謝您啊,給您添麻煩了。”
監護室裡,每個病人手邊都會有一個按鍵器,他們在感覺不舒服或需要幫忙的時候,按下按鍵,就會把護士叫來。
住在ICU第一晚,那麼痛苦,但那個按鍵淑紅一次都沒按過。她只是靜靜地躺在病床上,睡不著覺也只是一直換姿勢。每次護士給她量體溫,她都會輕聲說句“謝謝。
就連排尿不暢這麼大的事情,都是護士主動過去看了,才發現的。
當時護士本想給淑紅插導尿管,但我擔心她因為插導尿管的刺激,造成顱內再次出血,所以,我和護士給她蓋上單子,把尿盆墊在屁股底下,鼓勵她自主排尿。
一開始她不好意思,直到勸了好久,她才終於尿了出來。
其實,人在生病難受的時候,大都很難有心情和別人交流,有的人甚至還會發脾氣。
但淑紅並沒有因此拒絕跟我們交流,她拖著病體儘可能地配合我們,生怕自己表現得不好,惹了誰生氣似的。
第二天上午,交班時我把她的情況跟科裡的大主任做了彙報。主任建議儘快安排手術,等待得越久,淑紅腦子裡的動脈瘤再次破裂的風險就越高。
手術方式有兩種,一是開顱,二是介入治療,都是常規手術,只不過後者比前者貴些。
我把這些情況如實告訴了她丈夫,同時,也想讓他在手術方式上拿拿主意,但男人堅持想徵求妻子的意見後再決定。
我在監護室外等著淑紅的丈夫出來,他剛一出門,就告訴我,他們已經決定開顱治療。
那天上午10點,我安排完術前的準備,來到病房跟淑紅談話。
剛走進去,就看見護士正在為她盤發。
淑紅的頭髮很長,時不時的就會和吸氧管纏在一起。護士一邊熟練地幫她梳理頭髮,一邊用言語鼓勵她。
不一會兒,護士就在她頭上盤了個髻。陽光從窗戶透進來,金色的,很溫暖的樣子。就像是年邁慈祥的老奶奶,在輕輕撫摸孫女的額頭。
“楊大夫,又麻煩您來一趟啊。”淑紅見我來,立刻跟我打招呼。
她見我還在忙碌,說道:“大夫,您這昨天忙一晚上了,今天還不下班啊?你們也夠辛苦的。”
這句話聽著讓我很感動,很少有病人生著病還能關心醫生的身體。
後來,我自信地向她保證,這個手術很成熟,主任也會親自操刀,而我也會以助手的身份來和主任一起完成這個手術。
我隨即指了指她隔壁的空床,說:“隔壁床的王奶奶做了和您一樣的手術,她的情況和您一樣,現在已經從監護室轉到普通病房了。您就放心吧。”
她這才點點頭,對我說:“大夫,我老公剛才也把這些事情跟我說了,我們都相信你。”
那臺手術過程非常順利,用時5個小時,術中出血50毫升,基本沒有出什麼血,開顱和關顱的操作也都很標準。
因為開顱的原因,術後,淑紅頭上的刀口周圍,產生了軟組織腫脹的情況,她一側的眼睛腫得就像被蜜蜂蟄過一樣,眼皮被頂得很清亮,完全沒辦法睜開。
雖然淑紅精神很弱,說話也不是很清晰,但聽到我的聲音,還是緩慢地說到:“謝謝大夫”,接著,她朝我伸出了一個大拇指。
淑紅恢復得很快,從手術室剛剛推出來不久,我就給她做了測試,讓她活動四肢,伸出手指,再咳嗽幾下,她都是一口氣做下來的。
第二天晚上,淑紅口渴想喝水,因為是術後,護士只敢拿清水棉籤蘸一蘸她嘴唇。
哪知道剛沾溼了,淑紅突然雙眼發直,然後四肢僵硬,很快意識消失,呼吸也不好了。
我們幾乎沒有排查出任何可能性。
主任的考慮是,淑紅術後產生了全腦血管廣泛痙攣的併發症,但也僅僅是考慮。
他讓我再去跟淑紅的丈夫說說話:“畢竟你才是主管醫生,這個時候需要扛起大旗,要不然你怎麼成長?”
得知淑紅出事後,那個男人蹲在我的面前嚎啕大哭:“楊大夫,這是怎麼回事?主任剛才說人不行了,可是昨天她還好好的啊!”
我沒做聲,幫他拿了凳子,讓他坐在凳子上,但他仍然蹲在地上。過了幾分鐘,他慢慢緩了過來,坐了下來。
他低著頭說:“她是個苦命人,嫁給我沒跟著過過幾天好日子,現在又得了這種病,我很對不起他。”
淑紅的丈夫當兵轉業後,成了公交車司機,常年在外工作,淑紅則在學校當老師。
他說,常常覺得自己沒本事,兩個北京人卻住在燕郊,讓淑紅跟著他受苦受罪。
但淑紅卻總對他說:“我當初和你在一起,啥也不圖,就圖你是個老實人。”
淑紅膽子小,丈夫又時不時加夜班,每次夜班回到家,淑紅總是沒睡,並且已經把熱好的飯菜給他準備好了,看著他吃完了飯,才會跟他一起休息。
聊了很久,他對我說:“我能進去看看她嗎?”
他顫巍巍地走進監護室,走到淑紅的床旁,撲通一下跪了下來。
他握著淑紅的手,眼睛緊緊盯著淑紅,總看不夠似的:“阿紅,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啊……”說著說著,他哭了,但盡力壓著聲音。
大概過了十分鐘,我扶著他出了監護室。
等他緩過勁兒來,他看著窗外,忽然說:“楊大夫,她是特別好的一個女人,為什麼會趕上她呢?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也不知怎麼回答,我只知道,自己要不惜一切代價,去救淑紅。這關乎我做這個職業的目的。
我要做一個好醫生的想法,從我小時候就有了。
我出身在一個小縣城,從小怕死,有次嘴上長了一個包都把我嚇得要死,連夜去掛號。
初一的時候,一天躺在床上,我感覺到心突突直跳,整個床都被帶著跳。嚴重的時候,我臉色蒼白,噁心想吐。
去了醫院,做了心電圖,那個醫生告訴我說,我心臟上面有根線,比一般人都細,這個線如果斷了,隨時會死掉。
我非常緊張害怕,但不久又自己好了。現在我知道,那叫做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算不上大病,那個醫生的話簡直是危言聳聽。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想做一名醫術高超的醫生,可以給自己看病,也可以讓別的病人不再擔驚受怕。
後來如願考上醫學院,當上了醫生,我感覺自己對這份工作有使不完的勁兒。
做住院總醫師是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的第一步,有家醫院曾有這樣一個說法,以形容這個職位的辛苦——據說所有的男醫生進去後,都要剃光頭,因為一旦忙起來就是幾個月不休息,根本沒時間理髮。
我在的這家醫院,兩個醫生每人輪值24小時。我最多曾連續工作接近50小時,離開醫院的時候,腳都在打軟。
我知道,那個狀態,我隨時會猝死,可是,如果下次還有需要,我還是會去上50小時的班。
那時我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醫生,但我就想不遺餘力,讓自己所學有所用。
尤其是淑紅這樣的病人,她越是不願麻煩我,我就越想幫她。
因為我還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是不喜歡麻煩別人的人。
在宿舍睡覺,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我都躡手躡腳的,生怕吵到別人;手術室裡別人脫了衣服可以隨身一扔,我得強迫自己撿起來;別人可以隨意把車停在某個地方,我不行,誰給我打了電話,我也會著急,趕緊要挪車。
更何況,我還給了淑紅一個期許,說我肯定能救好她。
她還說不管怎樣都相信我。
我越來越覺得,救好淑紅這樣的病人就是我做醫生的理由。
自從淑紅出事後,我幾乎沒睡覺。出事當晚,我熬了一宿,翻看她各種抽血化驗的結果、CT報告、平時的檢查,同時,幫她調整呼吸機,提升血壓,糾正電解質紊亂。
連著兩天通宵後,我實在熬不動了,想回去休息一下。
可到了床上,睡覺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腦子根本停不下來,反反覆覆迴圈的,全是淑紅的病情。
然而,一切的猜測在週一交班的時候都被推翻了。沒有人能對淑紅的情況做定論,只能說高度懷疑術後全腦血管痙攣。
如果想驗證這個理論,只有帶病人去做進一步的“CTA”檢查,需要往血管裡注射顯影劑,並帶去CT室。但現在淑紅經不住折騰,可能還沒推出病房,人就沒了。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累了。
手術前,我因為不確定淑紅的精神狀態,曾經多次對她進行查體和測試。
有一次,我進病房的時候,發現她精神好了很多,嘆氣少了,雖然還是閉著眼睛,但氣色紅潤不少,血壓和心率也很平穩。
但我們只聊了一會兒,她就問道:“大夫,我病得突然,也不知道孩子怎麼樣了。我老公剛剛過來了,但我們沒說上幾句話,您能讓他進來跟我說說話嗎?對了,大夫,我這到底是得了什麼病啊?早上的檢查有結果了嗎?”
我斟酌著一點點把病情告訴她,聽了我的話,她把頭轉向窗外,又閉上眼睛,雙手合十,向我表達感謝。
直到術前的幾個小時,淑紅還在問我是不是住在監護室,就說明她的病情很嚴重,可能沒得救,又或者擔心她的女兒很久沒有見媽媽,吃不到媽媽做的飯菜會不習慣。
後來,一向不愛麻煩別人的淑紅,第一次對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堅持要我把丈夫叫到監護室裡說說話,把家裡的銀行卡、存摺的存放點和密碼告訴丈夫。
靠著升壓藥,淑紅的生命被延長了兩天,但我們仍舊沒找到淑紅的病因,高度懷疑全腦血管痙攣的結論,還是沒能被改寫。
內疚感持續圍繞著我。
我感覺自己欺騙了患者。說好的小手術呢?說好的回去照顧閨女呢?我沒有實現,我感覺到了當醫生以來最蒼白無力的時刻。
再見淑紅丈夫,他明顯滄桑了許多:“大夫,淑紅是個怕麻煩的人,所以,她出事到現在,我也沒有通知什麼親朋好友,我最後的希望,就是想讓她父母和我們的女兒進去看看她,可以嗎?”
那時,淑紅住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這裡的探視規定和普通病房不一樣,每天有明確的探視時間段,每個病人家屬,也需要遵循儘可能少地待在監護室的原則,而且一次只能允許一名家屬進入探視。
考慮到淑紅正處在彌留之際,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允許多名家屬同時探視她。這大概也是淑紅入院後,給我們添得最大的“麻煩”。
這幾天,淑紅的丈夫也一直想方設法瞞著淑紅的父母,本以為淑紅很快就能痊癒出院,到那時再跟他們說也不晚。
站在我旁邊的男人嘆了口氣,說:“現在是怎麼瞞也瞞不住了。”
得知女兒的訊息後,老兩口第一時間趕到了醫院。
看見昏迷的女兒,頭上纏著厚厚的紗布,氣管插著管,什麼反應也沒有,老父親假裝鎮定著,而老母親因為傷心過度,沒多久就住進了樓下的心內科病房。
最後一個得知淑紅病情的,是她的女兒,那個她在清醒時一直擔心,放不下的人。
那天早上,一個瘦瘦高高的身影,跟在淑紅丈夫身後,進了醫院。在父親的帶領下,女孩終於見到了自己的母親。
監護室裡,女孩愣愣地站在那裡。
直到父親讓她摸著母親的手說說話的時候,再次感受到母親那冰冷的雙手的時候,這個孩子哭了,很大聲音的哭了,不停喊著“媽媽……”
男人最後說:“閨女啊,過來,給你媽媽好好磕個頭吧,感謝她的養育之恩吧!”
女孩泣不成聲地跪在地上。
砰!砰!砰!
我聽見了一遍遍清脆的響聲。
那一刻,我再也繃不住了,淚水奪眶而出。我趕緊扭過頭去衝著牆,我怕家屬看到,我也怕別的護士看到。
過了很久,淑紅的丈夫從監護室裡走了出來,對我說了一個讓我十分震驚並且久久難忘的決定:
“大夫,我們想好了,我老婆是個善良的人,總想著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平時在家,她也經常救助樓下的流浪狗、流浪貓,我們商量了一下,已經聯絡好紅十字會了,要捐獻淑紅有用的器官,給那些需要的病人。”
行醫幾年來,很少聽說有家屬主動願意捐獻器官的,雖然新聞上經常見到零星報道,但這個事情,其實離我們醫生和老百姓都很遙遠。
聽到他的話,我心裡五味雜陳,只能告訴他,因為我所在的醫院沒辦法處理活體器官捐獻,所以,淑紅需要先去到紅十字會醫院,在那裡結束搶救措施,等待生命結束,再讓醫生從她的體內取走能用的器官。
這個轉運的顛簸過程,對她而言可能很痛苦,我讓淑紅的丈夫好好考慮。
最終,男人在捐贈書上籤了字。
淑紅帶著呼吸機和搶救用的升壓藥,被緩緩推出醫院,我的心都要碎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我和科室照顧過她的護士,還有主任等一行人,把這一家子送到醫院門口,看著淑紅被抬進救護車裡,越走越遠。
她正緩緩地離開我,離開世界。
淑紅是我真正救助失敗的第一個病人。在她之前,只有那些十分危重的病人,我才有可能救不回來。
她走之後,我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大概一兩個月,我的工作狀態都非常消極和混亂。
那時我掌管著科室分配病人的權力。每晚,科室收了新病人,我都會仔細檢視,只要發現是因為動脈瘤而入院的,我都會故意繞開自己,把他們分給別的同事。
有時實在繞不開,也會先接收。但到了病人手術的時候,我都會假裝在忙其他的事情,故意錯過這臺手術。
如果連手術都躲不掉,我上手術檯時,也只是會選擇一些簡單的、打雜的活兒來做。
當時有朋友和同事發現了我的異樣,和我一起出去吃飯,曾經性格活潑、總是滔滔不絕的我,已經變得只知道低頭吃飯,很少言語了。
有一次,我和一個同事吃飯,期間我不知因為什麼,想起了淑紅,總覺得是自己害死了她。我突然跟同事說:“誒,哥,你看我似乎不適合神經外科吧?”
同事以為我最近收病人多,工作強度大,累得都說胡話了,也沒當回事兒,囫圇過去了。
見他這反應,不知道為什麼,我接著問:“哥,我覺得以我的能力,乾脆轉到病案室整理文書得了,你說呢?”
同事笑了笑,說我忙工作忙傻了,讓我趕緊回家好好休息。等調整好狀態,還得繼續在神經外科奮鬥。
但這些話對當時的我而言沒什麼作用。
我漸漸像是有了什麼強迫症似的,時時刻刻都害怕自己的病人死亡,害怕病人會突然出現病情變化。
當時有幾個我接管的動脈瘤病人。
一個是在他的術後第一天,我就開了增強CT的檢查單讓他儘快做複查,我想確定他在術後,會不會有血管痙攣。
等那個病人到了CT室,值班的醫生問我,病人的病情還這麼嚴重,能不能過幾天再做檢查,沒必要非在病人情況還沒見好轉的時候做。
但我還是堅持要讓病人檢查,彷彿病人不做CT,就真的會像淑紅一樣,突然從我身邊離開。
還有一個病人,我開了經顱彩超的檢查單,但當時病人的頭上還纏著厚厚的繃帶,根本沒辦法做彩超。
超聲科的大夫看到檢查單,十分不解:“這頭上還纏繃帶呢,小楊為什麼非要讓他做彩超啊?”
不得不說,淑紅悲劇的後勁兒實在太大了,就像是踏進沼澤裡,我越使勁兒掙脫,陷得越深,甚至還波及到了監護室的護士們。
那段時間我進監護室都不太笑了,還經常會因為護士們沒有及時給患者吸痰,而衝她們發火。
有一次,有個護士調整了我給病人設定好的呼吸機引數,我看到以後,不僅氣沖沖地跑去質問她,還去質問和她一起值班的其他護士。
起初,我身邊絕大部分人都不以為然,覺得只是我間歇性的心情差罷了。後來,是護士長向我們科室的主任反映了我的情況。
那時淑紅走了有大約一個月了。
主任是發現我很久都沒怎麼管過因動脈瘤而入院的病人,並且還接到了影像科對我的投訴,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我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對病人再投入感情。
有一次,我值夜班,碰到一群遇到車禍的患者們,在救治一個患者的時候,我看他腿被撞得不輕,而且還是在剛收工準備回家時發生車禍,於是一邊幫他處理傷口,一邊多說了句:“你這工作這麼晚,撞得還不輕,真是不容易啊。”
沒想到他聽了這話,把我臭罵了一頓。
我和一個師兄聊天,他聽了我的遭遇,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還年輕,上次他還被人吐過一口口水。
這位師兄告訴我:一個好的醫生,可以跟病人共情,但更要學會節制,這行就是這樣,你想救更多的人,就不能讓自己越陷越深。
每一個醫生,最大的心願和企盼,都是想讓病人好好的。但在我們與天較勁的過程中,卻不總是能贏的。
後來,我又找到主任,把自己內心的壓力和想法都說了出來。
“主任,我覺得我欺騙了這個病人,我沒有把她救回來。”
主任反而沒有著急安慰我,他沉默了幾分鐘,才緩緩說:“你騙了她什麼呢?你已經做了你所有該做和能做的事情了。”
那天臨出門前,主任說,你必須要把這個病例記在心裡,使勁兒鑽研,畢竟,你的路還長著,想要成為真正的好醫生,就得不斷進步。
五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他們的話,成為了比當年更好的自己,救活了更多的人。
我遇到了一個從樓上摔下來,摔得一塌糊塗的人,但我沒有放棄,讓他活了下來;我也用100天的時間,救活了一位腦幹出血的患者,避免了一個家庭的破裂。
時至今日,我還留存著淑紅的病例筆記。我仍然不敢確定淑紅死亡的原因,是不是就是術後引起的全腦血管痙攣。
但我想,如果我還一直記得淑紅,我還繼續努力的話,總是會越來越好的吧。
楊正經對淑紅的感覺,並非醫生中的特例。
知乎上有這樣一個問題:醫生在搶救手術失敗後會有什麼心態?
很多醫生說都會有經歷無力感的時候,尤其是本來並非危重的病人,卻沒能救回來。
這種無力感,有時甚至會摧毀一名醫護人員。
比如去年就有一位護士因為確診疫情的病人自殺,內疚不已,整天都在哭。
還有紐約的一位急診科主任,頻繁目睹患者過世,在抗擊新冠疫情多日後自殺。
這是常人無法理解的壓力,也是醫生們必須獨自面對的一關。
我也一直擔心楊正經醫生有沒走出這段往事。而他的這一句話,讓我稍稍放心了些。
這是他偷偷給五年前的自己寫的一句話:
今後的日子,你還會遇到救不過來的病人,還會灰心、懊惱、鬱悶,但千萬別放棄,在淑紅阿姨之後,還有更多人等著你去救。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馬修 彈簧
插圖:花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