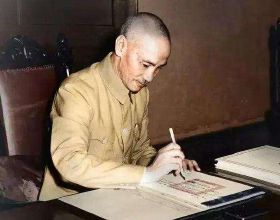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長期以來,軍人在阿拉伯共和制國傢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學者認為其原因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阿拉伯國家,軍隊往往代表相對先進的力量,具備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本條件;其次,阿拉伯較為落後的社會結構和部族文化形成“強者為王”的思維定式,這為軍隊干政提供了適應的外部環境;最後,中東國家面臨的安全難題,客觀上需要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參見田文林:《軍隊干政:中東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現象》,《世界知識》2012年第3期,第33頁。)因此,中東國家的軍隊不僅是指導現代社會所必需的工業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還是威權主義實現穩定的關鍵變數。
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軍人當道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則成為政權更迭的重災區,而這些國家又多是軍人階層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的政權,如埃及、葉門、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蘇丹和阿爾及利亞。其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和葉門薩利赫政權在2011年第一波“阿拉伯之春”中倒臺,蘇丹巴希爾(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政權、阿爾及利亞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政權則在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中倒臺。上述國家中,除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被美國推翻外,只有敘利亞阿薩德政權艱難存續至今。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相對於以往中東國家歷史上比較純粹的軍人政變,在“阿拉伯之春”中幾乎找不到軍隊直接憑藉武力奪取政權或進行暗殺奪權的典型軍人政變,但軍人階層在阿拉伯國家轉型中又的確發揮著十分重要作用。
從總體趨勢上看,相對於過去,軍人在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中的作用呈現出既利用民主程式又依靠實力施壓的隱性和柔性特點,這應該不失為一種微弱的進步,因為懾於民意、輿論和民主程式等壓力,軍人階層越來越無法直接發動赤裸裸的軍事政變。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並未出現直接的軍事政變。但是,如何準確評估軍人階層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十分困難。
首先,軍人在原政權倒臺和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十分複雜。它既可能在現政權命令下鎮壓民眾抗議,也可能表面上彈壓民眾抗議但並不全力鎮壓;既可能敷衍觀望靜待塵埃落定,也可能表面上站在民眾抗議一邊向原政權施壓,但實為發動隱性政變。例如,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軍人幾乎在不同階段扮演了上述所有角色,甚至更多角色。
其次,從政治轉型結果的角度評價軍人階層的作用更加困難。評價政治轉型,需要把民主、穩定和發展等結合起來進行辯證評價。如果徒有選舉等程式民主,而沒有穩定和發展,這無疑是失敗的民主轉型。另外,在阿拉伯共和制國家中,軍方還往往是世俗力量的代表,軍人干政往往具有捍衛世俗化、防範伊斯蘭力量建立伊斯蘭主義政權的作用。這些內容都涉及如何客觀評估民主與威權以及在複雜現實中合理平衡二者的關係。
在強調軍人作用複雜性的基礎上,結合軍人階層在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過程中作用的大小和差異,可以把軍人階層的作用劃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一、突尼西亞方式:軍隊基本未乾預民主轉型
在突尼西亞民主轉型中,軍人階層基本未對民主轉型施加影響,同時國家基本保持穩定,這是突尼西亞民主轉型相對成功的標誌。突尼西亞既沒有像埃及那樣迴歸軍人威權,也沒有像葉門、利比亞那樣陷入內戰和部落衝突。因此,有學者認為,軍隊在突尼西亞和埃及兩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不同的轉型環境是決定兩國民主轉型一成一敗的結構性原因。
突尼西亞的民主轉型具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軍方自始至終扮演不干預政治的局外人角色;二是各主要政治勢力達成了政治妥協。突尼西亞軍隊之所以未像其他阿拉伯共和制國家那樣長期干政,與突尼西亞軍隊在其形成和發展程序中相對獨立的傳統有關。首先,突尼西亞軍隊並非由獨立戰爭中反法殖民鬥爭的戰士組成,而是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軍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突尼西亞軍隊並非像埃及和阿爾及利亞那樣成為國家的締造者。其次,突尼西亞獨立後,無論是文人出身的布林吉巴(Habib Bourguiba)總統,還是透過軍人政變上臺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總統,都嚴格限制軍隊的作用和規模。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將軍方的職責限定在保家衛國、抵禦外敵的範疇;為防止軍人政變危及其統治地位,規定凡是在安全部門任職的公民不得參與選舉;縮減軍隊規模,壓縮軍費開支,使突尼西亞軍隊人數控制在四萬左右。
因此,突尼西亞不同於埃及等其他中東國家,軍人階層未能形成權力和利益相結合的特殊利益集團,其干預政治的動力也因此大大縮小。“突尼西亞軍隊的職業化和遠離政治的傳統使其在革命後迅速回歸軍營”,使突尼西亞民主轉型較少受到軍人干政的影響。禁止軍人干政也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透過立法得以制度化,2014年頒佈的突尼西亞憲法明確規定,武裝部隊“必須保持完全中立”。當然,軍隊未對民主化程序進行干預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如突尼西亞國民同質性較強,使其避免了部落、教派、部族衝突的干擾;其外部安全壓力也較小,不像埃及長期處在阿以衝突前線。
二、埃及方式:軍隊對政治轉型進行全程干預並且不斷變換角色
軍隊在埃及社會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軍隊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在一起,2011年以前,三位總統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都無一例外地來自軍人階層。埃及軍隊的特徵和作用可歸結為三個方面:團隊意識的明確化,軍人作為埃及民族主義的代表,是埃及共和國的創立者、建設者和保衛者;團體利益的特殊化,軍人階層是有著巨大經濟和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團體行動的自主化,軍隊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具有獨立於文官政治系統的自主性。憑藉自身掌握的資源對內政外交施加影響,並且根據自身利益決定其行為選擇。有學者甚至稱埃及軍隊為一塊獨立的“飛地”。鑑於學界對軍隊影響埃及政治程序的情況較為熟悉,這裡主要強調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軍隊對埃及政治轉型干預的全面性。軍隊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從2011年“1·25”革命到2月11日穆巴拉克辭職,埃及軍隊先是在抗議民眾和穆巴拉克政權之間態度矛盾,但最終轉向不鎮壓民眾抗議並對穆巴拉克施壓,成為穆巴拉克政權垮臺的核心原因之一。從穆巴拉克辭職到2012年6月穆爾西當選為埃及總統,軍方領導的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導了埃及的政治過渡程序,期間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圍繞議會選舉、立憲和總統選舉進行了複雜的博弈。
從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即穆斯林兄弟會執政期間,埃及軍隊與穆爾西政權貌合神離,並在妥善把握民主與秩序、世俗與伊斯蘭、穆爾西政權與反對派關係的基礎上,準確拿捏政治節奏,直至廢黜穆爾西政權。此後,軍方先是還政於過渡政府,後又由軍方代表塞西參加總統選舉,並兩次取得選舉勝利,同時採取打擊穆兄會、發展經濟、整肅極端主義等舉措,把經濟和安全作為主要施政任務。
從某種程度上說,儘管國際輿論對軍方在埃及政治轉型中的作用尤其是廢黜民選的穆爾西政權頗有指責,但埃及軍方對政治轉型的全程參與,是避免埃及轉型失控或陷入嚴重動盪的保障,因此有學者稱其為埃及政治的“總節制閥”。
第二,埃及軍方對政治轉型尤其是民主化影響的複雜性。首先是民主與威權關係的複雜性。在埃及政治轉型過程中,一方面,軍隊是民主轉型的促進者和監護者,軍隊在民眾抗議時期最終選擇站在民眾一邊,在最高軍事委員會時期組織議會選舉和制憲工作,在總統選舉中對穆兄會獲勝的認可和接受,在廢黜穆爾西政權後還政於臨時政府,都表現了其接受民主化潮流的一面;另一方面,軍隊對自身特殊利益的維護、為穆爾西政府設定障礙以及最終廢黜穆爾西政府,直至使埃及重回威權體制,又使埃及軍政關係有重回穆巴拉克時代之嫌。
其次是伊斯蘭、民主、世俗化關係的複雜性。埃及軍隊是世俗化的維護者,但其廢黜穆爾西政權的做法又無疑是對民主的傷害。因此,軍隊在埃及政治轉型程序中是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的維護者,也是世俗主義的捍衛者,但同時也是軍隊利益的維護者和威權體制的重塑者。
總之,埃及軍隊在政治轉型程序中體現出了它對威權和秩序的偏好,其態度也經歷了從觀望、中立到積極干預的轉變。埃及軍隊及其建立的威權體制固然存在著種種問題,但它又是當下避免使埃及陷入動盪和無序的現實選擇。這也恰如塞西在2013年6月23日對穆爾西政府的最後通牒中所言:“軍隊是有道德感的群體,我們有責任避免埃及滑向混亂、派系衝突、國家崩潰的深淵。”當然,當前具有軍政體制色彩的塞西政權仍面臨宗教與世俗、民主與威權、安全與發展等一系列矛盾的挑戰,其核心是解決“阿拉伯之春”的兩大核心訴求——民主和民生。
在北非地區,2019年發生政權更迭的蘇丹和阿爾及利亞,軍方在其政治轉型中的作用與埃及有相似之處。截至目前,在向蘇丹巴希爾政權、阿爾及利亞布特弗利卡政權施壓促使其和平交權,主導過渡時期政治程序方面,蘇丹和阿爾及利亞軍隊發揮的作用都和埃及軍方相近,其具體情況和最終結果都值得關注和研究。
三、葉門方式:部落化的軍隊與碎片化的政治轉型
葉門作為一個典型的部落國家,其軍隊至今也無法擺脫部落化特徵,導致軍隊並不效忠於國家和政府。在1978年薩利赫任總統之前,葉門政治為內戰和政變所充斥,其中都有部落勢力的影響。儘管葉門政府也試圖透過改革實現軍隊的現代化,但始終無法改變軍隊結構部落化的痼疾,導致軍隊高度分裂和脆弱。當然這種痼疾的形成既與葉門社會的部落傳統有關,也與葉門政府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把部落作為政治操控的工具密切相關。
從1978年薩利赫任總統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葉門政權與軍隊的關係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葉門政府利用葉門社會的部落結構,透過賦權給關鍵部落、在軍隊中大力扶持關鍵部落,換取關鍵部落對政府的支援,形成政權與部落之間的庇護網路。薩利赫透過對部落、軍隊和政府精英進行相互內嵌實現利益均沾,把部落、軍隊和各界精英構建成“部落—軍隊—商人複合體”,同時透過政治權術進行平衡,來維護葉門的政權穩定。
第二階段,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以來,薩利赫試圖利用美國和沙特支援葉門反恐打擊“基地”組織的機會,透過組建由其自身和家族控制、與常規國家軍隊平行的武裝力量,並透過改革削弱部落對軍隊的影響。但這種努力並不成功,導致薩利赫政權與軍隊和部落的矛盾日趨尖銳,這是軍隊和部落精英在2011年支援民眾抗議浪潮,迫使薩利赫下臺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見,部落和軍隊精英迫使薩利赫和平交權在本質上並非對民主的支援,而是由於其自身利益,也是葉門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反映。
2011年4月,在海灣合作委員會尤其是沙特的斡旋下,薩利赫和平交權,葉門進入政治轉型時期,這種和平過渡的方式還一度被國際社會稱為“葉門模式”。但軍隊部落化的痼疾使新任總統哈迪(Abdrabuh Mansur Hadi)繼續透過軍隊部落化、家族化清除異己力量,教派武裝(如胡塞武裝)和地方武裝(如南方的分離力量)、極端力量(“基地”組織)等多重武裝力量對抗政府,加之沙特等外部力量的干預,導致葉門的政治轉型很快為政治力量的碎片化所取代。
在葉門政治轉型中,軍隊部落化對政治轉型失敗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首先,哈迪總統以軍隊部落化的方式清除薩利赫家族和穆赫辛(Ali Mohsen al-Ahmar)家族的軍事高官,用來自他本人所在的南方部落軍官加以取代,這無疑是以新的部落化取代傳統的部落化,其後果可想而知。2012年,哈迪先是解除了4名省長、20多名高層軍事指揮官的職務,其中包括多名薩利赫系高官。隨後哈迪又解除了穆赫辛將軍的職務,並重組其控制的第一裝甲師,統一聽從國防部調配。在葉門軍隊重組過程中,哈迪重用南方系軍官,有意打壓包括薩利赫系與穆赫辛系在內的北方人。哈迪的做法激怒了兩個實力派系,在哈迪上臺一年半內,葉門至少有22個旅發生過兵變。此外,薩利赫本人及其派系之所以一度轉向與什葉派胡塞武裝結盟,共同反對哈迪政府,也與哈迪在政府和軍隊改組中對薩利赫派的排斥密切相關。
其次,什葉派胡塞武裝除對哈迪政府民族和解大會結果和政府取消石油補貼不滿外,對哈迪政府未能在軍隊中安排兩萬胡塞武裝民兵也強烈不滿。胡塞武裝的訴求無疑也是葉門歷史上部落尋求加入軍隊—部落庇護網路的做法。此外,薩利赫派和其他部落派系的軍隊之所以在打擊胡塞武裝過程中敷衍了事,甚至加入胡塞武裝,都是軍隊部落化的表現。
最後,在原有胡塞武裝與哈迪政府對抗的格局下,原本與政府合作的“南方過渡委員會”的武裝力量轉向與政府對抗。在沙特與哈迪政府長期打擊胡塞武裝未果的情況下,南方七省開始於2020年4月謀求 “自治”,其武裝力量與政府軍爆發衝突,這不僅是軍隊部落化的表現,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葉門政治的碎片化。
軍人干政會繼續存在,但日益受到規制
軍人干政是影響“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但也呈現強弱程度不同的多樣性和作用的複雜性,就其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方式的隱性和柔性特徵來看,軍人干政儘管會繼續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式的規制,赤裸裸的典型軍事政變已呈現頹勢。就本文選取的突尼西亞、埃及和葉門三個案例而言,軍人干政的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
在突尼西亞,軍隊基本未乾預民主轉型;在埃及,軍隊對政治轉型進行全程干預並且不斷變換角色;在葉門,軍隊部落化導致了政治轉型碎片化。就中東國家軍人干政的發展趨勢而言,儘管它會繼續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式的規制,典型軍事政變呈現頹勢。其原因在於三個國家的國內外環境和社會結構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也恰如亨廷頓所言:“隨著社會發展變化,軍隊的角色也就發生變化。在寡頭統治的世界裡,軍人是激進派;在中產階級的世界裡,軍人是參與者和仲裁人;當市民社會出現後,軍人就變成現存秩序的保守的護衛者。”
總之,軍人干政在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異常複雜,對其進行評價應該客觀具體。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