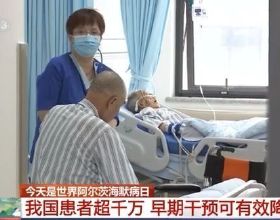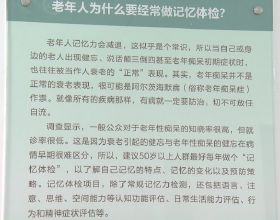你好生活,對生活說你好。
發生在2021年的故事,他們的開場是出乎意料的,過程如夢如幻,結局悲喜交加,回憶起來回味無窮。
稱呼在改變,感情在升溫
在職場上,有很多約定俗成的事情,比如稱呼。如何稱呼新入職的同事?大家習慣性地套用公式:小+姓氏。
我入職後,大家都叫我小陸。
最開始,有任何一個人打破統一模式,開口說出非小陸外的稱呼,其他人都會投來詫異的目光和驚奇的提問。“為什麼要這麼叫她?”或者笑著複述一遍稱呼。這時,我會感到失落,“為什麼不能這麼叫我?”
入職一年,我們一起經歷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有過很多相似的情緒,才換來革命般的友情。
她們從什麼時候開始不再叫我“小陸”?而是叫我阿月,這是一件很難追根溯源的事情。
關於稱呼的改變,我只記得其中一件很小的事情。一個同事叫我“小陸”,另一位同事詫異地問:“你怎麼這麼叫她?”
也許,有些人會不經意地回到統一模式,但會有人提醒她:我們的關係不似從前那般遠。
這個城市依舊繁華,人不要忘記快樂。
不該責怪年紀,其實是我玻璃心作祟
有一段時間總是提到“顏值即正義”,源於朋友在職場中因為外貌受到不公平待遇。
有一天,和同事吐槽業務線的上級工作人員,煩躁於她總是喜歡讓我們重複報同一份材料。同事評價她工作能力一般,態度卻非常差,長得也醜。說到這裡,我意識到我們的話題開始走偏,從就事論事變成了人身攻擊。
我想問:“這跟醜有什麼關係?”如果我這麼問,得到的回答肯定是“有關係啊!”如果我這麼問,會顯得我不近人情,首先是我挑起的話題,他跟我站在同一戰線,用他自己的方式幫我排解不良情緒,卻受到我的質疑,多少都感到心涼。所以,最終我選擇用沉默終結了這個話題。
被評價“醜”,其實是一件難以讓人接受的事情。
早上等打卡的時候,同事仔細端詳著我說:“來到這裡工作不久,阿月都糙了很多。”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後,立即恢復理智,精準地抓取量詞,不久和很多,閱讀理解過後得出正確答案:我是以倍速變得粗糙。
我是一個容易因為別人的評價而感到焦慮的人。
上初中時,發小就開始關注自己容顏的變化,面板出油、毛孔粗大,她都會想方設法去改善,而我滿臉爆痘,卻依然覺得自己挺好的,不需要護膚。上高中的時候,我被家人要求護膚,也只能做到“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到了27歲的這個早晨,我卻因為同事輕飄飄的一句話,開始陷入年齡焦慮、容貌焦慮。
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定義“花樣年華”。
在一些事情上,我總是開竅得比同齡人晚很多年。
我開始靜悄悄的焦慮,靜悄悄的悔不當初時。
卻有些人張揚地緩解了我的焦慮。
來自陌生人的讚美,真誠而熱烈。
很多故事都發生在有一天。
有一天,同事讓我幫她拿東西下樓給她的小姨。“她長啥樣?今天穿什麼衣服?我咋認識她?”“你只需要記住一點,她是兩個你。”用的詞彙不多,卻過分有意思。我總是在不經意間發現我同事特別優秀,特別是在描述別人這件事情上。
坐落在鬧市區的辦公樓,每一天都會上演人來人往、車來車往。這一天,最難的事情是在人來人往中找到我想找卻不認識的人。
“你是誰的小姨嗎?”在我打算問第二個人時,一箇中年婦女眼中含笑地從遠處走來。
你有沒有過瞬間清醒的感覺,驚覺“她就是我要找的人”,然後一腔孤勇向前,最後喜不自勝。
我把東西遞給她後,還廢話了一番:“因為我不知道您長啥樣,所以只能看誰像就問誰,哈哈哈。”
後來,我對同事說:“瞎說,怎麼可能是兩個我,頂多1.5,多一寸都是傷害。”
隔了好幾天,同事將她小姨的話複述給我們聽。她小姨直誇我長得漂亮,只是可惜她兒子已經結婚了。“她真是火眼金睛,我戴了口罩都能看出我很漂亮。”
我只能相信“美人在骨不在皮”。
還有一天,小學學生要接種第二針新冠肺炎疫苗,我們作為志願者去協助接種工作。在校門口等待進入校園時,校長說需要兩個打字比較快的志願者協助醫護人員。本來已經安排另外兩位同事去協助,另一位同事臨陣脫逃,對我說:“你打字比較快,還是你去吧。”
我們穿著志願者服站在教室門口,來來往往的學生中有幾個比較調皮地大聲說:“志願者姐姐好漂亮”。我當時還和同事玩笑道:“好在,不是叫阿姨。”
在忙碌列印憑證時,一個小男孩站在桌邊,露出半個頭,小心翼翼地問:“阿姨,我可以回去了嗎?”確認留觀時間已經足夠的情況下,我詢問他沒有家長陪同嗎?他小聲地解釋家長太忙了,他打完針後就走了,只剩下他一個人。我叮囑他回家注意安全,他就走進了人群,沒了身影。當時,我有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可當回過神看向通往校門的路,看向那一張張天真清澈的臉,眼前真實的一切讓我清醒過來。
我的童年校園時光是久遠到陳舊的事情,我就像是一下子長大,一下子生活在了大人的世界。
“每一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儘管只有少數人記得。”
那些牽著小男孩、小女孩的手的大人,都曾是小孩。
那些小男孩、小女孩總有一天會長成大人。
有時候想到時間如白駒過隙,情緒起伏會很大。
多希望時光慢旅,讓我們盡情享受這枯燥乏味的生活。
要做一股自由的風,自信且勇敢
小時候,老屋旁有一顆龍眼樹。到了夏天,等不及龍眼完全成熟,小姑姑就會帶我們爬上樹摘龍眼。我那時候膽小,不敢爬上樹,只能在樹下眼巴巴看著她們在樹上邊摘邊吃。
長大後,同齡人都走入婚姻,開啟新的人生,我依然還是那個眼巴巴地望著她們的人。
大學畢業的第三年,陸陸續續收到朋友的好訊息,也不間斷地收到家人、朋友的催婚。
我會在這些現實問題面前,變得焦躁不安。
但世界不是按照我的想法運轉的,我渴望的和真實發生的總是背道而馳。我遲遲遇不到一個真誠且堅定的人走向我。
我說:“談戀愛我只是女朋友的角色,而婚姻就不一樣,我要扮演兒媳、妻子、母親、保姆……我應付不來。”同事說:“我只是恐婚而已”。
也有人說:“當你遇到一個對的人時,一切都會變得很順利。”
想起陳銘說的:“客觀上你不需要愛了,你主觀上就做好了迎接他的準備。”
那麼多觀點放在一起,得出的結論還是一個疑問,愛情之於我,之於我們,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很難尋找到答案,卻還是會止不住的嚮往。
2021年的最後三天,我的耳邊一直響不停:“你看上哪個了?這四個你看上哪個了?”到最後,我連做夢都是相親,花花大世界的音樂節、趙雷在臺上唱著歌、《三十歲的女人》、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電影院的爆米花、最熱門的電影,很多毫不相關的人和事拼湊在同一個場景裡。
繁雜的一天,形成了一個很荒謬的夢。
朋友從十月份開始就一直在追問:“給你介紹個男朋友要不要?”我沒有肯定地回答他要還是不要。十二月底,謎底揭曉,他想要給他的堂弟介紹物件,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能幫到他堂弟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人生離不開“成家立業”這四個字。
後來,在辦公室,他坐在沙發上,指著他身邊的A對我說:“這個也是未婚。”我的腦海有很多冰冷的答案,比如關我什麼事?但我不該計較,“你真的是時時刻刻不忘紅娘這個角色。”
此後的工作中,他總希望把我和A安排在一組。
年輕氣盛時,總希望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中年人的熱情,然後不動聲色地拒絕,所有的故事止於相遇一場。
2021年的最後一天,我和A一組,但故事沒有更多的後續。
中午我在樓下等盒飯,A剛好結束工作回到辦公樓樓下,我讓他等我5分鐘,他答應了。但過了一會,他說:“已經過去兩分鐘了”我當時真的很詫異,問他“你不會真的在跟我算時間吧!”後來,我和同事複述了這件事情,她說:“真的要這麼計較嗎?”
突然的玩笑並不適合不太善於言辭的人,因為很難讓人感受到笑點。
那天下午,我被好幾個人圍住追問,“我們單位下來的四個單身男青年中,你看上了哪一個?”
這真的很難選,所以我最終放棄選擇。我應該是他們帶過的“學生”中最不開竅的那一個,寧願得零分,也要放棄唾手可得的一百分。
所有的工作結束,朋友還說:“明年爭取把我嫁出去。”我沒想到,我讓他這麼操心。
但不為所動依然是我雷打不動的作風。
古城樓,紅燈籠。
英文裡的過去式和進行時
離開校園多年後,腦海裡最先想起的英文單詞是bye、hi和hello,一個是離場結束語,一個是開場開場語,很適合用在這悲喜交加的最後一天和第一天。
2021年就這樣倉促地走到了終點,這悲歡交替的一年謝了幕,這滿是未知的一年正如朝陽般冉冉升起。
我圈子裡的人,都在彼此祈禱明年沒有創城和疫情,都在祈禱明年的所有材料一稿過。
我們都知道,無論明年的境遇如何,我們都要昂首踏步向前。
正如2021年,我們一邊哭泣一邊奔跑。
我站在2021年尾看2021年初,看2021年我們走過的每一步,每一步都飽含著希望。
“小時候我很喜歡逛街,但沒多少機會逛街,長大後我天天逛街。”這是副主任說的。
這一整年,我們在大街小巷留下多少腳步,與多少行人擦肩而過,和多少個小攤小販對話,撫摸過多少飽經滄桑的牆,多少次扯著嗓門高聲說話。
2022年敲響了我們的門,圍擋施工的道路通車,古城樓建成,大紅燈籠高掛,老藥房回遷,沉寂了一整年的角落恢復了生氣。
這一整年,我們在不變中經歷著很多變化。
早上下地鐵時,另一位同事興高采烈地向我描述,她在地鐵上遇到兩個長得很像的人,一個是我的同事,另一個是同事的朋友。她還拿出照片給我看。
後來,我見到了那個和同事長得很像的人,就在古城入口。
所以,你能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沒有驚喜嗎?
很多年前,我從朝陽地鐵A口尋找距離地鐵口一百多米的旅店,在百貨大樓和西關天地迷路了半個小時。很多年後,我一遍又一遍地走過這裡的大街小巷,走出了一張地圖,深深地刻在腦海裡。
人生真的很奇妙,緣分也許就在下一個轉彎,所以別害怕轉彎。
剛入職時,同事總問我為什麼不從A口出站,我對她說我對這地方有陰影,並將多年前的事情告訴她。
入職好幾個月後,早上上班的時候我們總會在A口相遇,然後一起出站,一起走過好幾個轉角,一起見證朝陽在朝陽的東方升起,照耀在商場的玻璃窗上,然後說一句“早上的太陽真的好烈”,然後快步向前。
文/阿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