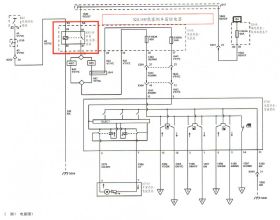自小我是個不曉事“闖禍阿二”。孃的粗暴擰扭記憶猶新。每年總有一兩次,娘撳住我頭,使勁用肥皂搓我的耳後和脖子,毫無溫情可言。
家父早逝後,母親靠48元一月的工資養活我們兄妹四個,只夠維持了城鎮最低的生活水平。哥哥格外懂事,十六歲就到外地鐵礦做工貼補家用,弟弟妹妹小,是媽媽寵愛的物件。我家子女過日子從不挑剔,有個三毛錢肉絲做的鹹菜湯,已是心滿意足。
上世紀七十年代,買東西都要票證,買點又便宜又能解饞的那個葷菜,只能半夜去排隊。一毛五分錢一斤的小帶魚;不要肉票的槽頭肉、奶脯肉,必須排在前五人才行。
半夜娘來叫床,她激勵我:“你可以有一毛錢,大餅油條粢飯糕、老虎腳爪、豆腐漿,一次買一樣,你可以輪著吃。”親孃不騙人,寒冷冬夜,我披著又大又舊的棉襖,拿個破籃,圍在街頭捂夜的大餅爐子旁,大概與新中國成立前流浪的癟三差不多。我從沒怪過孃的狠心,以為不勞而獲才是可恥。
我們兄妹四人上學都申請減免學雜費,這在優等生中是極少的。我們也根本不好意思向娘要一元錢買一支狼毫筆學書畫。所以我退而學剪紙,材料費省多了。文具、運動衣褲、運動鞋還是無著落。娘問同事要了兩隻青紫藍小兔,對我說:“兔子養大了,賣了錢,新球鞋、文具、小人書隨你們買。”
有了目標,我放學回家,馬上斜背一個布袋,無論是雨天還是大雪紛飛,都衝出去割兔草。那時窮人多,養兔的多。要走好幾裡地,才能裝滿布袋。冬天是兔子懷孕生崽的時候,必須選有白奶汁的“黃花郎”(蒲公英)。一個荒野獨家村叫墳山屋,屋後是一座高大土堆,那裡有很多蒲公英。灰暗的傍晚,陰風呼號,對一個10歲出頭的孩子來說絕對恐懼。我往往叫上一個夥伴,飛快地鑽入乾枯的棉花地裡,屏住狂跳的心臟,警惕地聽著各種烏啼,又飛快地逃離,這種事只能兩人同行,不會互嚇;三人行,必定被一人的疑神疑鬼弄得逃散。
那時孩子識相,總能擔當好家庭的角色。17歲未滿,我也主動插隊落戶,好給弟妹創造工礦工作機會。娘似釋然一粲,好似預料之中。就像高爾基《童年》中的祖母一樣:一個富人與高爾基打賭,如果少年高爾基晚上敢睡在一個剛死的人棺材上,富人就付一個金盧布。高爾基心動了,他的祖母居然高興地拿著被褥送高爾基去“值夜”。我娘則將父親留下的舊腳踏車、一件舊大衣和一雙舊高筒雨靴修好補好。
苦日子終於熬出頭,娘去還債時,幾次帶上我。為什麼不在借的時候?她不會讓孩子難堪,苦逼會壓垮靈魂的!而還債是一種驕傲,她只想讓我記住那些好人。
四個孩子相繼大了婚配成家,有天我跟娘去市百一店,買回憑票的新馬桶,從南京東路外灘到延安東路輪渡站,娘看著我一個大小夥子彆著大學校徽,拎著馬桶逛外灘,實在臉紅,就拿過馬桶自己拎。那天跟在娘背後,我忽然發現,她是我親孃。
冬至前,兄妹四家一起聚餐聊著“娘最喜歡誰”的話題,我卻說著娘種種“狠心的事”,大家都笑得噙著淚……(辛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