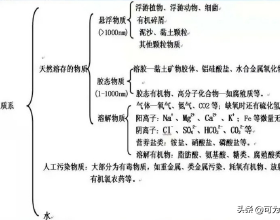今天來談談王陽明的“心法”。
陽明先生晚年始終在強調一句話,叫“事上練”。
他說:“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這個道理很好懂,人只有做事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長自己的本事。
離開了實踐,縱理論天花亂墜也不過紙上談兵。
所以人要多去做事,對不對?
如果我們如此去理解陽明先生這句話。
那就大錯特錯了!
陽明先生提出“事上練”,不是讓我們透過做事去磨練自己的能力,而是磨練我們的心。
因為心為人之本。
陽明先生談心從來要帶個功夫,因他把人心看得很透。
何為功夫?
透過練習進而達到某種境界即是功夫。
所以,陽明先生此言告訴我們。
人想要真正擁有強大的內心,一定是要在我們接觸到事情時候內心情感波動處去下功夫加以練習的。
光靠讀幾本聖賢書,聽兩句“人生哲理”,來個開宗明義式的頓悟。
或在風和日暖、鳥語花香間把著到個氣定神閒,定全都是自以為是的假象。
扭頭遇到事情,立馬就會被打回原形。
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陽明先生只提到一個“練”字,那這個功夫該如何下?
首先,佛家講人一念三千,一呼一吸間便有百千萬個念頭。
而大部分念頭多為閒思妄念,這些念頭固然是假,但對自我心理狀態的影響可是真的。
我們可以反思,我們有多少平淡的心境被無端冒出的陳年舊賬燃起怒火?
我們有多少鬥志死於內心對失敗未來的無限推演?
我們又有多少躁鬱來自我們與自我內心執念的糾結?
如此想來,李涉那浮生半日閒真是人生難得的至寶。
所以,陽明先生“事上練”的第一“事”,即是閒思妄念。
治心如治水,堵塞只會帶來更大的決堤。
念起念落就如同滾滾流水,人們總說要“止念”,但縱是你時刻緊繃著心絃,強行按壓著念頭,也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一念不生。
而且如此用功久了,精神長期緊張,反而搞不好要落下個神經衰弱的毛病。
我們當知所謂“止”,是將心門全部開啟,四面透風,任由念頭自然出入,無所滯留,進而實現的一種動態的“止”。
念起念落,我們只管生出旁觀者視角遠遠看著,監視自己本心不受念頭牽扯就好。
要勿忘勿助,既不忘記對念頭的監視,又不刻意干涉。
久而久之,功夫純熟,自我內心自然一片清靜,再不被閒思妄念所困擾了。
第二,我們的內心平日無事之時是“寂然不動”的,但因其有一念靈明,故能“感而遂通”。
也就是我們的情感、情緒等等一切心理狀態,在接觸到外物的時候自然就會生出。
或憤怒、或喜悅、或憂傷、或恐懼,這些心理狀態便是當“練”的第二“事”。
人不可能沒有情緒,我們要做的是讓情緒處於一個合理的範圍。
正如《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所謂“中和”,就是以情緒沒有產生的心理狀態,去調和喜怒哀樂這些情緒。
為什麼近乎各家都推崇靜坐呢?
並不是說靜坐能夠讓內心產生“覺醒”式改變,而是透過靜坐我們能夠體會到情緒沒有產生之前,那種清淨、平和、淡然的狀態。
這種狀態就好比鹼,情緒外放則好比酸。
只要功夫深,對這種狀態足夠熟悉,一旦情緒爆發,我們便立刻從內心翻出這種感受經驗去中和過分的情緒。
如此情緒便能夠很快穩定下來了。
第三,便是慾望的問題。宋儒提倡“存天理,滅人慾”,他們主張把自我內心一切慾望克除。
但人非草木,怎能無慾?
故而陽明先生講“存天理,去人慾”,主張我們要去除掉多餘的慾望,也就是私慾。
那麼問題來了,怎麼區分哪些慾望是多餘的慾望?
所謂“天理”,即我們內心本源生命情感的自然流露,依託生命情感而生的慾望就是正常的慾望。
而但凡慾望中加入了一絲人為的刻意,人為念個“偽”,故而此等慾望便是多餘的慾望。
好比我們遇見一個乞丐,窮困潦倒、飢寒交迫,我們心生不忍給了他一些錢。
這就是我們惻隱之心的自然流露。
但若我們幫助這個乞丐的念頭中多了一絲刻意,想著自己這叫佈施,是有功德的。
或是幫助完他之後心中感到洋洋得意,覺得自己真是個大好人。
如此私慾便來了。
順帶一提,如此佈施,恐不僅沒有功德,還造下了貪業,當注意。
所以,這第三“事”怎麼“練”,讓自我生命實踐的原動力迴歸生命情感之本源。
在每件事情發生之處尋找自己內心的那些熱愛、憐憫、感激等等情感,克服掉那些刻意的心機與功利。
長此以往,我們便無時無刻不在“天理”之中。
所以綜上,這就是“事上練”的三個比較典型的方面,如此分類而論是為方便理解的權宜之舉,本不該如此。
畢竟人心一念靈明,萬事萬念皆有所不同,其五花八門又豈能僅用三類涵蓋。
但這三類卻也將我們日常內心的普遍狀態盡數涵蓋。
相比僅僅把著著“事上練”三字行表面功夫,或走向了“實踐出真知”的旁路。
從此三點入手,倒也不失有“攻玉”之效,不妨一試。
最後,再次強調一下,心性境界的提高,只有靠每件事、每念間的功夫去磨練,進而實現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它沒有捷徑,不是頓悟來得,更投機不得。
所以,陽明心法聽起來高妙,實則簡單、粗暴。
我們一念下了功夫,心性境界就提高一分,一念忘記了功夫,心性境界便降低一分。
若念念不忘下功夫,久而久之,功夫自然純熟,境界也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