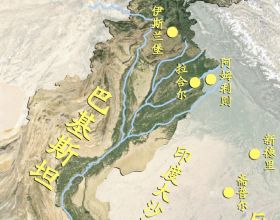1946年3月19日,《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等近十家中國權威媒體,在當天的頭版頭條,全部刊登著同一個醒目的標題:
“清算血債!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短短14個字,但那份激動和期待卻已躍然紙上,這一天,是梅汝璈趕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日子。
隨著日本投降,盟軍佔領日本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塵埃落定,不過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戰後的清算工作卻才剛剛開始。
為了讓那些在戰爭中犯下累累罪行的軍國主義狂人受到應有的制裁,同盟國在日本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用來審判日本首要甲級戰犯,這些人中包括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等,每個人手上都是累累的血債。
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近3600萬軍民的傷亡,此刻終於到了要血債血償的時候,中國方面也派出了自己的大法官,參與這場世紀大審判,這個人就是梅汝璈。
大法官是由各國政府提名,然後盟軍統帥部直接任命,不過在此之前,梅汝璈其實從來沒有正式擔任過法官職務。
這就很讓人奇怪了,要知道,大法官在如此重要的事件中,如此重要的人選上,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什麼挑中了一個沒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人呢?
從清華少年到法學權威
1904年,梅汝璈出生於江西南昌下面的朱姑橋梅村,由於父親梅曉春極嚴的家教,梅汝璈從小就刻苦讀書,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儲備,為之後人生中的種種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2歲那年,剛剛小學畢業的梅汝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這所學校是美國政府用部分庚子賠款建立的,目的就是培養中國的優秀人才赴美留學。
8年之後,20歲的梅汝璈從清華畢業,踏上了去往美國的求學之路,此後,他先後就讀於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並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1928年,完成學業的梅汝璈回到了中國,並接受了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時任陝西省教育廳廳長的冀貢泉的邀請,進入了山西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
作為留學歸來的法學精英,當時國內多所大學其實都對梅汝璈丟擲了橄欖枝,但他為什麼偏偏選擇了山西大學呢?
這其實跟山西大學的來歷有些關係,當時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在中國建立了兩所大學,一所是梅汝璈的母校清華,另一所就是山西大學。在清華學習了8年的梅汝璈很清楚,美國人在中國建學校,動機並不單純,他們有著更深層的目的,那就是的是想把中國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國,透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思想灌輸,將他們培養成為美國服務,幫美國控制中國的高階知識分子,說白了,就是讓他們變得“崇外”。
正如當時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中所說的那樣:
“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這是梅汝璈不願見到的事情,因此,來到山西大學後,他一邊教授法學課程,一邊培養學生們的愛國情懷,在與學生們的交流中,他直接點破了美國的企圖:“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以此引起學生們的警惕,避免被潛移默化地影響。
同時,對於當時的中國在許多地方落後於西方國家的事實,梅汝璈也從不迴避,相反,他教育學生,要大大方方正視這些問題,要“明恥”。
“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後來由於閻錫山“閉關鎖省”,梅汝璈離開了山西大學,之後,他輾轉在國內各個大學任教,教授法學課程,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同時,他還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對於各項法規的制定與推行,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不知不覺間,當初12歲的清華少年已經慢慢成為了法學界的大人物。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同盟國準備組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訊息傳來後,身為國內法學界權威的梅汝璈就成為了大法官的不二人選,他專業的法學素養以及赤誠的愛國之心都是勝任這個職位的有力保障。
不合理的座次安排
出發之前,梅汝璈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道:
“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託,作為莊嚴國際法庭的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那些擾亂世界、殘害中國的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這是他對萬千父老鄉親的保證,也是此行的最終目的。
梅汝璈知道,本次審判肯定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爭執和衝突,但他沒料到的是,審判還沒開始,就出現了問題。
開庭之前,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各國法官們的激烈討論,那就是大家的座次安排問題,11個代表各自國家的大法官,按什麼樣的方式排序就坐,這是一個看似無關緊要卻又十分敏感的問題。
關於這件事情,《法庭憲章》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既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的各國法官組成,那座次理應也要按照受降簽字的順序來排定,在1945年9月2日美國“密蘇里”號的受降儀式上,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是各國代表中第二個進行簽字的,僅排在美國之後,按照這個順序,美國法官坐在審判長的右手邊,中國法官則應該坐在審判長的左手邊。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慘、與日寇作戰傷亡最大的戰勝國之一,但本次審判的審判長卻由澳大利亞的法官韋伯擔任,不得不說,這著實有些不合理。
而更不合理的還在後面,韋伯想安排與他比較親近的美國法官及英國法官坐在他的兩側,梅汝璈一聽這話不禁怒火中燒,開什麼玩笑,英國在二戰中,尤其是遠東戰場,對日軍一再退讓,基本沒形成有效的抵抗,在東南亞一敗再敗,潰不成軍,反觀中國抗戰,當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3600萬軍民的傷亡,才換來了今日之勝利,兩相對比,高下立判,英國又有什麼資格排在中國前面?
梅汝璈知道,此刻的他就代表著中國,代表著身後千千萬萬的同胞,所以,他決不能答應。
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冷靜地提出應該按照受降書籤字順序來安排座次,並表示這樣才最為公正。
對於梅汝璈的提議,韋伯沒發表意見,既沒答應,也沒反對,態度很是讓人玩味,梅汝璈知道,平靜之下往往是看不見的暗流,韋伯模稜兩可的樣子讓他更為警惕。
拒絕彩排
1946年5月2日,梅汝璈已經來到東京40余天,今天要進行開庭前最後的預演彩排,這也表示座次的問題今天必然會確定,因為第二天就是正式開庭的日子。
下午四點鐘,11位大法官已經到齊,韋伯隨即宣佈了眾人的座次安排,中國法官位於美國和英國後面,排在第三位,韋伯果然沒有聽從梅汝璈的建議,仍然我行我素。
梅汝璈當即就提出了強烈抗議:
“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
梅汝璈的話字字有理有據,鏗鏘有力,得到了在場諸多法官的認同,隨後他接著說道:
“如今這種安排是荒謬的,究竟意欲何為?我不接受這種安排,也不打算參加預演!”
說完,他脫下象徵權力的法袍,拂袖離去,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以這種形式形式抗議韋伯的無理安排。
“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
韋伯沒想到梅汝璈的反應如此強烈,他跟隨對方來到辦公室,對這位強硬的中國法官解釋道:“我之所以把英美的法官安排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式更熟悉一些,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沒絲毫歧視中國的意思。”
梅汝璈不認同這種說法,他憤怒地反駁道:“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一定要英美派居中的必要!”
韋伯被說得啞口無言,他只得從另一個角度開始勸說梅汝璈:“按現在的安排,你的兩邊將是美國法官和法國法官,而不是那位蘇聯將軍,這對你來說應該是非常愉快的。”
聽到韋伯這好似為自己著想的話語,梅汝璈依舊不為所動,他冷冷一笑,說道:
“庭長先生,我不是為了愉快才來到東京的,我的祖國長期遭受日本戰犯們的侵略殘害,對中國人來說,審判日本戰犯將是一件非常沉重、嚴肅地任務,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工作。”
這番話說得韋伯面紅耳赤,他低聲說道:“那你稍等下,我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說完飛快離去。
不一會,韋伯回到了辦公室,這一次,他換了一副更嚴肅的表情,低沉開口道:“這項安排是盟軍最高統帥的安排,如果你不接受,很可能會影響到中美之間的關係,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這種行為。”眼見勸說無用,韋伯轉換了思路,搬出了盟軍統帥部和中美關係威嚇中國法官。
誰知梅汝璈絲毫不懼,針鋒相對的說道:“我絕不接受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我相信我的政府也不會接受,當然,我也可以辭職,讓他們請另外的人來接替我。”
說到這裡,梅汝璈看了看韋伯,繼續道:“此外,我懷疑,這是不是真的來自於盟軍統帥的安排。”
梅汝璈這句話,相當於直接質疑起了韋伯的誠實,但此時的他揹負著全國同胞的期望,早已顧不上這麼多了。
說完之後,梅汝璈開始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準備回下榻的帝國飯店,韋伯雖然臉色漲紅,但他看到梅汝璈要走,還是趕緊攔住了對方,再次說道:“好吧,我再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韋伯的妥協
十分鐘後,韋伯第三次來到辦公室,他笑著對梅汝璈說道:“這次預演只是臨時性的,不必太較真,法官們晚上會重新開會,討論座位順序。”
這話乍一聽好像頗有道理,沒什麼漏洞,但梅汝璈一下就分辨出了其中的貓膩。
本次預演彩排是有記者等在外面準備拍照的,也就是說等下預演的坐席是必然會登上明天的報紙的,那到時候再換座位,先不說能不能換,就算換了也已經無濟於事,因為照片早已傳回國內了。
看穿了韋伯的小心思,梅汝璈怒道:
“如果我同意了這個安排,就相當於侮辱了我的國家,侮辱了中國人為了抗日做出的犧牲、努力和堅持。如果不同意更換坐席,我馬上辭職,決不出席彩排!”
韋伯顯然被梅汝璈的話唬住了,他深知11國法官缺一不可,要不然審判將無法正常進行,真到了那一步,他這個審判長難辭其咎,而且今天的彩排已經推遲了將近半個小時,所有人等得都很焦急,這件事必須要做個決斷了,要不然可能會影響到明天的開庭,這是韋伯不想看到的結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佈了,絕不能貿然更改。
無奈之下,韋伯看著眼前軟硬不吃,眼神決絕的梅汝璈,說道:“好吧,我同意你的意見,就按照受降書籤字順序來安排座次。”
聽到韋伯的話,梅汝璈心中彷彿千鈞的大石落了地。
第二天,各大報紙都爭相報道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前的最後一次彩排,並附帶了現場的照片,照片中,11國大法官神情莊重,依次坐在肅穆的法庭上,其中,坐在最中間的是來自澳大利亞的審判長韋伯,坐在韋伯左手邊的就是戴著眼鏡,蓄著鬍鬚的中國法官梅汝璈。
這只是這場世紀大審判的開始,但梅汝璈卻是格外的謹慎小心,每件事都據理力爭,不讓分毫,在他眼裡,東京審判之中,絕無小事,因為他知道,數千萬軍民的犧牲在前,他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退讓,哪怕只是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