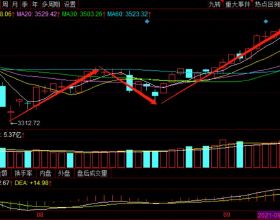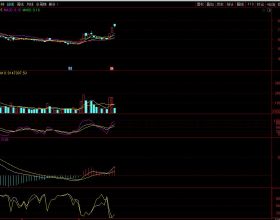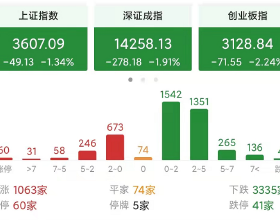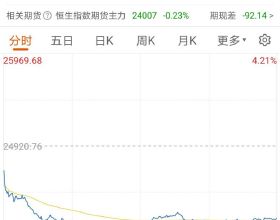記得有人說:人生要有一場奮不顧身的愛情,要有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那麼,人生就不遺憾了。
我過了四十歲,多多少少經歷過一些愛情,或甜蜜,或酸澀。不過離奮不顧身似乎總還是有點距離的,可也會在某個時候使我想起某些人、某些事,然後眼睛便會有些溼潤。說到旅行,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也是去過許多地方的,但從來都是醞釀好久才行動,說走就走,我沒有那麼灑脫。
但就在這個楊花落儘子規啼的四月天,我所居住的城市剛剛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雨季,恰逢五一小長假。我也剛剛從一場感情的旋渦裡掙扎出來,痛苦的枷鎖尚未完全擺脫,鬱悶像一片陰雲一樣壓抑在心頭。在耒陽社群工作的好兄弟老麥打電話來:“西門,車到你樓下了,咱們出去走走!”我早上還答應金子中午去她家吃飯的,然而現在就要離開這個城市,中飯還指不定會在哪裡吃?這算不算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呢?
周家大屋
汽車沿著鄉村公路向寧靜清新的農村行駛,躍入眼簾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綠色。深綠的樹木、翠綠的楠竹、淺綠的小草隨風搖擺,從車窗外不時晃過。
我們的汽車停在大義鄉東坪村的周家大屋前的公路上,幾個人下了車。周家大屋是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的後裔周德智所建,磚石木瓦結構,總建築面積有3680平方米,晚清年間建,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整個建築群坐東南朝西北,三進四廂,大小房屋51間,全部為磚石木雕、精工細做,斗拱飛簷,氣勢恢宏。很遺憾的是外面顯然是新建的一道圍牆,它顯得太新太豔了,找不到一點古樸的感覺。而且,因為這道圍牆,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角度來拍攝整個大屋的雄偉氣勢。於是幾個人步入大屋,迎面見了頗具規模的正廳屋,見了許多牌匾,同行幾人都是書法外行,看來看去,誰都看不出個所以然來,都只覺得比自己寫的好。那些木雕、斗拱、屋柱、牆磚我們倒是看得仔細,這的確不多見。那上面所雕刻的圖案依稀可辨。
周家大屋現在還有幾戶人家居住,我們不便打擾人家,於是退了出來。在大屋的前坪,辨認地上叢生的雜草。同去的幾人除了老麥是八零後外,其他幾個都是七零後,而且都在農村生活過,小時候扯豬草之類的活兒沒少幹。大家饒有興趣地辨認,居然認出了好多種:大葉白花的車前草,很少的時候就知道它是一種草藥;高挑挺立的淡綠的狗尾巴草是山間地頭最常見的一種野草,往往是不能找到足夠多的鮮嫩的豬草時才用它來湊數的;還有那滿臉皺紋的紫褐色的紫蘇,我們叫祖草,煮田螺用它很入味。谷彥平還在地上發現了幾株何首烏,我立刻想到了魯迅先生在百草園所發現的人形何首烏。“何首烏”單憑這名字就有些神秘了。
眾人說說笑笑,退到村口的愛蓮池。文老師面對池中盛開的睡蓮讚歎不已,那粉嫩、潔白的蓮花立刻讓人眼前一亮,一股清新雅緻的氣息彷彿一下子驅散了蒙在心頭的愚昧和汙濁。文老師眼角含情、面容嬌羞,宛如回到了風光旖旎的少女時代。老麥這個猛漢,我總是罵他土匪,而此刻也面帶微笑,很難得地表現了他溫情的一面。谷彥平一向是儒雅的謙謙君子,他時不時和我小聲交談,談兒時的回憶和自己對人生的感悟。
我自己亦有感悟。我過了四十歲,常常深入地思考人生,可越思索越迷惘。我所居住的城市,從我能記事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建設。人類對自然無休止的索取來滿足自己的貪慾,而這些又冠以現代文明發展的名義來掩飾。卻不知實際上我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我們對自然的索取造成極大的浪費,並且這些浪費還是我們失去許多不可挽回的損失所造成的。
西門年輕時在深圳打工,剛去的那一年有段時間住在筆架山下一個老鄉四面漏風的木棚裡。每天早上走五、六里路去上班,路過一幢幢高樓大廈總是無限感慨:深圳好多人沒房住!好多房沒人住!
而眼前這周家大屋,當初建造者也是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他又怎麼能想到這麼一大片建築如今就這麼佇立在斜陽深草中,荒蕪得連歲月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