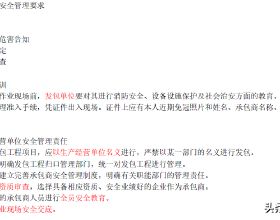一個老兵的回憶:
我作為一個老兵,回憶戰爭歲月,實實在在的,想忘也忘不掉。那許多熟悉的面孔,早已在黃土地裡湮沒,漸漸地在我的記憶中模糊了。每當想起了他們,都會使我反省,活在世上的人,就應該知足,對人對事要看得開,在生活中要永遠低調、別無苛求。可是這些話只有我自己相信,說給別人——甚至自己的孩子,他們都會認為我在擺老譜、說空話,他們會聽不進去,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苦難歲月,沒有足夠的人生經歷,必然會缺失相應的承受能力。
人到老年,總是憶舊,老是想起當兵時光:那時候我正年輕,作為一個新兵,我在一群老兵中顯得十分幼稚,他們講述西路軍征戰往事,那血琳琳的激戰場面、驚得我閉不上張開的嘴巴,一個湖南籍老兵好開玩笑,他會手托住我的下巴,讓我的嘴巴回位,他說,小伢子,莫要被嚇到。要好好練兵做準備哦,改天和日本人打仗,怕比馬匪更兇哦。其後,我被調到總部特務團教導隊,學習軍事技術,我們的老師有老兵,有高階將領,學習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有德國的、蘇聯的、還有敵人日本的戰略戰術,還要操練打野外,游擊戰術的單兵訓練,在肉搏戰術講解中,還請“反戰同盟”的日本兵,教我們拼刺刀……等到下課,也沒時間休息,大家都到野地裡去挖野菜,到石頭縫裡去扒拉陳年舊歲掉落在裡面的核桃,我們的肚子需要任何能把它填滿的東西,正經的糧食極其稀缺、遠遠不夠大家食用。
教導隊的集訓,只有短短的三個月,所有的學員都是排以上幹部,環境艱險、規定結業後立即迴歸原作戰部隊,我和另外幾個人卻沒有迴歸原來的連隊,39年底,通知我們到總部另行分配工作。還沒有跟大家告別就離開剛剛熟悉的老部隊,我們的心裡都有些彆扭,作為軍人、對未來的新任務沒有猜測只有服從。
在太行前總司令部,見到一個女首長,漂亮又精幹,她細細的腰上彆著一把小手槍。別人告訴我說,她是總部組織科長,長征過來的。同時說,她腰上是一把小號勃朗寧手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勃朗寧手槍。她首先向我們講明瞭軍工部建立的作用和意義,然後鼓勵我們在新的戰線上努力完成這“比打仗更艱鉅的任務”。工作交待完,她和我們握手道別,沒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面。41年底的黃崖洞保衛戰中,她壯烈犧牲。
以後的時光,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接手了地方上的鐵工廠,改建成兵工廠,我們白手起家,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槍炮和炸彈,幾年間我也成長為兵工廠長。1942年,我到軍工部所在地河北邯鄲開會。會議期間,我發現在領導席位上有一個我認識的人,姓袁,他是閻錫山部隊的軍官,我參軍以前,地方上建立“犧盟會”,當時給老百姓做報告的就有這個人,他當時穿閆軍軍官制服,我立即報告給保衛部門,保衛部門也不清楚,陪我向部長報告,兩位部長都聽了我的揭發,一會兒,政治部張主任就把那人帶來了,張主任向他耳語幾句又指了指我,他笑著過來和我握手,兩位部長都笑了:一家人,一家人。張主任鄭重介紹:袁處長,1931年的老黨員,曾潛入閻軍作地下工作,擔任過閻錫山新軍的軍事教官,所以,你誤會了,後來,新軍身份暴露迴歸八路軍部隊,原來是自己人,老革命。我啪的一個立正:對不起,首長,誤會你了,向你賠罪,敬禮!袁處長對部長說,不簡單,這位同志很有警惕性,對黨忠誠。會後,我們回工廠前,袁處長鼓勵我:不錯,參軍四年就有這麼大的進步,現在當了廠長也算領導了,來,給你開個小灶,換換裝備吧。於是,我拿著處長批條子到後勤部的軍械部門領武器,一進庫房,我立即看中了一把小號勃朗寧手槍。
這些年在軍工部門工作,我對各種武器,尤其是長短槍支有了些瞭解。在庫房的眾多型號手槍中,我立即看中了一把精巧的比利時生產的勃朗寧小手槍,當時俗稱“掌心雷”。老同志們愛說,官越大槍越小,我當時選擇小槍,並沒有從實用上過多考慮,這也許是年輕時的虛榮心吧。
不久,戰爭進入艱苦歲月,敵我拉鋸戰激烈進行,一次,隊伍打散,我們工廠一部分人員與縣武工隊相逢,於是結伴進入深山掩蔽,和武工隊匯合,使我稍感安心,因為我們兵工廠的人員大都沒有經歷戰陣,沒想到走過了幾道山樑,突然與一股日軍迎面相逢,一開始大家都沒有看出來,等到離得近了,大家一起驚呼散開,由於山溝裡灌木和野草茂盛,雖然遮蔽了我們,可是也看不到敵人,於是大家衝著前方不斷開槍,武工隊的還依託著土梁拋手榴彈,打了許久,不見了對方動靜,以為把敵人都打死了。膽子大地摸索過去檢視,原來對方只是一個小隊,居然後撤、溜了。大家鬆了一口氣,坐下來歇息。突然,王大隊長說:“敵人去向不明,注意隱蔽”。話音剛落,大家還沒找好地方,頭頂上一梭子子彈掃了過來,大家就地臥倒,慢慢向彈道的死角移動,原來小股敵人繞道佔據了一處制高點,架設了機槍,用火力掩護他們撤退。我由於精神緊張,打了幾槍,最後想起要給自己留一發子彈,開啟彈夾一看,子彈沒了,心裡又是一陣子慌張,因為大家都知道,不能當俘虜。所幸敵人也不敢戀戰晃虛一槍,終於撤得杳無人煙了。敵人跑了,大家反而更緊張了,誰知道周圍潛伏著多少危險呢,最後,大家找了一處山崖頂部休息,說是如果打,咱們在高處,打不過,身後就是山崖,咱們就跳下去。歇下來,我檢視自己的手槍,看見王大隊長在笑,我問他笑啥,他揶揄我:“你那個槍比老孃們的炕笤帚強,離著幾百米遠,你那玩意兒能頂啥用,留一顆子兒給自己,你到都打光了,捨不得自己用”。我也有點慚愧,作戰部隊都呆過,現在用這把只能打五十米的玩意兒,等於在戰場上玩命,令人後怕。由於過度疲勞,大家都躺在野地裡熟睡過去。半夜,槍聲大起,驚醒了大家,看到不遠處火光一片,槍炮聲密集,似乎是總部所在的XX鎮方向。不一會,聽見,武工隊王隊長一聲大叫,只見他手指著地面張著嘴說不出話;大家看見,地面上一大片過兵的痕跡,其中的馬蹄印跡歷歷可見,這是夜裡繞過我們的日軍留下的,他們的目的是偷襲既定目標——前線總司令部,所以就沒有驚動我們。大家偷偷吸了一口涼氣,我們的生死居然處於一線之間。雖然在半夜的山樑上冷風習習,可是我們都驚出了一頭冷汗。
天剛放亮,幾個人牽來一匹大白馬,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東洋馬。雖然我當兵就在通訊營,經常騎馬,對這匹顯然是受了驚、亂蹦亂跳的大洋馬也不敢造次試騎。中午時分,幾個戰士跑來尋找,見到了大白馬立即向我們索要,說是陳賡司令員的。有人不服,說:口說無憑,你怎麼能證明是你們的?那個小警衛員沒理我們,打了一聲口哨,那馬立即跑了過來歡跳,又隨著警衛員的口令臥倒、起立。好啦,我雙手一拍,沒得說,是陳司令的馬,歸還。小警衛看見我腰間的槍,跑來一個敬禮:謝謝首長。我的天,沾了這小手槍的光,成首長了。那個年頭,我軍可沒有軍銜,所以,看佩槍的檔次判斷。
知道我這把小擼子的人還不少,一天,有人找上門來,拿來一個沉掂掂的布包,小心翼翼開啟,一把大威力的勃朗寧。
想起在山裡跑反時,王隊長說過我的槍中看不中用。是女同志護身的。後來,在緊急時刻,我也覺察到它威力不足,彈夾裡只有六發子彈。別人告訴我,真正的好槍是新的大號帶連發的博朗寧,裝十發子彈,一槍打過去,能把人打一個跟頭。現在,這麼巧,有人送了過來。原來,我的佩槍早有人惦記,所以,有人便用這把大號的勃朗寧來換,其實,經歷了那場遭遇戰,換一把威力大的手槍,正合我意。
反掃蕩戰役後,我打聽到自己原來的部隊駐紮在附近,就抽空去看望,從調工作離開他們快三年了,等大家見了面我才知道,原來鬼子偷襲總部那場戰鬥,就是我原來的部隊在保衛總部,敵人的武器兇猛,我軍損失很大。活著的同學們告訴我,教導隊一半學員都已經犧牲了,我抱著剩下的這些同學大哭起來,我實在太難受了,我們那些同學都是多麼好的人啊,他們有許多人是紅軍西路軍戰士,躲過了馬匪的屠殺,卻犧牲在抗日戰場。
1945年,我們分割槽司令員要結婚,他的前妻就是總部當年給我安排工作的那位女科長,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這位未婚妻是太行地區有名的女婦救會長,由於去分割槽司令部要路過我們這裡,就安排由我招待她住宿,我立刻把我的住房打掃好,安排我愛人來招待她過夜休息,吃飯時,我陪著她,看到到她的腰裡彆著一把“掌心雷”——居然就是我原來那把1906型勃朗寧小手槍,連槍套都是原配。
我的大威力勃朗寧在我手中,直到全國解放都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兵工廠成了大後方。後來兵工部門與軍隊分離。我把槍交還了有關部門,但那個牛皮槍套我留下了,至今還在箱子底下,和我的八路舊軍裝在一起,這是我在部隊生活的一個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