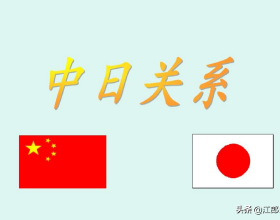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伊斯蘭恐懼症”如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澎湃新聞:您還寫過另外一篇文章,闡釋“伊斯蘭恐懼症”是如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的。您提到,在談論“伊斯蘭恐懼症”時,即使是美國人也不例外,他們會將9·11事件與從十字軍東征到奧斯曼土耳其圍攻維也納城的歷史聯絡在一起。但諷刺的是,20年後,美國就這麼草草地從阿富汗撤出了。
費薩爾·德夫吉:“伊斯蘭恐懼症”的問題,確實會發生。無論如何,我們目前在西方看到的是對與聯軍合作阿富汗人無盡的痛惜,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在喀布林機場已經被撤離,另外一些人湧向了巴基斯坦、伊朗邊境,在美國、在英國,外界似乎有太多的同情。目前還沒有太多的反移民和反難民的聲音,但是這很快也有可能發生轉變,就和敘利亞最初的情況一樣,一開始敘利亞人是受歡迎的,但隨後迎來了反移民和反難民的高潮,也導致歐洲國家的極右翼更為強大。所以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也很有可能以一種“伊斯蘭恐懼症”的方式發生,就像敘利亞人的情況一樣。極右翼擔心恐怖分子正在透過難民的流動滲透到西方國家,但現在這一刻還沒有發生,我們要觀察一段時間,看看那裡(歐洲)會發生什麼,但我認為風險肯定是很高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問題也將會是更加重要的。
澎湃新聞:很有趣的是,三年前我在敘利亞遇到了一些歐洲的極右翼,他們往往都與阿薩德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當敘利亞政府軍奪回大片土地時,他們為阿薩德歡呼。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歐美一些極右翼支持者也在為塔利班慶祝。
費薩爾·德夫吉:這非常有趣,因為在敘利亞,你可以想象,這些極右組織可能會把阿薩德政府視為是一個非伊斯蘭的政府,但是我們不能這麼看塔利班,因為他們的政府將會是遵循伊斯蘭教法的。一方面,阿薩德政府得到了來自俄羅斯的支援,另一方面,它也得到了像伊朗這種伊斯蘭國家的支援,這是曖昧而矛盾的。塔利班可能也是如此,也許歐洲的極右翼運動更加關心的是難民是否會湧入,其次他們才會關心政權本身。
同時我也認為,極右翼反自由主義和反全球化、新西方自由主義的性質實在太過強烈,以至於他們看到任何反對這種政治形式的人都會自動成為他們的盟友,所以他們建立起了這種荒謬的“友誼”。極右翼同時也模仿著一些物件,即使是他們不喜歡的人。在這種基督教“聖戰”的思想中,人們的心被團結在一起,塔利班其實也是類似的,因為西方的極右翼其實與政治伊斯蘭分子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點,他們對於社會的幻想——人類在道德上可以是完全純潔的、在這個社會中男女完全隔離、保持等級制度、法律是嚴厲的……他們共享著所有這一類的想法,即使二者的合法性來源全然不同。所以你會經常看到,伊斯蘭恐懼的極右翼們和伊斯蘭國家、領導人及政府之間的關係似乎相當矛盾。
澎湃新聞:為何人們只會說“伊斯蘭恐懼症”,而從來沒有過“基督恐懼症”或是其他宗教的恐懼症?歷史上也發生過很多基督徒實施極端襲擊的事件,2018年發生在紐西蘭清真寺的襲擊就是一個例子,但是人們並不會責備整個基督徒群體。
費薩爾·德夫吉:現在,“伊斯蘭恐懼症”這個詞好像十分自然,每個人都會用這個詞,但其實這個詞是新造的,從上個世紀90年代才開始使用,這個詞有太多需要批評的點。首先,這是一種“伊斯蘭例外論”(Islam Exceptionalism),沒有其他的“恐懼症”,只有“伊斯蘭恐懼症”。當然,現在一些印度民族主義者也會說,世界上存在一種“印度教恐懼症”(Hindophobia),但這種邏輯其實還是“伊斯蘭恐懼症”的邏輯。
我不喜這種例外論的行動,就像我也不喜歡“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這個詞,對於其他宗教來說,不會有這種詞,只有伊斯蘭教。這種例外論把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從這個社會的語境當中剔除了。關於“伊斯蘭恐懼症”的有趣之處在於,人們選擇了“伊斯蘭”這個詞,但這並不適用所有穆斯林,而“恐懼症”(phobia)這個詞是一種分析心理學的術語,通常指的是精神疾病。一方面,這個詞把問題政治化了,另一方面,它注重的是抽象化的概念——伊斯蘭,而非作為個人的穆斯林。這種現象其實有很長的歷史,人們反對的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信仰它的人。
在兩個案例中,都會有虛偽的事情發生,因為實際上“伊斯蘭恐懼症”的受害者不是伊斯蘭教,它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它不存在,它的受害者是穆斯林人民。同時,伊斯蘭教被呈現為受害者,也授予了一些人“政治代理權”,因為“伊斯蘭恐懼症”這個詞的存在,穆斯林再次陷入激進分子宣傳的刻板印象的圈套中,即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是受害者。我認為,穆斯林也很有必要否認自己是受害者,因為群體一旦被視為受害者,會導致非常可怕的心理障礙,也會妨礙穆斯林作為一個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共鳴。這是我對“伊斯蘭恐懼症”的反對意見。同時,我也同意,確實存在特別針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和歧視,就像人們對黑人、對亞洲人,或是女性的歧視一樣。
穆斯林與西方:多元化還是同質化?
澎湃新聞:您也提到了“伊斯蘭例外論”,其實很多西方的學者也尖銳地提出,他們看到穆斯林嘗試了這麼多年,都沒能完全讓自己的國家成功實現現代化,或者說是達到西方標準的現代化,他們認為問題出在伊斯蘭教本身。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在您看來,政治伊斯蘭運動是由根植於伊斯蘭這種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所驅動,還是說,這是一種對政治、經濟等其他機制的結構性變化所作出的回應?
費薩爾·德夫吉:當然,我認為任何“合法的”歷史學家都會選擇第二種,否則,就會創造出例外。確實,政治伊斯蘭運動的領導人可能會回到宗教文字,甚至是很久以前的文字本身,但是隨著時間流逝,這些文字的意義會發生改變,語境不會是相同的。政治伊斯蘭主義者和反政治伊斯蘭主義者另一重諷刺的關係在於,二者都認為存在一種單一的、持續的歷史。我反對這一點,我認為歷史是改變中的歷史,一切都取決於政治、經濟等結構,它們當然會改變。文字和教義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它們在不同的語境下起著不同的作用,也擁有了不同的內涵。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的變化,有時重要,有時不重要。這些過去的元素、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從那個時代開始起已經發生的事情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和辯證關係,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如此。所以我想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將這些穆斯林團體當中的任何一個排除在外。當然,人們可以像我一樣對他們持批評態度,但同時又不將他們排除在外。例如,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歷史上的一個特定階段,此前從未出現過。但是法西斯主義利用了很多歷史上的元素,反猶太主義早於法西斯主義,在西方基督教當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這段悠久的歷史在納粹主義那裡被拿去做了非常不同的事情。相似的是,種族主義也出現在法西斯主義之前,但是它同樣被改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形式。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討論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我們也可以如此討論政治伊斯蘭主義和聖戰主義,或是任何相關的事情。
澎湃新聞:您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張口閉口‘穆斯林統一’只會使穆斯林遠離統治其社會的民族國家構成的政治社會。”在談論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語境下,可能很多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在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社會的問題上,您更贊同哪種方式?是像英美一樣更多地允許文化多元,還是像法國一樣,在所謂的“世俗主義”(laïcité)框架下進行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ulation)?
費薩爾·德夫吉:我認為這取決於不同的國家和它的傳統。我願意相信,以多元化的方式來理解政治生活是可行的,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必須看起來一樣,做一樣的事情。但我想比起允許多樣性、堅持公民身份的統一性,這個問題更多是一個是否獲取平等機會的問題。
我想知道,如果法國能夠確保所有的公民都得到平等對待,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問題是否還會出現?大多數法國穆斯林都是世俗的,法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通婚率是歐洲最高的,這意味著許多人都很好地融入了“法式生活”。但是如果他們仍然會因為自己的名字或者膚色被歧視,那麼就有問題了。需要統一的公民身份還是多元化的公民身份,這與各國的傳統、憲法和歷史有關,不能以同樣的方式普遍化,但是可以普遍化的是所有公民的平等,一旦這一點得到保證,我認為其他問題就不會那麼成問題了。
我們必須記得,歐洲,特別是西歐,有著很長一段時間的轉型期,直到很近的一段時期社會才變得多元起來。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前,歐洲也是一個完全基督化的社會,可能會有一些猶太人,但猶太人在一些國家也會遭到驅逐。在被征服之後,穆斯林、猶太人在西班牙被驅逐,在英格蘭被驅逐……儘管有一小部分猶太人,但他們的存在也不被寬容。隨著宗教改革,西歐出現了新教教會,這些國家必須進行重塑(refashion),無論是新教國家還是天主教國家,它們必須在內部實現統一,所以統一基本上是歐洲傳統的一部分。
到了20世紀中期以後,歐洲才不得不開始應對多元化的問題。但其實我們看看亞洲和非洲,這裡聚集著大量的宗教、民族和語言多元的群體,無論是在中國、印度、中東,還是非洲,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每個人都要在語言、宗教或族群上統一的情況,其實世界其他地區並沒有西歐所具有的同質化(homogeneity)歷史。我認為,在一種“製造同質”的政治議程下,西歐其實比其他地區面臨的問題更大。
現在是西歐歷史上第一次真正面臨種族、民族和語言多樣性的挑戰。在過去,西歐只有特定的幾個國家擁有一種以上的語言,而這些語言之間的區別可能又不大。總之,這都是關於同質化的問題,公民身份的問題也與之相關,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在不同質化的情況下實現平等?我想在亞洲、中東或是非洲,我們可以更容易找到這個答案。北美甚至南美是另外一種情形,因為這些國家是殖民者建立的國家,它們吸引了歐洲不同地區的人來定居,當然,他們也有土著人口,還奴役了非洲來的黑奴,所以他們已經不是同質的了,不可能再像西歐國家那樣變得同質化。
比起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法國模式可能正在進入一種危機,儘管兩種國家都遭遇了恐怖襲擊。法國的“世俗主義”模式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我不清楚,一旦法國社會開始在人口結構上發生變化,它還是否可行。即使法國在帝國時期,社會也非常同質化,基本上是羅馬天主教教會,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律開始標準化,一種民族性被創造出來了。帝國末期,隨著移民的到來,突然間一切似乎都處於危險之中。

畫家菲力波託(Philippoteaux)描繪了1848年革命的景象,1848年革命後七月王朝覆滅,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 。
歐盟的出現,讓更多的人開始質疑民族性格的重要性。金融主權不再存在,某種程度上政治主權也不再存在,因為有了歐洲議會。因此,文化問題變得更加重要。國民手裡的金融、軍事和政治主導權被奪走,他們能夠依靠的只有這些歷史和文化身份。我認為與其說這是一個政治原則問題,這更多像是一種心理上的問題。
“你永遠無法打一場針對抽象的戰爭”
澎湃新聞:人們在談論不同的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時候,總是傾向於把它們分成“溫和的”、“極端的”,但事實上它們在理論上可以算作擁有同一種意識形態根基。在這20年來我們談論“反恐”的時候,“極端主義”又幾乎和“恐怖主義”劃上了等號。在您看來,“溫和”與“極端”之間有分界線嗎?“溫和”是如何走向“極端的”?
費薩爾·德夫吉:我認為沒有一種真正能夠區分的方法,當然,這兩種說法經常會被提及,特別是一些政府可能會用到。我們會認為“極端”意味著人們會使用殘酷的暴力形式,但是其實並不總是這樣。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現在人們竟然嘗試區分“好基地組織”和“壞基地組織”,所以,即使是20年來我們看到的最惡劣的敵人,他們當中也可以分出溫和和極端。
這取決於哪些團體可以被西方國家利用,或與之進行談判,與他們實際做了什麼幾乎沒有關係。大多數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可能沒有像“伊斯蘭國”一樣蓄意、殘暴,像“努斯拉陣線”還有一些其他的組織可能會很暴力,但這(溫和與極端)通常與暴力程度無關,而與國際地緣政治有關。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實際上所有這些組織都沒有對任何一個國家形成既定的挑戰,即使是在伊拉克或是敘利亞,除了摩蘇爾被佔領這樣的事件。之所以這些組織得以變得如此強大,與國家被制裁有關,也與國家之間的代理人戰爭有關,許多外部力量被捲入,他們各自支援自己的代理人,這是我們熟知的故事。這也更能說明,這些組織的“極端”與“溫和”與他們本身的關係不大。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情況會隨著地緣關係的改變而改變。
澎湃新聞:前一段時間我在採訪前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的時候,他的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恐怖主義是一種戰爭的工具,並不是你可以反對的東西,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一種手段,一種暴力的手段。你確實無法有效地反對一種手段。”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我們今天應該如何應對恐怖主義的威脅?
費薩爾·德夫吉:我確實認識傅立民,我曾經在貝魯特和他見過好幾面。我完全贊成他說的這段話。恐怖主義是一種工具形式,對於恐怖分子來說,它可能具有存在意義,但是它並不特定於任何意識形態。當然可以有伊拉克恐怖分子,也可以有巴斯克恐怖分子,也可以有伊斯蘭恐怖分子……許多不同種類的恐怖分子,有國家恐怖主義,還有非國家恐怖主義。確實,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是荒謬的,但美國人打了一場這樣的戰爭。
美國人有很多場戰爭,並不是真正的軍事戰爭,比如反犯罪、毒品或貧困的戰爭,這是一種政治語言被軍事化的現象。不僅僅是語言被軍事化了,在哥倫比亞等南美國家,在這場“反毒品戰爭”當中,實實在在的戰爭也發生了。“反貧困戰爭”也是真實存在的,因為有時貧困的人會成為目標。“打擊犯罪戰爭”也是一樣,這導致非裔美國人的監禁率非常高。這些戰爭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戰爭,但具有非常真實的影響和後果。
所有這些戰爭,都是針對抽象(abstraction)的戰爭。反貧困戰爭,反毒品戰爭,是什麼意思?毒品只是一種商品,商品是怎麼流入的?為什麼人們會去購買?誰在推銷這些商品?導致吸毒上癮的社會問題是什麼?這才是人們必須考慮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反恐戰爭也是一樣的,雖然他們沒有用“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Ism這個詞綴指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他們用的是“反恐怖戰爭”(war on terror),“恐怖”這個詞,只是一種工具。
你永遠也沒有辦法打一場針對一種工具的戰爭,你也沒有辦法打一場針對抽象的戰爭,像是恐怖、犯罪、貧困……你必須要理解誰才是你要與之戰鬥的人,而這正是這麼多年來人們疏忽的。阿富汗之所以到今天的局面,是因為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被人們忽略了。人們關注的一切都是有關工具的,人們把某些群體工具化,人們找來了外部承包商重建,找來了非政府組織為婦女賦權,但實際上這些都沒有觸及任何真正的問題。
責任編輯:張無為
校對:張亮亮